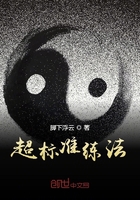中对于这些条文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中体西用的色彩。如对于“忠君”就是要“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涤风雨飘摇之惧。”这样就会使在当时已经不可收拾的“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所谓“尊孔”则是要让学生在儒学的熏陶之中,“以使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但是从尚公和尚武等条文虽然其解释的依据依然是从儒家的经典出发,但已经明显与传统的儒家教育观有一定的距离,而是更有着时代性,并带有明显的西方教育观的影子。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儒家已经不再作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随之,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连带着教育的制度和课程的设置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1911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就明显是针对1906年的教育宗旨而发的。他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912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很显然,新教育观体现了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改称学堂为学校,令上海各书局将旧存教科图书暂行修改应用,并令废止读经,并禁各校用《大清会典律例》等。当年五月,又由教育部宣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条文很多,对于学校和教科书特别提出:“(一各项学堂改称学校;(二)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民国宗旨。前清学部宣布所颁及民间通行教科书中有崇清及旧时官制避讳抬头字样,应逐一更改。教员遇有书中有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并指报教育司,或教育会,通知书局更正。(三)师范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
1912年9月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在第一章《总纲》
的第一条中指出:“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在11月颁布的《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与儒家有关联的是修身、国文和历史。
在《教则》中对这几门课的教育目的作了说明。“第二条:修身要旨在涵养儿童之德性,导以实践。初等小学校,宜就孝悌、亲爱、信实、义勇、恭敬、勤俭、清洁诸得,择其切近易行者授之;渐及于对社会对国家之责任,以激发进取之志气,养成爱群之精神。高等小学校宜就前项扩充之。对于女生尤须注意于贞淑之德,并使知自立之道。
教授修身,宜以嘉言懿行及谚辞等指导儿童,使知戒勉,兼演习礼仪;又宜授以民国法制大意,俾具有国家观念。”
1915年起,启蒙教育又分为国民学校和高等小学校。但在教育宗旨和课程设置上并无大的变化,国民学校和高等小学校的修身课的内容与1912年的基本一致。唯一值得指出的是在1915年的课程设置中,均加上了“读经”课。
如1916年1月颁布的《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中指出:国民学校学生的“读经要旨,在遵照教育纲要,使儿童熏陶于圣贤之正理,兼以振发人民爱国之精神。宜按照学年程度讲授孟子大义,务期平正明显,切于实用,勿令儿童苦其繁难。”
同时颁布的《高等小学校令实施细则》,指出“读经宜照教育纲要讲授《论语》”。而在同年10月颁布的修正稿中,均删除了有关读经的条目。
1912年9月,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公布了中学校令,明确指出“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而在同年12月公布的实施细则中,对于传统意义上与儒家有关的课程“修身”课作了如下规定:“修身要旨在养成道德上之思想情操,并勉以躬行实践,完具国民之品格。修身宜授以道德要领,渐及对国家社会家族之责务,兼授伦理学大要,尤宜注意本国道德之特色。”其课时均为每周1小时,在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中,对四年中的修身课内容作了更具体的说明。
第一学年,讲授:“持躬处世,待人之道”。
第二学年“对国家之责务,对社会之责任。”
第三学年:“对家族及自己之责务,对人类及万有之责务。”
第四学年:“伦理学大要,本国道德之特色。”
虽然很多内容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但是可以明确看出,在避免使用儒家的标识。但对于外国课则是一如既往的重视,中学四年,外语课则是每周6小时。
虽然当时另公布了针对女生的时刻表,但只是有一些小的差别,并不影响本文所要推导的结论。
1912年教育部公布了大学令,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913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分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原有的经学科没有了。
有关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我们可以在哲学门中的中国哲学类、国文类和中国史类中找到。当时列入课程表的儒家经典有:列入中国哲学类中的《周易》《毛诗》《仪礼》《春秋·公、谷传》《论语》
《孟子》。
列入国文类有尔雅学等。列入中国史类的有:《尚书》《春秋左传》等。原来将大学毕业后继续深造的机构称为“通儒院”,这时也已经改为“大学院”。学生从高等学校毕业授予相应的学位。
从上述教育宗旨和课时变化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废除科举之后,儒家的价值观和儒家经典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越来越找不着自己的位置,最终随着民国建立——儒家制度的合法性的消失而失去了其存在的空间,大学以下的各级学校取消读经课,即使是大学里的有关儒家经典的内容,也已经是作为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学的文献,已经完全“非经学化”了,只是作为众多知识中的一部分,只是众多课程中的一门。
由此,运行了一千多年以察举、科举等选举制度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儒家传播体系,也终于因选官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建立而宣告中断。
虽然《剑桥中国晚清史》对于废除科举之后的教育内容是否有实际的变化持怀疑态度。他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是(1)由于难以找到合格的老师,如1909年,在教初等小学的教师中,有84%的人有传统功名,他们难免会按传统的旧课程上课。
(2)几乎所有私立学校均由绅士开办。
(3)制度中保留了尽量多的旧东西。如学堂毕业授予相应的功名和对于留学生的奖励办法都能明显看待这种连续性。
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理由的重要性,例如前面所列举的新学堂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由于教师和资金的问题在具体的操作中可能出现的变样。
同样,我们也必须正视习惯的力量,因为很多人依然是以科举的心态来对待新教育的。这可以从众多的学生钟情于法政科中可以得到证明。
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并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以致于社会上更欢迎那些学徒而非学生。但我们不能否认废除科举和建立新学堂所造就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体系。
随着模仿西方的教育制度的建立,从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逐渐变成教育的核性内容,并形成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巨大的“惟科学主义”,这使得以儒家为核心的人文知识被日益挤到边缘性的位置。
其实,当西学被冠之以“新学”的时候,我们已经隐约能感觉到在新式知识分子那里,儒学已经被视为“旧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难以承担保国保种的任务。而作为新学之代表的科学,几乎成了新的迷信。
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之下,新学堂所采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外国教才的翻译和改编,而当时的教员也请的外国人,主要是日本人。
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便是随着这些新的教科书的使用而流传,当然西方的地理概念、男女平等思想、进化论观念、民主观念也随之而深入到新学生的内心世界,而中国本土的知识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如胡适回忆他小时候的学习生活时说:“二十五六年前,当我在上海做中学生的时代,中学堂的博物,用器画,三角,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往往都是请日本教员来教的。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武昌,成都,广州,各地的官立中学师范的理科工课,甚至于图画手工,都是请日本人教的。外国文与外国地理历史也都是请青年会或圣约翰出身的教员来教的。我记得我们学堂里的西洋历史课本是美国十九世纪前期一个托名’PeterParley’的《世界通史》,开卷就说上帝七日创造世界,接着就说’洪水’,卷末有两页说中国,插了半页的图,刻着孔夫子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这是二十五年前的中国学堂的现状。”
即使在农村和集镇的初级学校,教师的状况一方面由于不断的新学生的毕业而有所改变,同时旧绅士也经过适当的培训逐渐改变了他们的观念,或者说他们也开始接受新的观念。杨懋春的回忆可以作为佐证。
他说“当时(1915年)县政府在其辖境内每一较重要或中级以上的集镇上设一公立模范小学。校舍多是镇上的庙宇、祠堂,或其他不被使用的公私宅院。管理员(或校长)是由地方人士公推的绅董。
教员是县政府聘请或委派者。教员的资格多数是由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年龄在廿五到卅五岁之间。也有不少是清末科举制度下的秀才,后在县立或省立师范讲习所进修两年者。这类教员的年龄多在五十岁左右。模范小学的课程都是新的,包括国文、算术、博物(或常识?)、修身、劳作、音乐及体操。国文与算术两科份量最重,教学时数也最多。其次是修身。年轻的老师也会注重音乐。爱国情操浓的老师也多用体操课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要学生练习军操,一备长大后,从军保卫国家。因为那时候以日本为首的列强正想瓜分中国。”而在公费教育力所不及的地方,教会学校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近代的教育体系中,教会学校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充分加以关注的。
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新教育培养的就是旧制度的敌人和旧传统的解构者,就在科举废除后的五年,清政府便崩溃了。十年后,以彻底清除中国人观念中的儒家遗存而为西方的观念腾出空间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爆发。
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虽然不能将儒家传播体系的崩溃和中国的发展加以简单地联系,但是儒家逐渐失去了它所固有的依存物,而变成无根基的状态,则是其“花果飘零”、“收拾不住”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