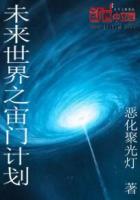中国以专制最久闻,自秦以来,为君主者不下千数,问其能实行完全圆满之专制者,能有几人乎?吾窃尝区二千年来君主之权力为四种。第一,有全权亲裁万机,毫不被掣肘于他人者,凡得二十二人,曰秦始皇,曰汉高祖、武帝、光武、昭烈,曰吴大帝,曰秦符坚,曰宋武帝,曰齐高帝,曰北魏孝文帝,曰北周孝武帝,曰唐太宗,曰周世宗,曰宋太祖、神宗,曰西夏李元吴,曰元世祖,曰明太祖、成祖,曰本朝圣祖、世宗、高宗。第二,其权力虽不如第一种之强盛,而承袭先业,继体守文,亦不甚被掣肘于人者,凡得十二人,曰汉文帝、明帝、章帝,曰魏文帝、明帝,曰陈宣帝,曰宋太宗、真宗、仁宗,曰本朝仁宗、宣宗、文宗。第三,初时行其全权,或穷侈极欲自奉一人,或穷凶极暴震天下,后卒身危国削身弑国亡者,凡得十一人,曰新莽,曰吴孙皓,曰宋废帝,曰齐明帝,曰梁武帝,曰陈后主,曰隋文帝、炀帝,曰唐元宗、宪宗,曰宋徽宗。第四,则不能自有其全权,或委政于母后,或委政于外戚,或委政于权臣、佥壬、宦寺。虽其间安危异数,荣辱殊途,大抵危而辱者十之七八,安而荣者十之一二,要之其不能自有专制权则一也。凡前所列诸帝以外之君主,皆属此种。由此言之,君主千数,而能真行专政权者不过此三四十人,其因此而酿弑亡之祸者,尚三之一焉。自余则虽拥有普天率土之名,而实则唯诺守府,祭则寡人,其甚者,则身处樊笼,背悬芒利,其困贳苦难不自由,有甚于吾侪小民十倍者。专制云,专制云,却笑年年压针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吾不知于君主果何利也若夫欲借此专制权以穷极耳目之欲者,则吾见夫为君主者无此心则巳,苟有此心,则其专制权终不能一朝居也。
夫不必其瘁心力以顾公益为民事也,即使欲保其产业以长子孙焉,固己不可不劬劳于在原,咨嗟于在庙,宵衣旰食,日昃不遑。昔人大宝之箴,帝范之鉴,迂儒腐生,皆能言之。
乾隆御制诗有云:“不及江南一富翁,日高三尺犹铺被。”诚哉,其阅历心得亲切有味之言也。黄梨洲原君篇又云:“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故吾以为人而不欲求耳目之乐则巳耳,苟其欲之,则他种地位皆可居,而惟专制君主之地位万不可居。苟居之,则乐未极而哀巳来,欲未满而身为葿矣。专制云,专制云,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吾不知于君主果何利也准此以谈,则吾所谓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者,虽苏张之舌,其无以为难矣。夫其利害之理,既至分明而易识别也若彼,利害之数,又屡经验而有成例也若此,则诚宜如梨洲所云,以俄顷之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而竟数千年覆辙折轸,不绝于天攘者何也?曰溺于所习,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边沁倡乐利主义以为道德之标准,而世固有纵饮博之乐,贪穿窬之利,而自托于边沁之徒者焉,算学不精,而因以自误也。夫世之君主及君主私人,以拥护专制政体为自乐自利之法门者,亦犹是而巳矣,亦犹是而巳矣且君主及君主之私人,所以必拥护专制政作者,吾知之矣。彼其心以为专制政体,与君主相依为命,去其甲而乙亦不能立也。噫嘻,其陋矣!专制政体为一物,君主为一物,两者性质不同,范围不同,夫乌得而混之。不观欧洲乎,今世欧洲十余国中,除法兰西、瑞士外,皆有君主,此读史者所能知也;除俄罗斯、土耳其外,皆无复专制政体,又读史者所能知也。而最近之日本,又其明证矣。百余年前之欧洲、日本,其贵族专政之祸,犹吾国也;其女主擅权之祸,犹吾国也;其嫡庶争位之祸,犹吾国也;其宗藩移国之祸,犹吾国也;其权臣篡弑之祸,犹吾国也;其军人跋扈之祸,犹吾国也;其外戚横恣之祸,犹吾国也;其佥任朘削之祸,犹吾国也。所谓亡国十原因者,而彼等备其九焉,所缺者惟宦寺之人妖耳。而诸国历代君统覆灭之远因近因,亦恒在此,此无一而不犹吾国也。每读近世史,至屡次之日耳曼帝位继承问题,波兰王位继承问题,西班牙太后马渣连事件,俄罗斯太后苏菲亚事件,英王查利斯第一事件,法王路易第十六事件,乃至其余种种糜烂纷扰惨酷困难之现象,未尝不叹古今东西政治上之罪恶,何以若出一辙!今则自俄罗斯以外,问诸国犹有以此等罪恶污点其国史者乎?无有矣。中国馆阁颂扬通语,劝曰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若今者英、德、日诸国之群主,真可谓亿万年有道之长也。而不然者,则有若当世专制第一之俄罗斯,而亚历山大第二被弑矣,亚历山大第三以忧死矣,今皇尼古喇第二亦被刺于日本几不免矣。享万乘之虚名,无一夕之安寝,以视英、日、德诸皇何如矣?君主而不欲自爱则已耳,君主之私人而不欲爱其君则已耳,苟其欲之,宜何择哉然则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为君主者,当视专制政体为一己之私仇。彼其毒种盘踞于我本群者,虽已数千年,合上下而敌之仇之,则未有不能去者也。
虽然,若君主及君主之私人而不肯仇彼焉,从而爱惜之,增长之,则他日受毒最烈者,不在国民而在君主及其私人也。
按诸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不相容,则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专制政体之不能生存于今世界,此理势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与理势为御,譬犹以卵投石,以螳当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故吾国民终必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吾敢信之,吾敢言之。而其中有一机关焉:君主及其私人而与民同敌也,则安富焉,尊荣焉,英国、日本实将来中国之倒影也;君主及其私人而认贼作子也,则国民仇专制政体,而不得不并仇专制政权之保护主,法国、美国实将来中国之前车也。夫为英、日与为法、美,在我国民则何择焉,所最难堪者,自居于国民以外之人耳!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君子读史记屈原列传而不禁废书而叹也(新民丛报第廿一期,十一月卅日出版)
释革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
“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
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输然,从根祗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确译也。“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在旧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省文下仿此之意也。人群中一切有形无之事物,无不有其Ref,亦无不有其Revo,不独政治上为然也。即以政治论,则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谓之Revo.者;亦有屡经易姓而仍不得谓之Revo.者。今以革命译Revo,遂使天下士君子拘墟于字面,以为谈及此义,则必与现在王朝一人一姓为敌,因避之若将貱己。而彼凭权借势者,亦将曰是不利于我也,相与窒遏之、摧锄之,使一国不能顺应于世界大势以自存。
若是者皆名不正言不顺之为害也。故吾令欲与海内识者纵论革义。
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其事物本善,而体未完法未备,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经验少而未甚发达,若此者,利用Ref。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有窒于化,非芟夷蕴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则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
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又见乎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大变革,尝馘其王刈其贵族流血遍国内也,益以为所谓Revo.者必当如是。于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谓以仁易暴之Revolution,与中国前古野蛮争阋界所谓以暴易暴之革命,遂变为同一之名词,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然则朝贵之忌之,流俗之骇之,仁人君子之忧之也亦宜。
新民子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
灭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澌自毙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外境界无时而不变,故人事淘汰无时而可停。其能早窥破于此风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进步能随时与外境界相应,如是则不必变革,但改革焉可矣。而不然者,蛰处于一小天地之中,不与大局相关系,时势既奔轶绝尘,而我犹瞠乎其后。于此而甘自澌灭则亦已耳,若不甘者,则诚不可不急起直追,务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与他人之适于天演者并立。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明。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若此考,岂尝与朝廷政府有毫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亦可骇耶?呜呼,其亦不思而巳朝贵之忌革也,流俗之骇革也,仁人君子之忧革也,以为是盖放巢流彘,悬首太白,系组东门之谓也。不知此何足以当革义。革之云者,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今如破而可谓之革也,则中国数千年来,革者不啻百数十姓。而问两汉群治有以异于秦,六朝群治有以异于汉,三唐群治有以异于六朝,宋明群治有以异于唐,本朝群治有以异于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谓之数十盗贼之争夺,不能谓之一国国民之变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数千年来,各国王统变易者以百数,而史家未尝一予之以tion之名。其得此名者实自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役始,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役次之,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役又次之。而十九世纪,则史家乃称之为Revolution时代。盖今日立于世界上之各国,其经过此时代者,皆仅各一次而巳。
而已如吾中国前此所谓革命者,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贵高尚之美名也。故妄从革命译此义,而使天下读者,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则其言非徒误中国,而污辱此名词亦甚矣。
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
若十九世纪者,史家通称为Revo.时代者也,而除法国主权屡变外,自余欧洲诸国,王统依然。自皮相者观之,岂不认为是改革非变革乎;而询之稍明时务者,其谁谓然也。何也?变革云者,一国之民,举其前此之深象而尽变尽革之,所谓“从前种种譬犹昨日死,从后种种譬犹今日生”,其所关系着非在一事一物一姓一人。若仅以此为旧君与新君之交涉而已,则彼君主者何物,其在一国中所占之位置,不过亿万分中之一,其荣也于国何与?其枯也于国何与?一尧去而一桀来,一纣废而一武兴,皆所谓“此朕家事卿勿与知”,上下古今以观之,不过四大海水中之一微生物耳,其谁有此闲日月以挂诸齿牙余论也。故近百年来世界所谓变革者,其事业实与君主渺不相属,不过君主有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有逆此风潮者,则锄而去之云尔。夫顺焉而优容,逆焉而锄去者,岂惟君主,凡一国之人,皆从此道遇之焉矣。
若是乎,国民变革与王朝革命,其事固备不相蒙,较较然也。
闻者犹疑吾言乎?请更征诸日本。日本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自夸耀,稍读东史者之所能知也;其天皇今安富尊荣神圣不可侵犯,又曾游东土者之所共闻也。曾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实食一度Revolution之赐乎?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语及藤田、东湖、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此非吾之谰音也,旅其邦读其书接其人者所皆能征也。如必以中国之汤武,泰西之克林威尔、华盛顿者,而始谓之革命,则日本何从称焉?而乌知其明治以前为一天地,明治以后为一天地,彼其现象之前后相反,与十七世纪末之英、十八世纪末之法无以异。此乃真能举Revolution之实者,而岂视乎万夫以上之一人也由此言之,彼忌革骇革忧革者,其亦可以释然矣。今日之中国,必非补苴掇拾一二小节,模拟欧美、日本现时所谓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也。彼等皆曾经一度之大变革,举其前此最腐败之一大部分,忍苦痛而拔除之,其大体固已完善矣,而因以精益求精备益求备。我则何有焉?以云改革也,如废八股为策论,可谓改革矣,而策论与八股何择焉更进焉他日或废科举为学堂,益可谓改革矣,而学堂与科举又何择焉?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改革云,改革云,更阅十年,更阅百年,亦若是则巳耳。毒蛇在手而惮断腕,豺狼当道而问狐狸,彼尸居余气者又何责焉。所最难堪者,我国民将被天然淘汰之祸,永沈沦于天演大圈之下,而万劫不复耳!夫国民沈沦,则于君主与当道官吏又何利焉?国民尊荣,则于君主与当道官吏又何损焉?吾故曰: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将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始。
呜呼,中国之当大变革者岂惟政治,然政治上尚不得变不得革,又遑论其余哉!呜呼(新民丛报第廿二期,十二月十四日出版)
敬告我国民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
某不敏,谨因正月初吉,寓书于新民丛报读者诸君,冀以间接力得普达于我所敬所爱所恋所崇拜所服从之四万万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