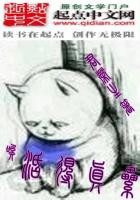特别值得提醒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是以西欧为典型并且从西欧社会的内部矛盾分析出发,来论述西欧的具体历史发展道路的。那么,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是不是一种必然趋势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属于它的低级阶段)是扬弃了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之后产物。在这里,虽然资本主义是西欧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但是商品经济却是整个人类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能逾越的社会经济形态。这样,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有两点就必须清楚,其一是,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反映了以西欧为例而引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二是,共产主义作为对商品经济的否定,则揭示了人类走向更高一级的经济形态的一般趋势。在同一个问题上所包含的两层意思,是混在同一个问题中,假若我们不能在理解中加以辨明,那么我们对这理论的理解就容易陷入简单化而混乱起来。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不仅建立在对西欧资本主义的矛盾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之上,而且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作为西方社会商品经济形式的历史必然性的肯定基础上。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
例如,马克思在写给给维·伊·查利苏奇的复信草稿中,几次表达了:能否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肯定成果”,能否掌握并利用“资本主义生产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对于非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意义。恩格斯在其具有总结性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写道:“只有当落后国家”,“看到怎样把现代化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富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
还例如,恩格斯在当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们幻想社会主义已经近在眼前的时候,就曾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作为商品经济形态的一种历史形式所具有的必然性,并揭穿了他们的历史唯心主义实质:“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段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
如果我们抛开上述经典作家论述的一些枝节而抓住其精神实质,就会体现到如下两点最为主要,即:第一,向共产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形式并不是必然的形式;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形式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商品经济的成熟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历史前提。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同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不是从普遍的正义、理性和一般道德出发,而是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马克思终于揭示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最伟大前景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的思想是清晰的、明白的、前后一贯的。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实社会主义却为什么与马克思的原来设想不同呢?
这个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很高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却恰恰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而整个社会仍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的;其二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经济之后的崭新社会形态,而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却恰恰是谁否定商品经济谁倒霉、谁无视商品经济谁吃亏,它仍然处在商品经济时代。这一切如何解释呢?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不同,但是人们却往往又从两种极端的方式中寻找答案。
一种方式是按照如下的思路完成的:即,既然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大工业生产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无法克服的斗争基础之上,而中国既无发达的生产力作基础,又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那么中国就没有资格建立社会主义,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人为的产物,从而主张,中国应该退到民主革命阶段,发展资本主义,而当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再建立和过渡到社会主义。而这一思路的附属观点则是,中国应该按照人类的正常规律办理,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它是推崇现代西方社会模式结构的理论根源之一。
另一种方式的思路则是:既然马克思所预见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经济之后的崭新社会经济形态,既然马克思讲的是生产社会化程度的高要求,那么,中国为了坚持社会主义从而也是为了坚持马克思,就必须确立我们社会的计划经济性质,就必须彻底铲除或者尽快铲除商品经济。不仅如此,既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那么,为了坚持社会主义从而也是为了坚持马克思,我们就必须将资本主义视若仇敌,是水火不相容、冰炭不能同器的关系,必须将资本主义的全部痕迹消除掉!
前一种思路的结果是否定了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性质,后一种思路的结果则是用一种抽象的理论规定了中国的现实。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两种思路的背后竞争隐藏着同一个理论出发点,这就是欧洲中心主义及其五阶段单线发展模式!
何以然?
第一种思路的情况显然易见,它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就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而重新经历一下资本主义。惟如此,似乎才能创造和积累起为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但这一切,又恰恰是西欧模式所提供的经验。这一种思路仅仅是知道共产主义否定的是作为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而不明白它可以把资本主义作为商品经济的一种社会形式而加以否定,所以在实际上,它的思考中,其理论参照系不是三大形态的不可逾越性,而是五阶段的不可逾越性,而这一点,却正是马克思所表明反对的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那种情况,这正是把五阶段理论夸大为普遍法则的典型例证。
第二种思路的情况虽然复杂一些,但其理论出发点却完全一样。这一思路首先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等同,于是,否定资本主义就必须否定商品经济便成为一个问题了。然而,这一思路恰恰不明白,在实现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方式之外,还可能存在着其他的方式,这样,它便将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自然看成是也否定了商品经济之后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思路在坚持单线模式时虽然没有第一种思路那种“历史感”,但由于它把资本主义看成了商品经济形态阶段上的惟一社会形式,所以仍然是一种五阶段单线发展模式的派生物。
可见,不冲破一元文化发展观及欧洲中心主义和五阶段单线发展模式的框子,我们是很难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的。
情况正是如此。如果我们站在多元文化系统观的立场上,问题便很容易理解。
一方面,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和联系性,使人类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不能超越其三大形态的依次递进的发展规律,从而共产主义将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但是,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生活在各不相联系的历史土壤和环境之中,所以当它度过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时,完全可能采用不同的社会形式,这是由于多元文化所造成的。例如,在原始的自然经济时代,可以有西欧的形式,可以有日耳曼的形式,也可以有日本的形式;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时代,可以有欧美的资本主义形式,也可以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形式,等等。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偏执地坚持人类的商品经济形态阶段上只有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呢?为什么就可以以为否定了资本主义就是否定了商品经济呢?
当然,这里也可以不客气地指出,在对未来的共产主义作出展望的时候,马克思不仅往往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解为一回事(只在低高级阶段上加以区别),而且由于历史的局限,也不可能具体地规划和测定出现实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所能解决的课题,我们不能苛求于他,然而,这一切又怎么可能作为阻碍我们具体地理解马克思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由呢?
十分明显的是,只是由于我们的教条主义思维方法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心理特征,才造成了既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又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情况;才造成了要么企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拉向倒转,要么企图主观地超越商品经济这一无法超越的历史时代的情况;才造成了既歪曲马克思,又歪曲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把中国拉向倒转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反对商品经济却有它的政治土壤和历史土壤。然而,中国跨入近代以来,太平天国试图消灭商品经济,结果仍然回到封建自然经济怀抱,而解放了的中国也企图否定它,结果是国家贫穷人民受苦吃大亏。
历史以它的严峻性和无情性宣告,规律是不容违背的。
中国人民终于在沉重教训中清醒过来,开始了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的历史。党中央终于代表整个民族在深刻的历史反思之后宣布,中国现阶段处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
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突破,而且是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把握。中国在曲折的道路行进中虽然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经验,但也确实背负着各式各样的包袱,中国唯有坚持改革才能振兴,中国也唯有在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才能最后奔向共产主义。
中国需要通过改革才谈得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应该在不断的改革中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人类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