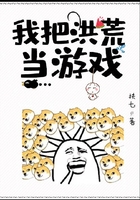我不知怎样去诠释世人,其中一个我也无法参透。我从小便生活在这个城市,起伏跌宕。城市就像一个大骰盅,人们犹如被罩住的一粒粒小小的骰子,被它摇来晃去几十年,最后开盅时拨开纷乱的骰子堆我竟然是个一点,当然也有可能是六点。我羡慕公园里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他们的意识里永远有一个无须感伤的未来,尽管这未来不可预测。我也天真无邪过,而当我们回首过去时,许多欲哭无泪的理由都竟告阙如。
火车踩着我的心跳声开动了。我第一次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选择暂时离开A市。窗外阳光明媚,A市的一切景象开始后退,我靠在座位上一会儿便睡着了。醒来时已经是深夜,车窗上布满水线,下雨了。远处灯火点点,才明白已经独自一人身处他乡。
肩膀上靠着一个妙龄少女,短短的秀发,脖子上挂着一个长方形的正面刻着梅花的小玉坠。那玉坠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来还有谁戴过这样的玉坠。少女呼吸平衡,我想是真的睡着了,也有可能是假装的,反正我不会喜欢她。呵呵!适时的臭美,让我心情开朗很多。不过,她的雍容给我一种奇怪的反感。
再次闭上眼已经睡不着了。无聊之极,我从随行的背包里拿出课本随便翻看了起来。看着看着,睡意袭来,肩膀一低,两头相撞。少女醒了。她摸着额头,盯着我的书,似乎惊讶于半夜火车上我坐在美女身边还能读圣贤书。我不理会她,我不是假正经,我得消磨时间。她忽然问我:“你凭什么撞我的头?”我觉得她问得很弱智:“你不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我睡着了怎么会撞到你的头?”她纤细的食指指着我的鼻子:“你——”我抢白她:“你什么你?要不我靠你肩上,你再撞我一下?”她指着我鼻子的右手握成拳头,看来是想揍我。这时“叮叮叮……”的声音响起,她白了我一眼,不知道从哪个兜里掏出一个金光灿灿的手机打起电话来。南方口音,滔滔不绝,吐沫横飞,她的旁若无人的境界让周围的人都频频的拿眼神鄙视她。噪音中天色渐渐的亮了。少女说的什么话我一句没听进去,我想如果她不是说而是写下来的话,也是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长篇了。
事实上,我打过很多次架,骂过很多人,但我从来不对女的施暴,我只英雄救美。不过,我还是苦思了好几个方案:一,冷不丁的把书敲在少女的脑袋上,然后站起来撸起袖子瞪着她,耍暴力她不是我的对手;二,把她的手机夺了,扔到一边去或者砸掉,她气不过要武力解决便正中下怀;三,霸王硬上弓,翻身按住她,吻住她的小嘴,让她无法再开口……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只是到忍无可忍时自己所准备的一切报复手段往往都全无必要。当我正在犹豫要不要执行我的计划、执行哪个计划时,列车员叔叔推着餐车过来了。“稀饭—咸菜—包子,美味可口的早餐啦!十块一份。”少女坐在走道那边,餐车上餐盒堆得老高,餐车经过时好像磕到什么东西后失去了平衡,最上面的几份美味可口的早餐全部泼洒在少女曼妙的身段上。少女和周围的人包括我都愣了一下,接着,史上最高分贝的尖叫声诞生了。不难想象少女会不依不饶的和勤快的列车员叔叔大吵大闹,术语叫做口角。我不关心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只注意到周围的几个人脸上的阴笑像刚吃过美味可口的早餐那样灿烂。于是,我立马取消了所有计划。
火车一站一站的过去。车厢里的噪杂声掩饰不了我那颗不安的心。
我一点也不想吃东西,甚至反胃、想吐。“美女让一下,我要上个厕所。”少女这时倒变得礼貌起来,把一双秀腿撇到一边。我在厕所里呕了半天,没吐出来一点东西。回到座位上浑身还是不舒服,到后来简直头晕目眩,假如这时少女找我单挑的话我只有任她宰割。渐渐的,我又睡着了。醒来时,脑袋里像装了铅,抬不起头。眄视身边的位子已经空掉了,少女应该早就下车了。我大吃一惊,忙问身边的人D市过了没,大家说没过才放下心来。
我不是第一次坐火车。逢年过节的时候我经常陪着妈妈坐火车到外婆家去,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中午时分,火车终于停在了D市。我背起包,蹒跚着走下火车。
D市是个小站,下车的人寥寥无几。雨淅淅沥沥的下着,阳光躲在云雾里。我没有带雨伞,加快脚步奔向出站口。检票口对面人影晃动。穿过栏杆我踏进陌生的土地,搜寻曾今熟悉的身影。这时我看到了她。她立在人群的最后面,着一身淡青色的夏装,左手举着一把撑开的蓝色雨伞,右手向我挥动着另一把红色的雨伞。画面再清晰不过,我抖擞精神向她奔过去。
我本来想好了,见面时要来个拥抱,可是我刚冲到她面前,她便把红伞递过来,给我的感觉像是一把剑抵在胸口。“喏。别把衣服淋湿了。”她出乎意料的憔悴,表情冷漠,言语中没有一点激动。我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接过伞却无力撑开,只知道傻傻的看着她。片刻后,她把伞举高,完全的露出她的脸,她盯着我的眼睛向我走过来,等白伞勉强可以遮住两个人的头顶时,苏寒笑了起来:“才一年多没见,你就忘了我了?”这笑容如旧,我像被闪电击中,立刻清醒过来。“你过的不好么?”我脑子里没有任何杂念。苏寒没有回答的我的问题,而是咳了两声:“我感冒了,这一把伞遮不住两个人。”我尴尬的撑开红伞。要知道我从来没有在苏寒面前发窘。
“你来看我的事,告诉阿姨了么?”苏寒知道我什么事都是先和妈妈商量。
“没有。我住学校宿舍,我请假来的。”我惊讶于自己为什么在“没有”后面加一句解释,好像生怕她有所误会、担心,难道这就是自己长大了的表现么?
“我弟弟过得还好吧?”
“嗯。挺好的,比你壮多了。他有时候叫我去他们学校踢球。”
苏寒还欲再问。我突然萌生了回归旧日的感觉以及由此爆发的勇气,我打断她的话:“我饿了,让我吃了再说吧。”
D市给我的感觉像五年前的A市,火车站前的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座锈迹斑驳的铜塑马。没有高楼大厦,店铺林立,街道拥挤。我跟在苏寒后面,穿梭在大街小巷。在一幢大概八层楼高的蓝色玻璃建筑大门前停下,楼层从上到下四个镀金大字——明月商场。苏寒说:“我在六楼的kappa专卖上班,今天我休息。一楼有餐厅,我上班的时候就在这吃午饭。”我仰望建筑物,计算六楼大概在什么高度,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已经被苏寒拉到餐厅一旁的位子上坐下。她说:“梓原哥哥,想吃什么?”“哦——随便。”我从来不反对别人尽地主之谊,拉拉扯扯应该吃什么、抢着付钱的样子足以打消食欲。
苏寒把伞靠在桌子旁,到斜对面不远处的窗口去了。不一会儿端了满满一大碗东西朝我这边走过来。那瓷碗是我喜欢的青花瓷样式,苏寒端着的样子似是举案齐眉。我猜想碗里是什么食物,盖浇饭?牛肉面?还是麻辣烫?这些食物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想着苏寒上班的时候都会在这里吃这样的食物便心痛不已,虽然之前在A市吃得不见得比现在好。她比小时候还要消瘦,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D市显然不是苏寒的福地。
苏寒把碗放在我的面前,是刀削面。有香菇、肉丝、蛋白,没放辣椒。“饿了吧!加了鸡蛋,去了蛋黄的。”“你怎么不吃?”“你说十二点半到,我十一点在家吃过中饭来的。”苏寒所说的家是她和萧建组建的家。他们离开A市不久后就结婚了,婚礼是在萧建老家所在的D市郊区的一个叫梅花镇的地方办的,苏寒的外公外婆还来祝贺过。苏宏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我清楚这不是苏宏的主意,我对苏寒这样的安排着实恼怒过,我甚至怀疑萧建从中作梗。“萧建人呢?他是怎么照顾你的?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苏寒坐在我的对面,见我提到萧建,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弄得我也没心思吃东西。
“阿建——死了。”
这四个字的意义被我理解后,让我浑身不是滋味。我皱着眉头直视苏寒的脸,她下颚轻微的颤动。我体悟到离我半米远的这个女人真是命苦。事实上,我还是挺佩服萧建的,他能把苏寒追到手,而且还结了婚,这样的人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死掉了。抛弃了自己新婚不久的妻子(我不知他们有没有孩子,有的话应该刚出生不久,苏宏没有告诉我,我也没问过),年迈的父母。虽然死亡或许不是萧建自己可以控制的,但我还是觉得他很无情、不负责任。活人不能对死人追究什么,活人可以挽救活人。我把视线收回来。我不知道该对苏寒说什么,说“节哀顺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之类的么?我不会说如此薄情寡义的套话,她妈妈死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劝过她。那时,她简直成了一个呆子。她弟弟一个星期后就好了,唯独她哭啊闹啊的,后来睡在床上昼夜不起了。于是我每天都弄些钱,给他爸买烟,然后到她的床前奉上好吃好喝的,给她讲学校最近发生的事,讲她的理想,讲我们的未来……
我嘴中的半个蛋白没有及时咽下去。苏寒死了丈夫,或许还有孩子,我该怎么去挽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