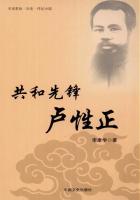客观真实、具有电影风格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一百页左右的篇幅里再现了50年代哥伦比亚的政治氛围。小说情节简单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主人公上校为一封信等了十五年,他相信这封信很快会到,能带给他发放退役军官养老金的消息。小说主要内容是描写上校和老伴——无名无姓,就是“老伴”——在保持尊严的前提下,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故事时间跨度不长, 50年代某年的10月至12月(可能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1956年,因为小说中两次提及这场危机;见第25页、第41页)。无所不知的第三人称叙事者并没有直接提供细节,而是读者被故事吸引,根据对话所透露的信息,逐渐勾勒出人物生平的轮廓。我们很快就发现,上校和老伴因为失去儿子阿古斯丁而深受打击,而后其死因逐渐透露,原来他卷入反政府活动,并且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部中篇小说最无从捉摸的,不是出现在书名里的那封信,而是上校家的公鸡:尽管他和老伴已经无异于在慢慢饿死,上校依然拒绝把公鸡卖掉。公鸡有象征性的价值,除了有不吉祥的含义,让人联想到死亡之外(第71页),还让人联想到左派意识形态、老两口死去的儿子(公鸡曾经是阿古斯丁的)、人们对更加光明的未来的期盼(小说快结束时提到的“幻觉”,第70页)等等。这样,公鸡就代表了人们生存下去的决心,虽然他们面对的是最卑鄙的政治压迫。《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主题,正如鲁文·佩拉约所言,是哥伦比亚权势阶层的腐败。还在巴黎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一直在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诚如杰拉德·马丁所言,在某个层面上,这部小说以虚拟的形式,对他当时与西班牙女演员塔奇雅相恋时真实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再创作。同样重要的是,小说带给读者“等待”的强烈感觉。马尔克斯无异于创作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哥伦比亚的戈多形象:“他坐在燃烧的泥炉子旁边,等着茶水煮开……这时,上校觉得好像内脏里有毒蘑菇和百合在生长。这是十月份。”(第56页)蘑菇和百合在他身体里生长,这个怪诞的意象当然会让我们联想到马尔克斯早期作品中对死亡的特别关注,但是对马尔克斯来说,这也是十分有个人特色的意象。在T. S. 艾略特看来,四月份是“最残忍的月份” ,然而在属于马尔克斯个人的象征库里,与死亡、厄运还有茶壶(pava)联系在一起的总是十月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上校显然是作者的化身(他们都在等待永远没有寄到的汇款;都感觉到好像已经死了;都讨厌十月份)。小说的意象构成是多层面的,正如马尔克斯所指出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出发点,是一个在巴兰基亚市场等着看轮船下水的男子,默默的,有些焦急;多年以后,在巴黎,我发现自己在等待一封信——很可能是汇款——同样有些焦急,这让我觉得跟那个记忆中的男子很相似。”当然,还有童年记忆:记得当年外公参加1899至1902年的千日战争之后,很多年来一直等待着领取退役军人养老金(见本书第1章)。第三个层面是政治上的讽喻,小说其实也是关于哥伦比亚的政治紧张局势,尤其是暴力冲突所带来的恐怖,这从小说中的只言片语可见一斑,例如上校的评论,“这次丧礼可是件大事儿呢……多少年了,头一回有人自然死亡”(第11页);此外还有他们的儿子阿古斯丁未加解释的死因。在第四个层面上,小说受到德·西卡的影片《翁贝托·D.》(Umberto D.)的影响;跟加西亚·埃斯皮诺萨和蒂顿一样,马尔克斯这个时期小说的创作风格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小说带有自传成分,作者写作时的个人经历也是不可忽略的影响,马尔克斯把他与塔奇雅之间的关系写入了小说的某些细节。 这就是马尔克斯小说的绝妙之处,其创作源泉至少有五个层面,包括(1)令人难忘的视觉形象;(2) 童年记忆;(3)写作时的生活细节;(4)用某种文学技巧来构建小说,换言之,将这种技巧变为艺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技巧受德·西卡的启发, 50年代早期的灵感则来自卡夫卡);以及(5)借助文学隐喻而产生的政治讽喻,通常出现于看似无意的只言片语,其实是冰山一角。这五个层面相互交织,紧密相连,只有精密的刀锋才能将其剥离,正所谓 “无斧凿痕方为真艺术”(ars celare artem);例如,塔奇雅的人工流产, 不可思议地与自由党事业的失败联系在一起(两者都涵括在已经死去的儿子阿古斯丁身上);这就是为什么马尔克斯的小说总是让人有一种真实感,因为其中有五分之四的真实和五分之一的虚拟。唯一的难题是,真实从来不是某个单一事件,而是四个真实情景在美学上通融交汇所产生的一个艺术层面。这既是真实的,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一篇艺术力作,在一对老夫妻的日常生活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狭窄的框架里,作者成功地嵌入了国家命运的寓言画卷。确实,马尔克斯这个时期(50年代中后期)小说作品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刻画哥伦比亚潜在的政治怒火,用安赫尔·拉马的话说,这个国家“生活在旷日持久的暴力状态,不是公开暴力,就是暗藏的暴力威胁” (笔者译)。 短篇小说《大妈妈的葬礼》是拉丁美洲政治讽喻文学的开山之作,其中主要人物,是个被恰如其分地称作“大妈妈”的女人,马尔克斯借用大妈妈的葬礼,讽喻拉丁美洲后殖民时期怪诞的政治现实。小说创作于1959年5、6月间,也就是说,几乎可以看作是对古巴革命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作出的直接回应。开篇伊始,似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是政治讽喻小说,但是大妈妈掌管的事儿被一一罗列,她的权力是如此之大,读者不难看出,这是对始于西班牙征服者,并且延续至今的权迷心窍和滥用权力的讽喻;当这部小说在60年代被更多的人注意到的时候,公众的反应只能用“革命性的”来描写。所有细节——尤其是关系到大妈妈占为己有的、各种物质或者抽象的东西——渐渐使故事的叙述变成了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例如:
地下资源、领海、国旗的颜色、国家主权、传统党派、人权、公民权、公民自由、首席法官、第二轮审判、第三次辩论、推荐信、历史证据、自由选举、选美王后、传统演讲、壮观的表演、尊贵的年轻女士、正直的绅士、军事荣誉、杰出的贵族、最高法院、禁止进口的物质、放任的女士、性欲问题、语言纯洁问题、在世界上树立榜样、法律秩序、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南美洲的雅典、公众舆论、民主选举、基督教道德、硬通货短缺、避难权、共产主义的威胁、国家库存、高额生活费用、共和党的传统、弱势阶层、表示支持的信息。
所有这一切大妈妈真的能拥有吗?由于没有任何持异议者的声音,拉丁美洲的地方政治首领巧取豪夺,擅权专利,对此还有比这篇小说更加怪诞、更具讽刺的描写吗?在拉丁美洲,寡头政治国家政权的法令将权利、特权和禁忌搅合在一起,有哪一个作家曾经如此毫不掩饰地揭示这种状况在实质上的空虚无聊?既然没有来自国会另一半的“皇家异议”,甚至也没有来自下层的声音可以倾听,大地主们(latifundistas)就可以擅自获取特权、权利和其他任何东西,好像他们是上帝似的。鉴于小说写于1959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肯定是借此攻击拉丁美洲殖民统治怪诞的独断专行,因此,虽然没有明说,却也间接表达了支持古巴革命所代表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怀。其实,《大妈妈的葬礼》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封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自我介绍信,对卡斯特罗在60年代那令人兴奋的年月里所代表的一切,表示热烈的支持,因为小说讽刺了拉丁美洲征服者,以及他们在“西班牙裔”(criollo)拉丁美洲的继任者,揭露了他们所占有的权利与特权的荒诞本质。我们当然可以从小说中挖掘出对拉丁美洲历史的反殖民激进解读,然而,这种解读也绝不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能会被认为是历史主义批评学派的过分先入为主。尽管如此,激进的解读是一种潜在的解读,影响着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另一方面,小说还可以有其他解读,比如说,对热带地区昏昏欲睡状态的刻画。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曾经说过,小说为读者提供了“现实世界的一种一成不变、具有排他性的图景”。罗宾·菲迪恩分析比较了马尔克斯在这部小说和其他50年代中后期作品中对“单调结构”的描写,认为“能使人联想到罗西里尼和德·西卡”。当然,在一些特定的圈子里——可能是60年代早期的古巴,或者法国、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或苏联统治集团——有人见到如此显而易见的政治讽喻,会心照不宣地暗自得意;不过,我们还是暂且将其看作是在政治上或者其他方面有若干特定意义的小说,任何一种意义都未必是作家预先设定或者刻意嵌入的。 短篇小说集《大妈妈的葬礼》表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可以带给读者强有力的视觉形象,过目难忘;对话简洁精彩,描写精确到位,擅长营造氛围。例如,《礼拜二午睡时刻》(“Tuesday Siesta”)的第一个段落展示了精心挑选的细节(整齐对称、无边无际的香蕉种植园;扑面而来的风,随着火车从海边往内地行驶,越来越弱;吊着电风扇的办公室;棕榈树),在读者脑海里形成生动的视觉图像。小说很少评论,叙述像相机镜头一样客观,这就让读者目睹事件的展开,慢慢地才能体会到其重要性——我们随着一位无名女士和她同样无名的女儿,经过一段旅途,去悼念试图入室抢劫时被杀死的儿子,抢劫现场是蕾维卡的家,弄清楚这些情节,小说已经过了一半。对话十分简洁,冷嘲热讽,令人啼笑皆非,其中一段堪称马尔克斯的对话佳作。女人告诉神父,她每吃一口东西,都能尝到牙齿的味道,是儿子为了养活她所敲掉的牙齿,神父说:“主的意愿高深莫测。”(第119页)《此镇无贼》(“En este pueblo no hay ladrones”)的结尾峰回路转,出人意外,罗克透露,他一定会要达马索归还跟台球一起“被盗”的两百“比索”(第125155页,第155页)。 这些短篇小说像简短精美的小品文,犹如幻灯片一样反映了哥伦比亚香蕉产区的生活,放在一起看,会更加有意思。比如,在《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La prodigiosa tarde de Baltasar”)里,巴尔塔萨没等何塞·蒙铁尔的儿子付钱,就把笼子给他了(第156164页,第163页),看起来是得不偿失; 但是,如果跟《蒙铁尔寡妇》(“La viuda de Montiel”,第165172页)放在一起看,我们就会明白,巴尔塔萨其实是占了上风。原来,蒙铁尔是个罪恶的暴君,以前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在他家里向他发号施令,因此,《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是受压迫的人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得胜的故事。通过不要对方付款的举动,巴尔塔萨解构了资本主义。这些短篇小说还像望远显微镜一样,让我们看到马孔多世界的浮光掠影;五年之后,这个世界将整合出现在《百年孤独》的框架中。在《周六后的一天》(“Un día después del sábado”)里,我们看到在蕾维卡家里死去的贼,就是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上校的哥哥(第173197页,第181页),我们会在《百年孤独》里再次遇见他。有些故事没有确切的结局,比如《蒙铁尔寡妇》《周六后的一天》和《纸做的玫瑰花》(第198204页),好像这些短篇小说是作家的练笔之作,在为写《百年孤独》而磨炼叙事的艺术。 这个短篇小说集子里的杰作是《某日》。罗宾·菲迪恩注意到,这篇作品是“1958年3月份前”写就的。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出现政治讽喻最清晰的例子。小说长度不到四页纸,写的是牙医奥雷良诺·埃斯科瓦尔和镇长(没有名字)之间喜剧性的对抗,但是故事所展示的却是更大的画面。埃内斯托·博尔肯宁指出:“牙疼带有形而上的维度,迫使作为暴君的病人直面自己孤家寡人的悲剧。”牙医迫使镇长同意在拔牙时不用麻药,并且在把牙拔出来的时候说道:“中尉,这颗牙偿还了你欠下我们的二十条人命。”这句话告诉我们,镇长压迫民众,肆无忌惮地杀害了二十个政治对手(“自由派”的牙医与这些人是同一条战线的)。小说艺术的绝妙一笔出现在故事夸张的结局处(第26页):
“把账单给我送过去。”他说。
“送你家还是送到镇议会厅?”镇长根本没抬眼看他。他关上门,透过铁格栅说:
“没什么区别。”
这就有如象形符号,在无法无天、腐败和国家政权之间画了等号,撕开了国家话语修辞的面纱,这样的话语从西班牙征服殖民地开始,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如此简洁明快的妙笔足以让T. S.艾略特之辈汗颜——拉丁美洲的政治讽喻就诞生在这短短的三十一个单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