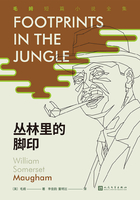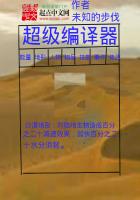张瞎子用细长的木棍探着路走出了家门。他得知韩世昌下世后,皱纹堆垒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块粗糙的木板,只轻声说了一句话:“早死早脱生啊……”随后就躺在土炕上沉浸在无光的世界之中了,直到今天才肯走出来。
张瞎子慢慢走着,高万生从对面走过来。
面对给师父和自己弹了几十年弦子的张瞎子,高万生恭谦地大声说:“大伯,有些日子没见着你了,你身子骨儿还不错嘛!”
张瞎子听出高万生的声音,站住,苦笑着说:“我呀,还就是这副身子骨儿好,阎王爷总也不叫我。我是个废人,不像你师父是个大能人,只可惜他走得早,不等我这个老伙计。他这一辈子,除了乐亭大鼓,什么都没留下。世上艺人苦,艺人里你师父苦哇。不说这些了,说起来我伤心哪!”
高万生说:“我不会像我师父那样穷一辈子、苦一辈子的。”
张瞎子摸索着拍了拍高万生的肩膀,说:“万生,你可得给你师父撑门户啊,韩世昌乐亭大鼓这杆旗可不能倒哇!”
高万生话里有话地说:“什么大徒弟不大徒弟的,我可扛不起您说的那杆大旗呀,竖大旗的事得靠我师弟了!不过话说回来,竖不竖旗,我都得把乐亭大鼓唱下去,这是我师父的命,也是我的命啊。哦,我这儿有十块钱,您拿着,是我当小辈儿孝敬您买点心吃的!”
“万生,我……”
高万生不等张瞎子说话,把钱塞进张瞎子手里,向前走去。
张瞎子摸着钱,听着高万生走远的脚步声,感动地自言自语道:“世昌啊,老哥们儿,你大徒弟有人心哪……可他说的话我怎么听着有点儿别的味儿呢?”
张瞎子思忖片刻,向城外走去。走着走着,一阵茶香飘过来,他知道这是到万和茶楼了,过了茶楼就快出城了。
万和茶楼分上下雅间和大堂两层,不大,但很雅致,颇有茶风。老板娘秦梅红是一个刚交四十的寡妇,她嫁过两个男人,都命短,有茶客暗地里说她命相不好,枉长了一副好身材和好脸蛋。秦梅红确实是一个标致的女人,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弯月似的眉毛,黑灵灵的大眼睛,光洁高翘而又小巧的鼻子,红嫩嫩的嘴唇,无可挑剔的五官配上颀长的身材,使她周身自然地既洋溢着成熟妇人撩人的风韵又不乏青春少女的魅力。
“高挑龙帘挂金钩,隋炀帝无道又下扬州。文官上殿来保奏,武将上殿把主留……”秦梅红在大堂里边小声哼唱着乐亭大鼓边擦抹着桌椅,她很喜欢这段《隋炀帝下扬州》,也知道高万生唱得拿手。此刻,她的茶楼里有一个特殊的客人。
秦梅红正忙着,三十多岁的伙计大春走过来,小声地说:“梅红姐,二楼雅间里那个小鬼子也不怎么喝茶,一遍又一遍听那个大喇叭筒子放东洋歌儿,还直哭呢。你说他哭什么?他们漂洋过海到咱这儿定杀人放火都不眨眼睛,听着歌儿乱哭个什么劲儿?”
秦梅红停住擦桌椅,甩了几下抹布,也小声地说:“大春,记住我的话,他喝茶咱就卖他茶。他不糟害咱们就是好造化了,你管他是哭是笑干什么?”
大春点点头说:“他栽阴沟里摔死才好呢,谁有闲心管他哭天抹泪儿的?我是说他那个大喇叭筒子有意思。得了,我忙我的事去吧!”
二楼雅间里,白洋县日本驻军司令官福冈身着日本便服边听留声机边擦眼泪,留声机放的唱片是日本民间小调。他就是那个特殊的茶客。
唱片放完,福冈关了留声机,神情阴郁地走出雅间,下了楼,把一张钞票放在柜台上,出了茶楼。
大春从楼上下来,对站在柜台里的秦梅红说:“这杂种蛋子,把那大喇叭筒子寄放在咱这儿了,咱还得给他看着!”
秦梅红收起钱,说:“看着东西总比看着人强,你不知道,他不光爱听他们日本歌儿,还会唱乐亭大鼓呢,前天我亲耳听到他哼了几句,唱的是韩世昌的《单刀赴会》呢!”
“是吗?这鬼子,真他妈怪!”大春把空茶壶放在柜台上说。
这时,坐在离柜几尺远的茶桌前的一个茶客搭了腔:“这有什么怪的,日本人能喝咱的茶,就不能唱咱的大鼓了?”
大春定睛看了看那名茶客,笑着说:“哟,我认得你,你是韩世昌的大徒弟高万生,我听过你们爷们儿的大鼓,地道!”
听着大春发自内心的恭敬话,高万生心里荡过一丝得意,微笑着端起茶杯轻呷了一口,然后又轻轻放下。一副名家的派头。
秦梅红以前听过高万生唱乐亭大鼓,那是在书场上站在人群最后边,从没近距离见过他,所以高万生到茶楼里喝茶有一个多钟点了她也没在意,听了大春的话才认真看了他几眼。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个和他师弟齐兆鸣一样有名气的艺人身上有点让人说不清的东西,尽管作为乐亭大鼓的喜好者,她内心里有些崇敬他。
来了几名茶客,大春招呼茶客去了。
高万生依然悠哉游哉地喝着茶,但他心里却堵着一团乱麻,《尚雅籍》出乎意料地落到齐兆鸣手里这件事成了他的心病。一想起这件事他就很气恼,但又无从发作。在他看来,师父到头来并不和自己这个大徒弟亲,否则就不会把那么重要的《尚雅籍》传给师弟了,这怎么能让他心里安稳呢?《尚雅籍》是师父一生唱乐亭大鼓的精华所在,齐兆鸣得到它看通了一定会在技艺上超过他——他心里清楚,别看自己早齐兆鸣一年学艺,但二人的功底差得并不太多,很难分伯仲。他期待着齐兆鸣能够明白事理,主动把《尚雅籍》交给他这个师兄,这也是考验齐兆鸣心里尊敬不尊敬他的机会……猛地,高万生想:就在自己喝茶的同时齐兆鸣兴许在看《尚雅籍》呢!
高万生想错了。此时的齐兆鸣没有在家中看《尚雅籍》,而是到白洋县城外去看师父了。
齐兆鸣先是跪在韩世昌的坟前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神情庄重得和当年拜师仪式上一样,随后,他边用随身带来的扫帚轻轻掸扫着坟墓上的浮土边说:“师父,我陪您说话来了……”
齐兆鸣身后传来张瞎子苍凉的声音:“我也来了。”
齐兆鸣惊讶地扭回头:“大伯?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张瞎子紧走几步,来到齐兆鸣身边,动情地说:“兆鸣侄子,我和你师父在一块儿混了好几十年,别看他躺在地下了,我也能闻着他身上的味儿。老伙计,我大你几岁,要走也应该我先走,老天爷没睁眼睛啊!”
齐兆鸣哽咽着说:“大伯,您这样说师父他老人家会不高兴的。师父大鼓唱得好,您弦子弹得好,往后我还得靠您多帮衬呢!”
张瞎子面对着齐兆鸣,枯瘪的眼里涌出了清亮的泪水:“兆鸣侄子,有句话我得告诉你,你师父他临去前还真说过让我多帮衬你的话,他不光跟我说了这话,就连想把《尚雅藉》传给你的话都跟我说了!”
齐兆鸣激动地说:“师父对我恩重如山,我结草衔环无以回报,我对天发过誓了,一定保存好《尚雅藉》,绝不让第二个人过手!”
张瞎子使劲点了点头,却随即叹了口气,说:“《尚雅藉》是一本奇书,传到你手里也许是好事,也许……”
说到这里,张瞎子停住了话头,但话里分明有难言之隐。齐兆鸣不解地问:“大伯,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千万别留半句啊!”
张瞎子沉吟了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咱们虽然有交情,可是照比你们师徒、师兄弟我终究是外人,有的事情我不好说,你好自为之吧!”
齐兆鸣思忖着说:“您是说……”
张瞎子摇摇头,示意齐兆鸣不要往下说了。他伸出手,摸着坟头上的青石,感慨地说:“老哥们儿,你走了有兆鸣给你上坟、守孝,赶明儿我闭了眼睛恐怕连个填坟的人都没有啊!”嗓音里透着无尽的苍凉。
齐兆鸣疑惑地望着张瞎子,因为他知道张瞎子有一个儿子,名叫张汉虎,但不知今天张瞎子为什么这样说,便问道:“大伯,我那汉虎兄弟……”
张瞎子难过地说:“前年离家自己闯荡去了,至今连个信儿也没有。唉,他成龙成虫只能任凭天命了。”
齐兆鸣真诚地说:“大伯,大娘早走了,汉虎兄弟又不在身边儿,您一个人太苦了,您要是不嫌弃,就住我家去吧,您是我师父生前的挚交,也是我的长辈,我给您养老送终!”
齐兆鸣话语使张瞎子身子一颤,他连忙摆着手说:“那可不行,我这个废人怎么能到你家里去添乱呢?”
齐兆鸣握住张瞎子的手,说:“大伯,我已经说过了,您不是废人,您手头儿功夫好,也不白住我家,等我守孝期满就登台唱大鼓,到那时我可离不了您这把弦子啊。您刚才也说了,我师父生前把我托付给您了,侄子我求您了!”
张瞎子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辞了,颤抖着嗓音说:“兆鸣侄子,你好仁义呀,我这把老骨头就是你的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唱大鼓,我就豁出命给你掌家伙!”
齐兆鸣重重地点着头,再次握紧了张瞎子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