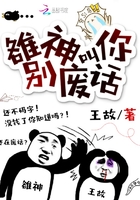离开时,李睿晟的房间已经披上洁白的棉麻罩布,清洁冷清得像他没有来过,只有程虹雨立在花园门口同我们招手送别。今天的天气不好,阴郁着,她穿着一件灰色棉布的裙子,站在周围一片热烈的月季当中,更显出萧条与孤寂。
“虹雨,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我心里略感抱歉,她也满心欢喜的来,没几日光景就孤零零一个人了,“要不是我,你们还很热闹的呢……”
“南京有事,我肯定要回去的,只不过早跟晚的区别,我走了睿晟肯定得走,至于你嘛,确实对她是个伴,但是你走了也没事,早先就只有她一个人打算来。”他懒洋洋地转动手中的方向盘,车子沿着山路稳稳当当地向山下盘旋。
“她一个人在这屋子里,不冷清吗?”我又回头,那法式的小楼已经消失在绿意盎然的树林之后。
他轻笑一声,“不还有佣人吗?去别人家也不远,她都认识。而且就算真就她一个人待着,她也是巴不得的。”
她这么想一个人静静?这还是我看见的在舞会里招蜂引蝶、人群簇拥的程虹雨吗?我又想起那次在夫子庙,她局促地在那妇人与男子身边陪着,比人家女佣而低三下四的模样,看来她在南京的日子没有表面这样光鲜。转头看程昊霖,他紧闭了嘴,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把家里隐秘的事情暴露出来。
下了山,乌云背后,还是能感觉到灼热的阳光。我隐约觉得这是迎着太阳在行驶,“程先生,我们是在向南去吗?”
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你还认路?”
我拧拧眉,他是当我昏头转向的,任他带到别处去?若不是知道他的底细,我只当是遇上拐子了。
“一有事情就忘了和你商量,你未婚夫家的事情急吗?”
本就是个谎,现在回去,他家门还能不能进我都不确定,还有什么好急的,“不急。”
“那好,冷小姐若是不介意,我们绕道去趟杭州。”我又皱了皱眉,张家中意的儿媳不就是杭州来的吗?心中不快,全落了他的眼,“至多两日,争取明早就回去。”
我忙舒展了眉,“没事,不急的,程先生办事顶要紧。”
“张家在苏州城算是大户了吧?”他带着闲聊的慵懒,问得我心中一提,愣愣看向他,博容在他心里一直就是红房子咖啡厅里被他手下按在墙上的人罢了,怎么现在连人家姓谁名甚都知道了。
“算是了,做些生意,江浙都有些铺子。”定是程虹雨私下里告诉了他什么,那就是冷琮说出去的没错,这样急吼吼地告诉了别人,往后这个烂摊子怎么收?稍稍转念,也不能怪冷琮,这铁板上钉钉的事情,谁能知道也就是镜花水月。
他点点头,“老字号了,经商信誉很好,想来家长和张先生本身为人也不错,结了这门亲,你家里肯定很放心。”
我无奈地一笑,“只要为人不错就可以了,老字号什么的于我反倒是个拖累。”
他古怪地看了我一眼,“现在这个年头,还有人嫌弃家里有个祖业的?”顿了顿,让开对面来车,继而爽朗地笑了,笑得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冷小姐是嫌未婚夫家太有钱了?”
“我……”其实也就他这个意思,只是被他说得沾满铜臭,心中不大喜欢,“倒也不是。”
“那是什么意思?”他低头看我,满眼的琢磨,“你倒和你演的那个角色像得很。”
我勉勉强强知道他说的是《傲慢与偏见》,“那可差太远了。”可他之前还连书名都忘了的。
“哎,树大招风。”招揽来玲玉之类的人。
“那还不就我说的意思。”他又大笑,有上气不接下气之感,我暗自腹诽,我是推心置腹地说了心底的话,到他这儿倒好,落得一阵取笑。“那你倒说说你理想的境地是什么?”
我斜了他一眼,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为人好就好了。”
“没别的要求了?你们吃什么穿什么?就摆个那样的摊子?”他手指指窗外,恰恰路过一个集市,街角一个满身迂腐气的类似旧时秀才的男子摆个小摊,背后一个旗杆扎在地上,上头飘面白旗,黑色大字“卖字”,驻足者寥寥。
“程先生也太……”心里觉得他在侮辱人,没有他这样的大富大贵,却又不至于这样,好歹我也是中央大学的学生,“为人好未必沦落成这样。”
他敛了笑,正色道,“那你期望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期望……”我转头望向窗外,这才想起今天是周日,又是早上的集市,外头熙熙攘攘,大多是周围十里八乡的庄稼人来赶集,各色布衣打着补丁的人摩肩接踵,小贩吆喝;而我们走的又是一条连接城市的主干道,前后不乏一色的黑色轿车,隐约见得衣冠革履的政府人员或是买办。“也没个具体的行当,教师、记者、医生、银行职员,或者自己开个小铺子,经营点小买卖,正正经经过日子,都是可以的。”
“你倒是会挑职业,你觉得现在的记者也是好人?”他略带不屑。
“有好有坏,和记者这个行当没没有什么关系。”
他摇摇头,“溜须拍马,各个势力养一帮文人,在报纸上相互口诛笔伐,你觉得这样的人你喜欢?”
我摇头,“被势力拉拢的都是有名、有立场的记者了,若是他们当真想什么写什么,那倒也还算好,就是那些为了自己利益歪曲事实、断章取义或是夸大渲染的最可恨了。”
“除了这些黑白颠倒的,还有别的记者?”
“有啊!”他这一棍子打死一批冷琮这样的人,“有许多独立的报社,知名高校的学生都会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那些记者不好吗?”
“那种事情你遇见了别搀和,关系好的同学你也劝劝,关系不好的嘛,就算了!”他嬉笑着,看不出来还这样小心眼,“说是前所未有的昌平年代,这种社论,白字黑字的,回头真要追究,一个都跑不掉。”这个话已经不是开玩笑,听得我竟一个哆嗦,可学校里的教授和学生都还是热烈参与的,不像他说的这样凶险。可看他一脸严肃也不便反驳。
“也还有写写风土人情、名人轶事的小记者,悠悠闲闲的,挺好。”翻开前面的,新开个题。
“你还挺了解,有认识的这种记者?”
“我哥就是啊!”我一脸得意,原来不知不觉中我对冷琮也是自豪的。
“你还有个哥哥?”他瞪大双眼,喃喃一句,“我怎么不知道,你家孩子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