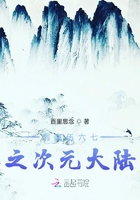婚礼推迟两个礼拜,是我要求的,伤口养养好,才好穿得漂漂亮,程昊霖起先死活不答应,就怕夜长梦多,好说歹说才同意。
婚纱是月牙色的白,他说头一次看到我时那身旗袍便是这月牙色的,淡淡晕着,整个人都笼在一片温婉里;后来鲜血喷涌时仍然穿着那月牙色的旗袍,他以为这是老天跟他开的玩笑,所好万幸万幸。
绸缎的长裙,立领和胳膊是繁复的蕾丝,带着奶油蛋糕似的白。领口用一排珍珠扣合起,恰好遮在伤口上,掩得干干净净。
我从试衣间里走出来时,他本是在沙发上慵懒地舒展了身子,猛地抬头眼中的惊喜,印在我的眼中,荡开阵阵涟漪。
“程将军好福气,冷小姐穿这一身好漂亮哎。”立在一旁的女店员接口倒很快。
程昊霖这个时候反倒露出难得一见,不,是从没见过的腼腆,“是好漂亮,包起来?冷伊,你觉得呢?”
我对着镜子里转了个圈,仿佛脚下是舞台,头顶全是炽热的灯光,我是最美的舞者在台上起舞,而台下是最重要的观众,却只有他一个。停下来冲他点点头。
这些天,我们在筹备婚礼,程虹雨早出晚归,却总不和我们打照面。程昊霖一心想让她即刻动身去香港,被我劝住,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婚期在即,他的妹妹在这之前离开南京,岂不是昭告天下,程家的后院起火,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还是关起门来自家人解决,莫要让别人看了笑话,他才同意下来。虽是暂时留了她,一想到那些个事儿,我的心里仍旧凉凉的。
婚礼的前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忽然听见阳台上有轻微的响动,先是试探的轻声敲门,我从床上坐起,那敲门变成了规律的。
走到门边,他听到脚步声才停了,等了会儿,见我不开门,他有点急了,“让我在这儿站着?”
“难不成请你进来躺着?”我靠在门上,噗嗤一声,“明天结婚,你今晚上不能消停些吗?”
“不能,就怕你又跑了。”他也靠在门上。
“今晚可是你程将军最后一个未婚的夜晚,明天你就有了家室,你还不去外面花丛里最后再流连一下?”
“你这都是什么歪心思?”他愤愤地批驳我,“只盼这最后不安定的一晚快过去吧,恨不得整晚守在你床边上。”他点了根烟,叼着烟的口里含含混混,“方才睡不着觉,就怕明早来看,你一声不响又消失不见。”
“你不离我就不弃。”脱口而出,出口才后悔,他要笑话我了。
果然他哼哼了两声,“你从没跟我说过这么好听的,你不弃我就不离。”
两人一齐笑了,他说外面的月亮很圆很亮,正应团团圆圆的景,从月亮谈到鲜花,谈到江南的烟雨与塞北的大雪,谈到小时候黄梅雨天,雨水泛滥,我和冷琮在院子里钓鱼玩儿,谈到小时候他和昊霆、虹雨在山林间打雪仗,过去的时光里也有忧伤的日子,譬如总有人笑话我没有爹,他去别人家作客,大人们以为人小不懂事,当着他的面都能说他是姨太太的儿子。从前,隔得那么远的那么多年,我们的生活迥异却又有惊人的相似。
直到夜已深,外头再无旁的声息,我们才相互道晚安回房睡去。
这次他透着前所未有的沉不住气,早晨是被他敲门敲醒的,只为探个头进来看到我还在,他仿佛长舒一口气,“我在隔壁换衣裳,让文竹进来帮你。”
文竹帮着我洗漱穿好,外头的化妆师摄影师也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许多年没见了的《西洋画报》的摄影师,当初帮我摄下花王牡丹照的黄老师,他扭着胖胖的身子进来,翘着个兰花指,“哟,冷小姐,你这个婚纱裹得太多啦,裹成这个样子怕给人看去啦?”又望望站在走廊里不住探头的程昊霖,“也对也对,程将军就生怕你落了人家的眼。”
匀细的粉面,淡红的胭脂,不一会儿镜中便是个娇羞的女子。走出去的时候程昊霖的眼中又是一道光亮。
他执着我的手往楼下走去,程虹雨红着眼守在楼梯口,递给我一束捧花,淡紫同白色的花球。她小心地跟在我身后替我将婚纱的曳尾摆动好。
我们在大太太的房里对着她鞠了鞠躬,给她敬了茶,她仿佛清醒了许多,对着我俩一个劲地笑。
坐上轿车往中央饭店去,程昊霖仍旧捏着我的手不放,紧张得反倒要我宽慰似的再反捏捏他。
草坪上早就装点了和手中花球一色的白玫瑰和淡紫的绣球,热烈地绽放如当下的初夏,正散发着夏日空气里的甜香。
听说茹梦和吴庸两个人一早就在这场地上忙活开了,我们到的时候,茹梦一手插在纤细的腰里,一手到处指着,支派那些忙活着的服务生以及吴庸把各个物件摆放到恰当的位置上去。吴庸边笑边忙着满足她那挑剔的要求。
明明是我们的婚事,有了热心的别人张罗,我俩反倒没事人似的站在花束搭就的一个圆拱之下。
他双手扶着我的肩,满脸遮不住的喜悦,“刚刚有个人来告诉了我件事。”他顿了顿,抑制了下自己的感情,他这样难以自持的样子着实少见,我觉得很醉人。
“什么呀?”不知不觉自己说话的声调也变了。
他摸了摸我盘起来的长发,“冷琮被救上来了,虽是染了肺炎,但已无大碍,正在广州养病,不出意外,过两个礼拜应该就能到南京。”
我愣了片刻,欢呼了一声,向前一步,抱住他的脖子,他顺势搂住我的腰,“我们之前错过了太久,老天有眼,这次有心成全啊。”
“程昊霖,我爱你。”平静了一小会儿,咬着他的耳朵说。
“我也爱你,比你爱得多。”
“哎哟,你们俩,我都看不下去了!”冷不丁茹梦从斜里冲出来指着我俩就是一顿数落,“马上就结婚,这么一会儿也等不得?”吴庸叉着腰站在她身后,不看我们只看她,也是一脸甜蜜。
“快快到前面去,马上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