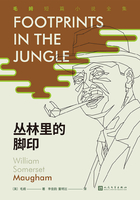克丽丝汀低下头,把脸藏在他肩膀下。
第四天,他们躲进农场上方的山间桦树林。那天佃农要搬运草料。克丽丝汀和尔郎的看法不谋而合,觉得不必让人知道她来这里陪他。他到屋舍去拿一两次食物和饮料,她则坐在矮桦树之间的石南丛里。他们坐在这边,可以看见男人和女人背着草料,辛辛苦苦走回家。
尔郎说:“你记不记得,以前你答应过我,我若落得在山间当小农夫,你要来替我管家?你大概会养两头母牛,几只山羊和绵羊——?”
克丽丝汀轻笑着,抚弄他的头发。
“尔郎,母亲若逃出教区,遗弃他们——你想儿子们会说什么?”
尔郎笑道:“我想他们乐意在柔伦庄当主人。他们年纪不小了,可以做主。高特年纪虽轻,你知道他是优秀的农夫。纳克可以算大人了。”
孩子的母亲静静笑道,“噢,不。他自己是这么想——是的,他们五个都这么想——不过他还缺乏成人的智能——”
尔郎说:“他如果像父亲,可能要很晚才有成人的智慧,甚至永远没有。”他泛出顽皮的笑容:“克丽丝汀,你以为你还能把儿女藏在裙摆下——纳克今年夏天做了爸爸——我想你不知道吧——?”
“不——!”克丽丝汀坐在那儿,面红耳赤,吓得发呆。
“是死产——我想他会三思而行,不再到那个地方——女方是此地豪根山庄‘巴尔之子’的遗孀;她说孩子是纳克的;无论真相如何,我想他并非完全没有错。是的,你我现在成了老人家哕——”
“你儿子惹上麻烦,招来耻辱,你竟说得出这种话?”丈夫说话太轻松,她痛心极了——他的眼神有玩笑意味,她却不觉得好玩。
尔郎照旧说:“那你要我说什么?小伙子十八岁了。你自己明白,你把他们当小孩子,成天严密监视,并没有什么效果。你上山来陪我的时候,我们想办法让他成家——”
“你以为我们可以轻轻松松为纳克找到相配的对象——?不,夫君,出了这种事,你千万要跟我回家,帮忙管管孩子。”
尔郎猛支起上半身:
“我不干,克丽丝汀。我在你的家乡是陌生人,永远如此——这里每一个人都把我当做国王和国家的叛徒。我住在柔伦庄的几年间,你从来没想到我活得不自在——在史考恩的家乡,我的身分可重要多了。即使青少年时代——我生活不检的消息传遍各地,被教会逐出教门——我仍是胡萨贝的‘尼古拉斯之子尔郎’!克丽丝汀,后来——我有幸向山北的乡亲证明,我并非先祖的不孝儿孙——不,我告诉你!在这个小农场上,我自由自在——没有人监视我的言行,在背后说闲话。听着,克丽丝汀吾爱——陪我留下来!你决不会后悔的。此地住起来比胡萨贝更舒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克丽丝汀——打从小时候,我在那边就不愉快、不轻松。我和爱琳的生活有如地狱;你和我住在那边,心情也不愉快一可是上帝明察,我认识你以后,每一天每一个钟头都深深爱你。我想那个庄园大概被人施了魔咒——我母亲在那边痛苦而死,父亲也从来不快乐。克丽丝汀,这里很舒服——只要你肯陪我一多年前玛格丽特弥撒那一夜,你睡在我的斗篷下——我坐着看你,你像一朵纯洁、清新、年轻、没有人碰过的鲜花,当时我好爱你——我发誓,今天我对你仍珍爱如昔。”
克丽丝汀低声答道:
“尔郎,你也记得吧,那天晚上你祈祷说:但愿我永远不必为你流一滴眼泪——”
“是的——上帝和天上所有的圣徒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事与愿违,不错——我们在人世间,大概难免如此。但是,我无论使你受益或受害,心里始终爱你。住下来吧,克丽丝汀——”
她依旧柔声说:“你有没有想过,父亲遭人议论,儿子们的命运也许很艰苦?他们七个不能全部逃入深山,躲避教区的闲话——”
尔郎低头看地面。
他说,“他们是年轻、标致、豪勇的青年——他们会自己闯出一条路——克丽丝汀,我们过不了几年就老了——你愿意荒废自己还漂亮、抖擞、适宜享受人生的年华吗?克丽丝汀——?”
她垂下眼皮,躲开他那迷乱的目光。过了一会儿才说:
“尔郎,你忘了我们的两个么儿还是小孩子?我若抛弃劳伦斯和慕南,那我算什么——”
“你带他们上来嘛——如果劳伦斯不肯跟哥哥们同住的话。其实他也不小了——慕南是不是像以前那么漂亮?”做父亲的人含笑问道。
母亲说,“是的,他是最漂亮的孩子。”
后来他们闷坐良久。再开口时,谈的是别的话题。
她在山上每天都是破晓时分醒来,次晨也不例外——躺着听马儿在屋墙外跺蹄。她双臂紧搂着尔郎的脑袋瓜。前几天一大早醒来,她也跟头一天怀着相同的恐惧和羞耻感——努力压抑着。他们不是反目又和解的夫妻吗?父母能和好,对儿女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
今天早晨她设法顾念她的儿子。她好像中了邪——尔郎带她走出第一次相拥的吉达露森林,直接来这里。他们好年轻一她不可能真的为他生过七个儿子,成了壮汉的母亲——她似乎一直躺在他怀里,胡萨贝庄园多年的婚姻生活只是一场梦——他的莽话引诱着她,在她心中回响——她吓得头昏眼花,觉得尔郎似乎挥开了她的七种责任——就像一匹小母马站在畜场的牧地上——包袱、马鞍、头套都卸除了;山风迎面吹来;她自由自在吃柔软的山草,可以随便跑上所有的高原荒地。
同时她又心甘情愿想承受新的负担。她已经昏陶陶渴慕着未来九个月将要孕育的胎儿。打从第一天早晨她在尔郎的怀中醒来,她就知道了。不孕症已随着她心灵的干热病消失。她子宫内怀着尔郎的孩子,心灵万分焦急,等待孩子出生的一刻。
她暗想,大儿子们不需要我。他们嫌我昏愦烦人。我和小家伙只会妨碍他们。不,我不能离开这儿一我们必须跟尔郎住在这里。我不能走——
可是夫妻对坐吃早餐的时候,她却说要回家去看孩子。
她考虑的是劳伦斯和慕南。现在他们不小了,她一想到他们跟尔郎和她住在这儿,发现父母变得这么年轻,也许会用惊讶的目光看他们,她实在不好意思。可是他们两个又少不了她。
她谈到归程,尔郎坐着凝视她。最后他脸上掠过一抹笑容。
“好一你若想走,那就走吧!”
他准备送她一程。两个人骑马经峡谷进入西尔区,他隔着松树梢望见教堂的屋顶,遂跟她道别。他直到最后还微微笑,笑得顽皮又放心。
“你知道的,克丽丝汀——无论你白天来或者晚上来——无论我等了你多久——我都会欢迎你,把你当做下凡的天后——”
她笑道:“我不敢参与这么大的神迹。爱人,我想你一定知道,男主人回家那天,必是你家最快乐的日子。”
他摇头笑一笑。两个人含笑道别。他们并肩坐在马背上的时候,尔郎探身吻了她许多许多次,空当间并用笑眯眯的双眼凝视她。
他终于说,“克丽丝汀,那我们来看看谁比较倔强吧。这决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我都知道!”
她通过教堂外面,不觉打了个寒噤。她仿佛由山魔王的殿堂走回家;尔郎就是山魔王,不能行经教堂和绿地的十字架面前。
她拉拉缰绳——差一点回头去追他——
接着她俯视绿草斜坡,俯视她自己的庄园、草地和田地,以及弯弯流过山谷的河流。群山耸立在蓝雾中——天空满是鼓胀的夏云。简直发疯。他理当在家陪儿子。他不是神话骑士——虽然个性疯疯癫癫,喜欢胡思乱想,他却是基督徒;是她无论好坏都忍耐到底的结发丈夫——他反复无常,害她痛苦,她也忍受着。她必须容忍他;既然少不了他,她只得尽力奋斗,忍受恐惧和不安全感。现在他们又欢聚了,她认为丈夫不久一定会回来——
12
她对儿子们说,父亲要在豪根屯料理一两件事情,然后才回家。他可能在初秋下山。
她在庄园上走动,显得年轻,脸蛋儿嫣红,表情柔和温婉,做事情手脚麻俐——结果却不如平日安安静静、有条有理进行来得成功。儿子们如果做错事或者害她不满,她不像以前厉声责备他们。现在她以玩笑口吻说话,或者一句话也不说就放过他们。
劳伦斯打算跟哥哥们睡阁楼。
“好,儿子啊,也许我们该把你算做大孩子了。”她伸手去摸儿子密密的黄棕色的头发,把他拉到身边——他的高度快到她胸口了。“慕南,你呢,你肯不肯妈妈再把你当一段时间的小娃儿?”晚上么儿到大厅安歇后,仍然喜欢母亲坐在床边,爱抚他一会儿;他把头枕在母亲膝上,喋喋说些儿语,白天哥哥们听得见的时候,他是不说这种话的。母子讨论父亲返家的日期。
接着他挪向墙边,母亲替他盖好被子。克丽丝汀点上蜡烛,拿起儿子们要补的衣裳,着手缝衣。
她解开胸口的别针,甩手摸摸乳房一又圆又挺,像少妇。她把袖子卷到肩头,借着灯光打量自己光裸裸的手臂。手臂变白、变胖了。于是她站起来走一走——穿着合脚的室内鞋,自觉步态好轻柔——她抚一抚瘦削的臀部;不再像男人又尖又硬了。血液流遍全身,像春天的树脂在树干中流动。青春在她体内发芽。
她跟菲莉达在酿酒房工作,倒些热水去泡谷子,准备做圣诞节的麦酒。菲莉达忘了及时照顾;麦子还在膨胀,就任它发干。克丽丝汀没有骂女佣人——她笑眯眯听对方找借口。克丽丝汀自己也头一回忘了注意。
圣诞节尔郎一定回家陪她了吧。她派人送上怀孕的消息,他必然会立刻返家的。他不可能疯疯癫癫不让步——他该看得出来,她体内有小生命,不能爬上豪根屯,远离民众。但是她要拖一段日子才捎信去——甚至等体内有了胎动再说——他们迁居柔伦庄的第二年秋天,有人说她不得不避开人群。当时她很快就求得安慰。这次她不怕会如此——不可能。然而——
她觉得自己必须倾全力保护体内这个弱小的生命一就像一个人弓手庇护新燃的小火种——
秋末的某一天,伊瓦和史库尔说他们想骑马上去看父亲——现在山区优美又有趣;正是清爽的黑霜期,他们想叫父亲带他们去打猎。
纳克和布柔哥夫坐着下棋;停下来注意听。
克丽丝汀说,“我不知道。”以前她没有想过——该派谁去传消息。她看看两个半大的儿子。她自觉很傻气,硬是没办法对他们开口。她不妨叫他们带劳伦斯同行,叫他单独告诉父亲。他年纪还小,不会惊讶的。可是——
她说,“你们知道爹很快就要回来了。你们去找他,只会碍手碍脚。不久我自己也有口信要带给他。”
双胞胎嘀嘀咕咕发牢骚。纳克由棋盘上抬起头来,厉声说:“小鬼,听娘的吩咐。”
圣诞节快到了,她派纳克到北方去找尔郎。“儿子啊,你必须告诉他,我现在渴望他回来——我想你们大家也是一样!”她不谈新的理由——她认为成年的儿子可能看出来了。他该自己判断要不要告诉父亲。
纳克回来——说他没找到父亲。尔郎到劳玛斯山谷去了;他好像接到女儿和女婿要迁往布柔哥文的消息,玛格丽特希望在维奥岛和父亲见面。
合情合理嘛——晚上克丽丝汀睡不着——小慕南睡在她旁边,她不时摸摸他的脸蛋儿。尔郎不回来过圣诞节,她很伤心。但是机会来了,他想见见女儿,完全合乎常理。她抹去偷偷滴下来的眼泪。现在她又像年轻时代那么爱哭了。
圣诞节过后,艾瑞克神父去世了。秋天他卧病在床,克丽丝汀不只一次到罗曼庄去看他;也参加了他的丧宴。此外她从不和乡亲来往。教区老神父去世,她视为一大损失。
她在丧宴上听说有人在莱斯雅遇见尔郎,可见他正在返家的半路上。不久他一定会回来的——
后来的几天,她坐在小窗前的板凳上,手持她特意找出的小镜子,对着它吹气,把它擦亮,照一照自己的娇颜。
最近几年她被太阳晒黑了,有如贫农的妻子,可是现在日晒的痕迹一扫而空。她的皮肤很白,双颊又圆又红,像图画似的。跨出少女时代以后,她从未如此娇美——克丽丝汀惊喜得屏住了呼吸。
如果接生婆的说法没有错,那他们终于要生一个尔郎多年企盼的女儿了。梅根希尔德——他们这回必须打破惯例,为第一个女儿取祖母的名字——
她想起以前听过的神话故事。有七个儿子为了胎中的小妹妹被父亲赶出门。接着她又自嘲自笑——她不懂自己怎么会想起这个故事——
她由缝纫椅内取出独处时缝制的细白麻衬衫;抽出亚麻线,在透明的抽花背景上缝些鸟儿和动物的图形——她已好久好久没干这种细活儿了——噢,但愿尔郎现在就回来——趁她漂亮、年轻、挺拔、脸蛋儿嫣红如花的时候——
乔治弥撒日(3月12日)刚过,天气好得像春天。雪融了——亮得像银子;斜坡上已有棕色的田地吸取阳光;山上罩着蓝雾。
有一天高特站在庭院中修理一架破雪橇。纳克倚着柴棚看弟弟工作,克丽丝汀由厨房出来,双手捧着一大槽新烤的黑面包。
高特看看母亲,然后把斧头和螺丝钻放在雪橇上,追上去接过面包槽;端到储藏屋。
克丽丝汀猛停下脚步;两颊发红。高特回来后,她走向两个儿子说:
“我想你们这几天必须上山去找你爹——说家里头现在很需要他,分担我肩上的责任。现在我什么都不能做——而且我会在春耕期间分娩一”
孩子们用心听,他们也脸红了;但是心里很高兴。纳克故作漠然说:
“我们不妨今天去——晌午时分——弟弟,你看如何?”
次日中午。克丽丝汀听见院子里有马蹄声。她走出去一是纳克和高特——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站在马儿旁边,低头看地面,一句话也不说。
“你爹说什么?”母亲问道。
高特倚着矛枪站立——仍旧低头看地面。
纳克说:“爹叫我们告诉你,整个冬天他一直期望你上山去找他。他说你会像上次一样受欢迎。”
克丽丝汀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那你没对你爹说——我现在怀孕——不久就要分娩了——?”
高特没有抬头看母亲,他说:
“爹好像觉得这不成理由——不认为你因此就不能搬到豪根屯去。”
克丽丝汀静静站了一会儿。
她粗声问道,“他说什么?”
纳克想说话。高特举起手,以哀求的目光望着哥哥。长子不管,仍旧把口信说出来:
“爹要我们转告你:你怀这个娃儿的时候,明知他的财务状况。现在他不比当时有钱,却也不比当时穷。”
克丽丝汀转身背对着儿子,慢慢走向大厅。她沉重又疲乏地坐在窗前的板凳上。春阳已经把窗子上的冰柱和白霜融化掉了。
——不错。是她先要求躺在他怀里的。现在他提起这件事,实在不应该。她觉得尔郎
不该叫儿子们送回这样的答案——
春天的气候持续了很久。有一星期吹风,下大雨——河水高涨,哗啦哗啦响。山腰的溪泉汩汩流;山谷传来雪崩的声音,然后阳光又露面了。
一个灰蓝色的傍晚,克丽丝汀出来站在房子后面。田地下方的树丛内百鸟争鸣。高特和双胞胎到山间畜场去了——他们正在追黑野鹬。一大早猎物的鼓翼声就传到庄园。
她握拳按着胸口下方。产期将届——她必须忍耐到底。她常常刚愎自用,很难相处——为孩子日夜担忧,判断不正确——照尔郎的说法,也就是不合时宜。不过她仍觉得丈夫狠心。他马上就该回来看她了——他一定也知道。
阳光和阵雨轮流出现。有一天下午儿子们呼唤她,他们七个人和全体家仆都站在院子里;山谷对面有三道霓虹;最里圈的虹脚搭在佛莫庄园的屋子上,完完整整,色彩鲜明又强烈;外面两圈颜色较淡,位置很高——
他们正在观赏美妙的奇景,空中渐渐暗下来,一阵暴风雪由南方横扫而至。雪花纷飞,不一会儿全世界就白茫茫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