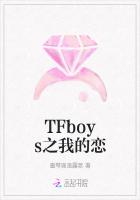但她又喜欢干净。干净,多么简单美好的词语。只有从宁良生的眼神里,她可以看出这两个字。有的时候,看着他骑着自行车去上班,把挣来的钱给她买一瓶眼霜,不是不心酸的。
多数时候,她无动于衷。
有人享受,就要有人下地狱。
她准备把自己献给宁良生的。只一夜。一夜就够了。
这么多年了,也应该了。她居然是这种报答心理,从进门的刹那,她就黏在他身上——他到底是男人吧,何况刚才还那么冲动地亲了她?
可是,他把她抱在怀里,忽然哭了,哭得很伤心:梁梁,你跟我好吧,就跟我,行吗?我会和你好一辈子的,我会的。她也哭了,跟了那么多男人,没有人和她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人。他们把她当作点缀,当作符号,只有他是真心的。
你要我吧。她轻轻地说。
他捧起她的脸,你说,你只和我一个人好,我们结婚,我养着你。
呆子。她笑了,你养不起我的。
我有了钱你就跟我,行吗?
行。她轻易地说。她知道,宁良生是不会有钱的。
四
但宁良生有了钱。
他买了两年彩票,买到灰心时,中了。
当他知道自己中了五百万时,他显然不敢相信。手都有些哆嗦,这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告诉梁梁。是的,告诉梁梁。
梁梁的电话关机了。
他打车,四处去找她。
她住的地方他几乎都去过,画家的798,摄影家的宋庄,导演在燕郊的别墅……他也舍得打车了,从前总是挤地铁,现在,他有钱了!
五百万呀。
最后,他在一个造型师的工作室里找到了梁梁。
梁梁显然还没有醒,她睡眼惺忪地问:有事呀?造型师在旁边说:有他妈的病。他管不了那么多,兴奋地说:梁梁,我有钱了——五百万。
梁梁说:真的呀?
当然!我中了!
宁良生说话还没有这么高调过,声音都高了八度,他说,你说怎么花吧?我都给你。
这句话让梁梁感动了,她拉着他的手,走,先带我去吃饭吧。
那天他们在浪淘沙吃了鲍鱼,宁良生笑着说:以后,鲍鱼我都让你吃顶了。
接下来进入了花钱的狂热期,宁良生为梁梁买了一整套三环的房子,在方庄那边,又买了一辆宝马车,手里的钱居然所剩无几了。梁梁说去趟欧洲,问是不是可以。宁良生喜悦地说,当然可以,别说欧洲,月球咱也去。
他喜悦的是自己喜欢的女人居然能花上自己的钱了。
这才知道,有的时候犯贱也会幸福。
五百万以为很多,三花两花也没有了。不过半年时间,五百万就彻底没有了,宁良生的所得就是去欧洲时留下来一些照片,有几张梁梁和他的合影,很乖地站在他的身边。就为这些照片,宁良生觉得也值得了。因为他喜欢她。喜欢一个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他没有想到梁梁还是不要他。
真的没有想到。
在他给梁梁买来的房子里,住着年轻英俊的北漂男人,还有莫名其妙的诗人。在他给她买的车里,常常拉着乱七八糟的女孩子,最不能忍受的是,梁梁居然给他介绍起了对象。
一个叫红红的女孩子。
他看着她,心酸地问:梁梁,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我?
梁梁吃吃地笑:呆子,咱俩根本是两条平行线,不可能的。
他想问她,那你为什么还不离开我?可又不敢问,如果问出来,一切就失去了。关于这五百万,他也不说,因为,这是他心甘情愿。
红红问他,宁良生呀,你为什么这么傻呀。
他记不清红红的长相,只觉得这个女孩子粉涂得太厚了,头发太黄了,而且腰也粗了些,他抱过梁梁,纤腰一把,非常让人震撼。
红红之后,梁梁又给他介绍了张妙。
张妙是戏剧学院的,眼睛都会说话,总是以为他有钱,因为他给梁梁花了这么多钱呀,可是宁良生老实地说,我是中了彩票的,除了梁梁,我也不可能喜欢别人的。张妙再也没有联系他。
在梁梁还要给他介绍第三个女友时,他央求她说:求求你了梁梁,你别再伤1我了。你可以不爱我,不要我,但请给我留一点自尊。好吗?
好吧,梁梁说,那你自己找女朋友吧。
五
宁良生知道,这世上原来有这样一种苦痛——说不出,真的说不出。它隐藏在自己心里,是那样发疯似的生长。长到黑夜里,只能在黑夜里。
他甚至连要求她都觉得是狂语。
当然不可能去找什么女友的。
她是唯一。
这唯一有时给他打电话,吃饭喝酒出席什么什么开幕式,他仿佛是她的陪衬,也可以有,也可能没有。
好男人是坏女人的温床。他滋生了她的坏脾气,她有一次骂他:你怎么就一副窝囊废样子?哪个女孩子会看上你呢?你不能一辈子总靠抓彩票吧,也许永远不会中了!你得找点事干呀,一个月三千块,喝西北风呀!
其实是有女孩子的。父母给他介绍了一个叫丽然的,护士。也不难看,一看就特别贤惠,和他小时候一个班待过,对他印象不错。如果没有梁梁,宁良生想,他可能真就和丽然好了,两个人生个孩子,过下去。很多人就是这样老的。
可是,他有了梁梁。
一切不同了。
这个女人会在喝醉时说,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宁良生,你也是我最醉人的酒,你还是太阳下最白的白衬衣。这些句子,丽然不会说。
他宁愿这样一意孤行地孤单下去。
也知道自己傻。
五百万呀,自己可以过一辈子,可是,没几天就让梁梁花完了。花完了,她亦不是他的。这是她的命。
只要能看地就好。
可是,可是没想到梁梁会蒸发,会失踪,会再也没有了踪影。
方庄的房子没有了,车卖掉了。梁梁彻底在北京失踪了。好像她和他就是一个传说,一个故事,连她和他的合影也全在电脑里,没有洗出来,他身上一点梁梁的印迹也没有。如果说有,就是那个冰凉的吻吧,轻轻地在他的唇上游荡着,让他痛彻心扉。
登了寻人启事,也去了电台。
后来才明白,梁梁是刻意离开这个城市,他虽然没有要求什么,可天天准时出现,很多男人都问过梁梁,这个男人是干什么的?
梁梁大概没有好意思让他走。于是自己走了。卷着所有的东西,走了。
宁良生走在空空荡荡的大街上,只觉得一片茫然,二十八了,他周围很多同学早就结婚了,还有的出国了,还有的发了财。
而他和刚毕业时一样,一无所有。穿着一百块钱一件的衣服,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吃三块钱一碗的拉面,胡子拉碴,有一天看到理发馆里自己的样子,居然头发很长很长了,黑瘦黑瘦的,眼睫毛还是那么长,他颤抖着,不停地哆嗦着,终于放声大哭。
理发师说,哭什么哭,你妈死了?
哭够了,他说,理个小平头,干净的那种小平头。宁良生知道,有一种方式是把过去忘记,重新开始。否则他这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几天之后他娶了丽然,丽然提了护士长了。婚宴办得很热闹,两家老人说了许多吉祥话,早生贵子之类。他在丽然的帮助下开始折腾药品,几年之后就发了财,这里面的秘密很多。他胖了,也学会了给客户找个小姐,送些购物卡,过年过节打点客户。坐在自己买来的宝马车里,有时会想念一个人。他不敢多想她,想多了,还1 0是心疼。
孩子五岁那年,他对丽然说,想出去走走,腻了。
丽然说,我陪你吧。
他摇摇头说,我自己吧。从结婚到现在,丽然算个好女人,同床异梦——她半点不懂得他,这才是好的婚姻,懂得了,那是爱情,不是婚姻。
他一个人去了欧洲。沿着他和梁梁曾经走过的路线,一边走一边想,当年是住过的哪个酒店,在哪个咖啡馆里喝过咖啡。
这么多年过去了,以为忘记了,却全记得。
虽然,虽然他只是她的七分之一。
回国后就托人打听她,这才明白,如果想找一个人,太容易了。不说有百度或人肉搜索之类,有足够的钱,找一个人太简单了。
拿到梁梁的地址后就订了去重庆的机票。
到了沙坪坝,寻着那个巷子慢慢走,一边走一边害怕着。
居然离开十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晓轩窗,正梳妆。这样想的时候,心里猛然一抽。问旁边邻居梁梁是不是住这儿?邻居一指,那不就是,她每天这一般光景出来买菜。
他呆住。
几乎吓了一跳——那女子胖得长宽高几乎一样,当年妖艳不复在,她本来就长他三岁,如今也是三十七八岁的女子吧?穿了特别宽松的衣服,简直像胖了的山口百惠被人拍到,让当年的粉丝差点自杀。他张了半天嘴,以为叫出了她的名字,却发现,根本没有声音。
他被光阴吓到。
一路狂奔下去,生怕被什么追上似的。
明月夜,短松冈。
原来,怀念适合在回忆里。适合在故人西辞的旧云烟里,他买了一张当天回北京的机票,以最快速度离去。
在飞机上,他无聊得想哭,可就是哭不出来。
他曾经在最年轻时陷入一场无法描述的爱恋,到最后才发现,原来,他爱上的是自己的狂热。虽然,他只是她的七分之一。
后来,他居然在飞机上睡着了。在梦中,他梦到了她,她还那样年轻妖艳,还叫他呆子。醒来,看到空中小姐站在他旁边笑着说,先生,你一直在叫一个人的名字呢。
谁?他说。
梁梁。多好听的名字呀。
你爱人的名字呀,空中小姐问。
他摇摇头,忽然觉得这满怀的心酸就让这一问逼出了,他说,麻烦递给我杯冰水。
接了冰水,他一饮而尽。
接着,北京到了。
他喝的那杯冰水,化成铁马冰河,一路紧逼而来,让他没有退路。
他知道他败了,到底。
他败给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