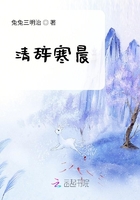他最后烫了我的手臂下端靠近肘部的地方,每次我都试图撑住,但没有用。屋子里烧肉的臭味和胳膊上创面引起的剧痛相结合,让我想吐。第二次和第三次烫我的间隔里,他还打了我的后脑勺,我猜用的是棒球棒。他打得我很疼,但胳膊更疼,反而分散了我刚刚挨的这一下所引起的痛感。
卢戈说:“你在银行有保险箱吗?”
“没有。”我实话实说,不幸的是,似乎没用。
“你的遗嘱放在哪儿?”他问。
“我没立遗嘱。”我说,意识到是不是很快就得立一个了。
他大笑着说:“犯大错了。”边说边用枪托在我后脑勺上打了一下。好吧,我似乎已经得到了自己那个没问出来的问题的答案。
他们又来烫我,这一次变本加厉,免得像前三次一样没有表达清楚他们的意思。当然了,烫我之前,那个人又不停地重复着那种病态的呻吟“火……火……火”,烫完之后又像只鬣狗一样哈哈大笑。
“我们会找到所有东西的,要是你对我们撒谎,我们就杀了你。”卢戈说。
“哦。”我说。听起来不管怎样你们都会杀了我,有什么区别呢?
他继续说:“明天给你老婆打电话,告诉她周五离开这儿去哥伦比亚。让她除了衣服什么都别带,包括她的珠宝首饰都得留下。明白了吗?”
我想他们真是太仁慈了,还允许我妻子给自己和孩子带点换洗的衣服。这些人像猪一样贪婪,他们什么都想要,想夺走我的一切。
“好,我明白了。”我回答。与此同时,我想这些人肯定赢不了任何智力竞赛,他们不想让我妻子怀疑,但是又让我给她传达一定会令其起疑心的口讯。当然,前提是她还未起疑。
“你家保险柜里有多少钱?”卢戈问。
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出现,我通常在保险柜里存一大笔现金。因为安德鲁飓风之后,我一度手头缺钱,因此这就成了惯例。说起这个,德尔加多曾提到过他就是这么做的,说我也应该这么做。
“五千块。”我说。
“让你老婆再取八千块现金,放在保险柜里。”
“好的。”我回答。这个“智囊团”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但他们做的事情却全部反其道而行之,就差举起一个写着“出事了”的霓虹灯广告牌,真够聪明的。
灼伤的创面疼得我思绪无法连贯,他们说了什么,说的话有多荒谬真的都不重要了,我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的确引起了我的兴趣。
“还有一件事,我们要派人给你家送一些箱子。告诉你老婆不能打开,把箱子放在车库里,不能打开。明白了吗?”卢戈强调道。
他们已经把我家当做新的邮寄地址了,我对箱子里的东西非常好奇,是枪吗?还是别的用来杀人、折磨我或其他人的工具?又或者是毒品?对这帮疯子来说任何东西都有可能。
“好的。”我说。我还能说什么?难道要说“哦,那得看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他们把我拽起来带进纸箱,我躺倒在地,鼻子里还有皮肤烧焦的味道。这伤口真让人抓狂,但因为手铐的限制,我甚至都没法抬起手来触碰它。那一刻说自己悲惨都不足道,这种感觉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了,我在这种局面下略微能够发挥一些主动性的就是确保家人免受伤害。除此之外都无所谓了,他们想要什么都行,我只能做这么多。
新一轮折磨过后,我相信他们只要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后就会杀了我。但我不能让自己陷入自怨自艾的境地,不能放弃希望,虽然我的未来看起来极其昏暗。即使这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必须保持斗志,战斗到底。我决定继续战斗,并对自己说,好吧,贱人们,来吧。
过了不久,他们回来了,带我去上洗手间。这次他们的确让我解手了,不过不是因为他们大发慈悲,可能是我裤子上散发尿液的味道令他们不快。好啊,这也算是跟他们捣蛋了。像往常一样,去洗手间的路上花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让我绕着圈走,好让我迷失方向,其实根本犯不着。
他们把我带回纸板箱,解开了我脚上的镣铐,又解开了手上的,然后用枪顶着我的太阳穴,把我的一只手拴到一把沉重的皮革椅子上。他们好像是用两副手铐做了一个链子,一头铐着我,另一头铐在椅子上。我只有极小的活动范围,但还是增加了一些自由,手铐也不再勒我的皮肤,算是一点慰藉,还是令人非常开心的。我感觉舒服了一些,如果在这种条件下还能用“舒服”这个词来形容的话。他们给了我一支烟,我坐在箱子上抽了起来。这一次,没有人来烫我的手。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卢戈进来说道:“我们担心你老婆啊。”
“怎么了?”我问,尽量装傻充愣,以便从他们的话里得到更多信息。
“我们窃听了你家的电话,昨晚深夜她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们可不喜欢这样。”他说。
这是真的吗?他跟我说的是实话吗?我无法想象这么一群小丑居然还会窃听电话。但是不管怎样,我决定跟他们玩下去,有时候装傻也有好处。
“我倒不太担心她能做出什么事来,让她走吧。”我说。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轻描淡写,尽量减少他们的恐惧。无论他们表面上在我面前如何装腔作势,内心还是会感到紧张和疑虑的。
“你觉得她是打给谁的?”他问。
我告诉他们:“她只会给她哥伦比亚的母亲或姐妹打电话,在这儿她没人说得上话。”不幸的是这正是事实。
“好吧,希望她别惹麻烦。”卢戈说。
我近乎恳求地说:“她不会的,让她离开就是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些人改变主意,不让我家人离开,而是把他们囚禁在家里,或者更糟的话,关进我所在的这个仓库。
“好吧,告诉你老婆和孩子周五离开。记住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把多余的现金放进保险柜,还有把那几个箱子留在车库里。”卢戈重复道。
“好的。”我松了一口气,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他要改变主意。
我靠着墙,想着还能做点什么。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大脑想不出来任何可行的办法。接下来我做的这件事可能很蠢,但当时却给了我所需要的信息。我以为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听不到任何人的动静,我知道我面前不远处就有件家具。
他们上次给我烟的时候,把烟放在了这东西上,我是从他们发出的声音判断出来的。我想抽根烟,便决定勇敢点,伸手取一根,果然找到了烟和打火机。我拿了一根烟想点着,还没点着,头上就被重重地踢了一脚,踢得我眼冒金星。我并非一个人,一直都有人在监视着我,这真是一个痛苦而有价值的教训。
屋子里这个人问:“你能看见?”他这么问也是情理之中,因为他不知道当我看不见的时候,其他感官就灵敏起来。我说我看不见。他说:“好吧,你要是看见了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我们就只有杀了你。”
我尽力向他解释,我谁都没看见,也看不见。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我太累了,根本顾不了那么多。
我坐在那儿傻笑着,毫无疑问,妻子离开后到了机场的安全地带,就能报警或找FBI,他们会来救我的。想到待在这儿的时间不多了,救兵很快就会来救我,我感到沾沾自喜。绑架我的人永远也拿不到钱或者别的东西,我坚信自己什么都没给他们,而且还把他们骗进了他们自己编织的圈套里。在一个一切按常规运转的世界里,这行得通。我其实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一个黑洞,现实在其中已经被完全扭曲了。
我靠墙坐着,监视我的人最终还是给了我一支烟。我慢慢地抽着,就像是在抽最后一支烟,在这种情况下这也很有可能。当时我甚至都不能够思考,脑子运转过度,精神上的恐惧和胳膊上的疼痛让我的思路完全闭塞了,也许这样最好。在救兵到来之前,我必须集中精力,鼓起勇气应对前方的任何事情。吸完烟我躺了一会儿,渐渐地睡着了,唯一能给我带来安慰和平和的就是睡眠。
***
1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条件反射理论建立者,曾获诺贝尔生理学奖。其有关消化道的实验是以狗为实验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