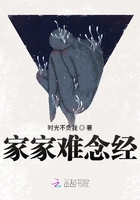每当踏上故乡的土路,总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梁玉龙多么希望一步就跨回家。
天气阴沉。
在乡村土路上疾行了近两个小时后,梁玉龙终于回到了他梦里的故乡。
与他一同回去的,还有夏槐。
不管这里多穷,不管这里多落后,这里永远是他梦魂牵绕的故乡。
故土难离啊。
身子离故乡越远,心便离故乡越近。
几乎在每个梦里,他都能梦见它。
他吃饭的时候会想,父母吃了吗?他们吃得怎么样?
他睡觉的时候会想,父母睡了吗?他们还在忙碌吗?
有时候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
越是接近家,他的心情就越是激动。
更让他激动的是,在村外多了一条公路。
虽然公路狭窄、路面凸凹不平,但总算多了一条公路了。
在这样的高山峻岭中修建公路,难度可想而知了。
能听见鸡的鸣叫了。
他有多久没听到鸡的鸣叫了?
无边的风声。
吹过檩子、瓦片,一些尘粒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站在故乡的领地,他的心荒凉一如她曾经茂盛的原野。
风,像儿时那般刮过低低的沟谷,刮过那棵已经至少百年的老皂荚树。皂荚树上结满了累累的皂荚,只是再也没人把它们当宝贝一样收藏起来,用作一家人一年的洗涤用品;或者在某个寒冷的冬夜,趁别家还在熟睡之际,悄悄地披着单衣起床,在地上摸索着捡起那些皂荚,等天不亮时再担到县城去卖,8分钱一斤,满满的一担,可以换回一家人半年的盐巴。
曾经在无数个夏夜,我躺在丰收的玉米棒上,和儿时的伙伴们睡在上面,一边吹着习习的凉风,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天空有流星划过,儿时的思绪就会飞得很远很远,想象着山外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西瓜成熟的季节,他带上一张篾席,到沙地的棚户下去照西瓜,虽然明知那时候没小偷,但他依然乐此不疲;在那些没有电灯的夏夜,一家人就着月光和星光,在院子的桌子上吃着稀饭,或者是一碗面条,看萤火虫在屋后的水渠边飞舞,他们会兴奋地丢下碗筷,去追逐那些夏夜的小精灵,将它们装在一个玻璃瓶里;启明星刚刚升起的凌晨,他们拿着镰刀,到地里去割豌豆,有一次,他的镰刀快要碰到一只野鸡时,这只野鸡才从睡梦中惊醒,慌乱地扑打着翅膀消失在依然漆黑的黎明……
从故乡的土径上,他们在秋天挑回属于自家的红薯,在夏天挑回黄澄澄的玉米棒子,在春天挑回硕大的土豆。在春天,他们把储藏了一冬的肥料挑到田野里去,漫长而陡峭的山坡,连一个歇脚的平地都没有,在需要连续翻过三个山头的土路上,只能让沉重的黄木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再从右肩换到左肩,他们抹一把快要流进眼睛的汗水,汗水无声地滴落在脚下的尘土,只有扁担吱呀吱呀的声音响在山谷。在秋天,他们一把火烧了田里的荒草,这些化成灰烬的野草能肥沃整整一个年头。为了收获更多的粮食,他们四处开垦荒地,在初春丢下几颗南瓜籽,在初夏土地就能回馈给他们吃不完的南瓜。如今,儿时青葱的田野已大片大片的荒芜,大批的人抛弃故乡,将故乡留给荒原。当年种满庄家的田野,荒草像游子思乡的心绪一样疯长,连人都钻不进去了。
每一个小山坡,每一处谷底,每一道沟壑,甚至每一段路,都有它的名字。这里是柚子树湾,那里叫白沙包,远处是三堆坟,还有枣子树坡里、红苕湾、岩包湾……他们曾经在这块地里种下过胡豆,种下过玉米棒子,种下过黄豆;他们曾经在那道山坡上放牛,打草仗;他们曾经在村庄前的水渠里捉过泥鳅和螃蟹,儿时的那些热烈的午后啊,太阳白花花地挂在天上,嬉闹声响彻云霄。
他已不记得自己是从哪一天离开故乡的,不记得自己是从哪一天开始疏远故乡的,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开始我的脚步不再踏入那些曾经再也熟悉不过的乡间小径的,不记得是哪一天开始长大的,只记得在无数个暗夜里醒来,他的脑海里闪现的,依旧是故乡青葱的草木,是故乡明亮的星辰,是故乡柔软的三月风。
他羡慕故乡的皂荚树。一百多年来它一直站在故乡的领地,看着故乡的每一个人出生,看着每一个出生在故乡的人离开,看着故乡的哪个人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过,看着哪个人再回到故乡时泪流满面,看着故乡的耄耋老者最终如何被抬着去了村里的坟地。它从未离开过故乡,故乡的每一个黎明,每一个黑夜,它一直见证着。
他羡慕故乡的一棵庄稼。它熟悉故乡泥土的味道,它看着蚂蚁成群结队地翻过广袤的田野,在大雨倾盆之前搬到高地,它看着一颗成熟的种子如何走进故乡人的箩筐,如何走进故乡人的灶台,如何成为故乡人的盘中餐,如何成为最原始的故乡的味道。
他羡慕故乡的一粒尘埃。它滋养着故乡的一切,它不会欺骗勤恳的故乡人,它的血液里流淌着故乡人的养分,任狂风刮起,任暴雨冲刷,它对故乡始终不离不弃。
儿时最大的梦想,是离开故乡,到外面的世界去。
现在,他最大的梦想,是离开外面这纷繁的世界,回到故乡去。
只是,那个曾经繁华的故乡,如今已沉默。
他在故乡的这一头,日复一日,时光的洪流将他和故乡隔离,直到他再也没有力气回去。
他站在故乡的荒原,故乡的风依旧,故乡的星辰依旧,故乡的草木依旧,儿时的嬉闹声破空而来,风依旧低低地刮过山谷,他在心里默念着:只是,当年,生活在这片热土和星空下的人声和时光啊,你们都去了哪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故乡的荒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