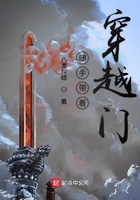8月28日,星期三,芝加哥市中心的格兰特公园正发生着大规模和平示威,人们向戴着防暴头盔的警察扔纸片、番茄、石头;而警察释放了催泪瓦斯。会议厅里,美国主要党派的大会也狼烟四起,你简直想象不到比这更精彩的事了。身穿西装的人努着嘴,眼冒怒火,在会议厅里推推揉揉,挥着拳头,代表团冲着话筒大吼大叫,话筒却发不出声音。
冗长的提名演说和投票之后,终于,汉弗莱赢得了民主党提名。但他领导的是一个政党,还是一场内战呢?
大会之后,汉弗莱踏出了党内大门。从东岸到西岸再到东岸,他做了一周的全国旅行,每站人气都跌落几分。他遇到了反战活动家的愤怒呼声,这证实了法律秩序献身者的推测,不管民主党人走到哪里,尖叫和混乱就跟到哪里,也提醒了鸽派,汉弗莱是亲战的。旅行每一站,他同样被没有遇到的人伤得很惨。在德克萨斯,约翰·康纳利冷落了他。在加州,杰西·昂鲁和萨姆·约蒂也一样。
他对费城的大学生说:“我认为,无论谈判与否,我们都能在1969年初或1968年底开始撤出部分美国军力。”次日,约翰逊未经事先通告,出现在新奥尔良的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不动声色地断了他的路:“没人能预测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他还是一样管着汉弗莱的嘴。在人们看来,精力旺盛的汉弗莱开始变成戈德华特那类分裂政党下不得志的候选人了,还整天说错话。《新闻周刊》办了一个选举人投票项目,标题是“汉弗莱会得第三名吗?”
一些新政论拥护者正考虑投给总部在伯克利的和平自由党,埃尔德里奇·克里夫是该党的候选人。一场攻击事件更推动了这股趋势:大会结束后,芝加哥警方在破晓前突袭了希尔顿酒店15楼的麦卡锡总部。警方称15楼的房客一直在冲他们扔东西,所以他们把人们从床上揪起来打了一顿。往上9层的汉弗莱助手听到了尖叫声,
但他有关会议周暴力的唯一公开评论就是:“我们不应继续揣测,认为戴利市长做了什么错事。”他的首席政治副手解释说:“现在不管做什么,都没办法让和平分子站到我们一边了,除非要汉弗莱在时代广场对着镜头对约翰逊的肖像撒尿——即使这样他们还会说‘你早干什么去了?’”
极少有总统竞选人像尼克松一样,在领先问题上行动迟疑,态度保守。“我不愿将自己隔绝进电视演播室,搞成‘无菌竞选’的样子。”单单从字面上看,确实如此。他没有将自己隔离进电视演播室,也没有搞成“无菌竞选”,但他在窃听上搞了不少创意。在他宣布开始全国大选的声明中,他称自己发现了延缓讨论芝加哥大会和越南问题的方法,而这时相当敏感的谈判已经在巴黎进行。这是现代尚未有人使用过的策略之一。之前,从未有候选人如此致力于对如此庞大的公众透露尽量少的信息。
鲍勃·霍尔德曼已经完美地将游戏计划好了。尼克松通常每天只举行一次集会,新闻摄像机将影像拍在赛璐珞上,然后这些珍贵的胶卷盒就被运到纽约进行显影。这样,尼克松新闻就离机场最近,刚好赶得上晚间报道。媒体为显示公正,通常会播一段民主党片段,一段共和党片段。尼克松的工作人员总是帮助制作人找出最重要的演说片段,而汉弗莱每天要赶十几场,制作人完全有机会找到最有新闻价值的镜头,例如失态、关于越南问题的前后不一含糊其词和一些大叫“杀人犯”的嬉皮士。
其余时间,尼克松休息,与赞助者见面,仔细阅读一本由二十多岁的研究助手团队不断更新的摘要,致力于回答可能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助手们用普鲁士般的高效,赶在晨报和晚报的截止期前投递着意见书。甚至为集会上共和党的象征物大象都做好了妥当的准备:备好了灌肠剂以防尴尬局面发生。
他不能禁止媒体与他接触,因为万事都可能变成新闻报道。所以,他给了记者团“见缝插针的采访”,即在飞机降落、空乘要求每人回到座位之前,在候选人专厢里采访两分钟。记者好像并不介意。莫里斯·斯坦斯为他筹集了2400万美元,都换做了数不尽的鸡尾酒和美味餐点。据一位英国记者的形容,飞机上的媒体一直处在“惊奇而懒散”的状态中。另一边,汉弗莱最大的资助人是总部在明尼苏达的冷冻食品大亨杰诺·鲍洛奇。显然他的公司有很多开胃熏肠库存,熏肠代替了鸡尾酒,在清晨中午和晚上持续供应。
尼克松获得了强烈关注。《新闻周刊》发出了第一周快电,称:“他在欢呼的人群中行动自如,形象稳重而自信,笑容魅力四射,讲话镇静而条理。”还提到了每一站汹涌的青年浪潮:“不管他出现在哪里,都引发孩子们的大叫和上蹿下跳——是的,上蹿下跳。”这些“孩子们”应该是嬉皮士。每次他们为了见尼克松而露面时,媒体就开始报道。
另一股影响巨大的力量是电视评论节目,新罕州做的只是初步的尝试。罗杰·艾尔斯将它称作“角斗场理念”。之前他曾把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句话制成了匾,挂在办公室:“荣誉属于切实身在角斗场、满脸蒙着尘土汗水和血的人”,而不是“指指点点,说强者是如何跌跤、行动者怎样做得更好的人”。媒体在电视监控器上看着节目,而尼克松在定制的圆形蓝地毯讲台上发表声明,普通市民讨论小组围着他坐成半圈,坐在露天看台的200名忠实支持的观众前。传奇的俄克拉荷马大学足球队教练兼ABC彩色频道评论员巴德·威尔金森担任司仪。
前圣迭戈联合报编辑、新闻秘书赫伯·克莱因警告说新闻人可能会有不满。弗兰克·莎士比亚说,这是必须要担的风险。如果放他们进来,他们只会谈论摄像机、灯光和给观众做指示的先期准备人员。媒体应该看到的是“不多不少,和伊利诺斯起居室电视里看到的一个样”。莎士比亚这么告诉克莱因,观众是布景的一部分,是为了“几个脸部特写镜头”的“鼓掌机器”。
电视观众看到的第一眼是预录的影像,车队在明显刚结束过现场集会的当地街道行驶,候选人做出标志性的双V姿势,挥舞着手臂。“候选人本人来个简单的游行,这样人们就能对马上要出现在电视里的人产生现实的亲切感。”一位年轻助理、前中学英语教师威廉·加文说,他主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描述如何给尼克松进行电视再包装,因此被招进了团队。这样,观众会产生在熟悉地方见到名人的激动心情。在芝加哥,这个方法特别有效——民主党大会溅满鲜血的街道,被满怀敬慕、穿着整齐的共和党民众救赎了。
节目是按区域放送的,这样尼克松就可以根据地区差异量身定做不同的信息。在北卡罗莱纳州快速发展的新南方都市夏洛特市,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刚提出针对反学校种族隔离的诉讼时,他就胆大包天地断言了最高法院关于布朗诉教育局一案的1954决议。接着他补充了一点作为缓冲:“要使用联邦财政力量扣留资金来执行法案的话,就太过头了……我认为,活动应该被严密审查,在很多案子中,活动应当被取消。”
提问的小组成员未经排练,但也只是舞台效果的一部分。他们就像二战混杂的野战排:这里有一位犹太内科医生,那里有一位支持移民的团体主席,还有一两位超员的新闻人,以显示角斗场上的男人没有回避他们,还有一位乡村主妇和一个商人。在费城,他们遇到了一点障碍,犹太内科医生被发现其实是个心理医生。
艾尔斯有了替换的主意:“一个脾气暴躁、拥护华莱士的好人出租司机。不错吧?他坐在这边,说‘行了,迈克,这些黑佬怎么了?’”尼克松可以在支持“温和”版本的观点时,表现出对粗鲁言辞的憎恶。艾尔斯走遍了附近的出租车站,找到了一个符合形象的司机。
轮到一个黑人小组成员提问。他问:“法律和秩序对您意味着什么?”
尼克松答:“在我看来,法律和秩序必须与公正结合。现在,这是我想要领导美国达到的目的。我想要值得尊重的法律与秩序。”
小组的一位记者可能问了唯一比较棘手的问题。这有另一个正面影响:让尼克松看起来像个诚实可欺的殉道者,而记者像个自大的卖弄者:
“你说鲁格教授‘呼吁’越南的胜利,但据我回忆,他完全没这么说。这就是我所说你在这类节目上躲避问题的能力。现在,实际情况是——”
“哦,麦肯尼先生,我知道实际情况如何。我知道。”
“实际上教授没有说他‘呼吁’胜利——”
“确实没有。麦肯尼先生,我相信我确切引用的、同时也是他所说的,是他会‘迎接即将临近的越战胜利’。”
“这完全是两码事。”
“麦肯尼先生,你想的话可以自己进行区别,但我现在要做的是,将问题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请他们自己决定语义差别。‘呼吁’和‘迎接’越战胜利的区别。”
制作人很兴奋,他们的候选人坚定而冷静地通过了试炼。这符合他们的叙述:尼克松已经历了各种困难,变得更加强大而智慧。化妆一丝不苟,面容热切、严肃而专注,既强硬又富有热情。牙齿雪白,双手放松。深色眼睛不过分凹陷,低低的下颌不过分松弛,在灯光下恰到好处。不论哪个角度,执行手段都与1960年截然不同。这就是电视的力量。
只有一张有魅力的新面孔才能领导共和党,这个命题曾引发了麦克卢汉一派的思考。尼克松团队利用麦克卢汉来兜售尼克松,摧毁了公众对他“乏味又惹人讨厌”的认识。艾尔斯分发了《了解媒体》一书的节选,麦克卢汉教授在里面赞扬了尼克松在1963年是如何谦逊地在杰克帕尔秀节目上展现他不算很好的钢琴水平。
实际上,1968年竞选中也策划了与帕尔秀中类似的时刻。
电视是美国最根深蒂固的媒介,企业企图控制自己的全国性品牌,一致利用了三大广告网络来覆盖底层大众。只有两个例外——CBS的“斯马瑟兄弟喜剧时间”本来是一档综合性节目,后来弟弟汤米·斯马瑟在节目中引入了新左翼话题,使电视网执行官大为惊骇。“鲁旺和马丁搞笑集”(与静坐抗议、时事宣讲、嬉皮士集会有所关联)是有意设计来控制暴动者侵入主流的新文化能量。它采访过一个体态巨大、头发浓密的假声民歌手小提姆,一个冷漠的纳粹喜剧演员,一个性感的身体上印着迷幻药口号的戈戈舞女,还有更多令人无法想象的性讽刺。
1968年9月16日周一,它采访了理查德·尼克松。
搞笑集的编剧之一是给尼克松编过笑话的保罗·凯斯。其中的一个玩笑是要不同的名人说出一句不合逻辑的讽刺话:“攻击我。”
一个浑身湿透的嬉皮女郎接了一个电话,应该是洛克菲勒州长打来的:“哦不,我觉得我们不能让尼克松先生也做这种‘攻击我’游戏。”
屏幕上映出了尼克松著名的削鼻梁和55岁的面容,配以自我调侃的冷漠而困惑的声音:“攻击我?!”
汉弗莱本来是活力十足的,如一个快乐的斗士兜售着他的快乐政治。没上搞笑集节目令汉弗莱后悔不迭,也是导致他大选失利的原因之一。
汉弗莱无法喘息。尼克松的电视广告创新十足,制作人金·琼斯是一位从未导演过广告的前海战摄影师。吸引竞选团队给予天价资金支持的是他的一部震撼视觉、毫无叙述的纪录片《战争的面目》,追踪了一支海上陆战队在越南长达97天多的战争情况。当尼克松媒体团队观看片子时,唯一的女性观众出去了三分钟,错过这一盘录像:“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之后的20分钟,全场鸦雀无声。
尼克松的广告能不加叙述,只用音乐和公开演讲片段的声音。电视专家哈里·崔利文对片子的美感自豪万分,甚至拿去给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放映,希望能加入馆藏。
另一队美国形象制造人惊恐不已。新闻部门和部门内人员将自己看作广袤荒地里的绿洲,为此深深自豪。新闻广播网络在50年代末的问答节目丑闻后就把滚滚的钱投入了新闻里,失利的领袖利用机会洗白自己形象,维护珍贵的使用公共电视广播的政府特许权。电视新闻俨然成了美国市民生活的道德中心,既独立又具有公众精神。催生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布尔·康诺在伯明翰的消防水管是他们拍的,导致了1965年选举权法案的埃蒙德佩图斯桥也是他们拍的。
NBC的“重磅晚间新闻”由亨特利·布林克里报道,它对自身道德水准最有自信。他们找到了芝加哥专门拍摄民权和反战运动的年轻人卢·科赫,想要了解民主党大会会不会有暴力发生。他知道有哪几方参加后,回答,绝对会有。会议周期间,科赫带领着团队在街道和公园采集暴力的影片。
他对他们制作的东西极其骄傲,这相当于1968年版本的布尔·康诺消防水管事件:光荣的道德剧;恶魔不加掩饰,造访无辜人群。在片子播出后,他赶往NBC在商品市场的总部。作为反战运动同情者,他认为自己极大地推动了他们的进程。
分配总编辑要他帮忙接电话,接线总机被打爆了。
第一通电话:“我看到警察打孩子的一幕了——警察没错!”
另一通:“他妈的共党分子!”他骂的是NBC,好像暴动是他们引发的一样。
有人看到的是高尚的警察无辜地自我防卫,有人骂电视广播网络雇警察打孩子好刺激收视。科赫被事情的发展震惊了,请了6个月假进行灵魂寻觅之旅。
媒体使芝加哥团结在一个信念之下:他们是英雄、先知和殉道者。《纽约时报》的汤姆·维克写道:“真相是,街上的是我们的孩子,芝加哥警察打了他们。”艾尔索普写道:“在芝加哥,我人生第一次发现,美国法西斯是有可能以某些形式存在的。”所有传媒的最高行政官,《纽约时报》的出版人阿瑟·苏兹贝格,《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的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时代公司总编赫德利·多诺万,以及《洛杉矶时报》出版人奥蒂斯·钱德勒给戴利市长拍了一封前所未有的电报,斥责了他对待新闻人的方式,他们“不断被警察挑出来殴打……以阻止记者报道这起警方与示威者的对抗行为,美国大众有权利知道这起行为。”
接着他们明白了,美国大众并不这么想。
很多读者来信大多是针对芝加哥会议的,倾向于另一种叙述。
“易比派和麦卡锡的支持者不仅冲警察和国民警卫军扔了啤酒罐和烟灰缸,还从15楼扔了塑料袋装的大便和砖头……”
“我的邻居是芝加哥警察,被指派保护希尔顿酒店不受暴徒侵犯。周一周二他连续工作了16小时,周四早晨他回家时遇到了我,全身覆盖着暴徒扔的大粪。”
不为所动的芝加哥新闻人指出,这些信编的明显不怎么样。换班之后,警察要回警局,他们就让他一身大便地进去了?他一身大便地直接开车去见妻子孩子?还有,在希尔顿酒店15楼,去哪找得到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