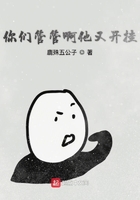“嗯。”司徒艾静眼神坚定地点了点头,再也不敢耽搁,往山里跑去。
司徒艾静一路急跑,只一盏茶的功夫便到了山脚下。看着满山遍野的野草,她深吸了口气,低下身子开始仔细地寻找起来。
春日的太阳虽然不似夏天般炙热,可长久地曝露在太阳下,司徒艾静也被晒的头晕眼花,汗水已经浸湿了衣服。抬头看了看太阳的位置,猛然发现似乎时间已经过了很久,甩了甩发晕的头后低下了头继续寻找起来。
司徒艾静只觉得头晕的更厉害了,腿开始发软,一下没站住,跌坐到了地上。
“不知不觉都快到山腰了啊。”她看了看离自己不远处的山崖,暗自乍舌,还好没走过去。
“啊。”手刚撑住地,手心处便传来一阵刺痛感,司徒艾静低下头一看,顿时大叫出声。司徒艾静瞪着大眼睛,趴在泥地上仔细看着刺痛自己的罪魁祸首,一株枝叶似针尖的草状植物。看着看着,总觉得很面熟,似乎在哪里看过。
“对了。”像是想了起来,司徒艾静慌忙从怀中取出大夫给的画纸,“就是它了。”
她小心翼翼地将草药拔出,拿出手绢仔细地包裹好,轻轻地放进了怀里。终于找到了救命草,她站起身来长舒了口气,抬头看了看天色,发现时间快到了,慌忙地迈开脚,往村子跑去。
她长这么大好像还没这么拼命地跑过,就算小时候被小朋友追着打,也没现在这样着急。白皙水嫩的脸颊此时已经绯红一片,光洁的鼻头处一层细密的汗珠,从鬓角处滑落的汗珠映着午后的阳光,闪着晶亮的光芒,仿佛耀眼的珍珠,从脸庞跌落到地上,一下摔的粉碎。
“孙伯,找到了。”司徒艾静叭地一声推开房门,语气兴奋而激动。
“快拿来我看看。”孙伯听后,站起身伸出了手。
司徒艾静小心地从怀里掏出手绢,谨慎地送到孙伯手里,看着孙伯查看着草药,全身紧张地绷直着。
“嗯。”仔细查看后,孙伯终于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此草。”
“呼。”司徒艾静心中大石落下,拍了拍快要跳出胸口的心。
“切碎,三碗水熬成一碗。”孙伯将草药重递给司徒艾静,叮嘱道,“小心看火,千万别让汤水溢出来。”
“好。”司徒艾静接过草药,快步走向厨房。
大约一柱香的时间,司徒艾静双手捧着冒着热气的药汤,一步一挪地走了进来。
“你把他扶起来。”
司徒艾静上前将司马庆宇扶起,可他处于晕迷中,完全没有力气支撑自己,无奈,她只能抱着他,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
孙伯将盛满药汤的汤匙送进司马庆宇的嘴里,可他的牙齿却紧咬着,完全喂不进去。
“怎么了?”司徒艾静见状连忙问道。
“这是高热的症状,因为身体很难受,故不自觉地紧咬牙关。”孙伯摇着头将药汤放下,忧心地道,“如果不乘热喂进去,药效就会减半的。”
司徒艾静将司马庆宇放下,看着他紧咬的牙关,心里焦急如万蚁啃咬。
“孙伯,我来吧。”眼看着药汤的热气越来越淡,司徒艾静一咬牙做出了决定。
“你?”孙伯睢着司徒艾静突然红透了的双颊,顿时明白她的意思,惊讶地道,“你可是一个大姑娘啊。”
“人命关天,静儿顾不了那么多了。”
说罢,司徒艾静端起药碗,将药汤含进了嘴里,走向司马庆宇。
此时的司马庆宇呼吸轻不可闻,因为脸被涂黑所以看不出里面已经煞白一片,犹是如此,那灰白色的嘴唇也看的司徒艾静揪心不已。
此刻,她只知道不能让他死,自己的清白、名誉都已经不重要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将饱含药汤的嘴唇贴紧了男人的唇,舌尖吃力地橇开他紧咬的牙齿,将温热的药汤一丝丝地送入他的口中。
良久,一口药终于全部喂进了司马庆宇的肚子,司徒艾静起身,只觉得双颊处烧的厉害,一颗心也似乎要跳出来,连忙捂住胸口,闭上眼深深呼吸着。
“你先出去吧,我要在他的身上施针,让药效发挥的更快些。”孙伯看出司徒艾静对床上男人的不一般,故意将她撵出去。
孙伯是看着司徒艾静长大的,看着她对这个不明不白的陌生男人动了情,他心里很是担忧。
司徒艾静也想出去洗个凉水脸,否则她还真担心自己会烧起来呢。
“孙伯,用过晚饭再回去吧。”司徒艾静拉住疲惫的孙伯,挽留道。
“不了,你婶子还等着我回去呢。”孙伯对她笑了笑道,“放心吧,他已无大碍,最迟明日便可醒来。”
“孙伯,慢走啊。”司徒艾静放心地笑了起来,冲孙伯摆着手道别。
天黑了下来,昏黄的烛火在房间里不知疲累地跳跃着,偶尔蹦出一个火花,啪地轻响一声。
司徒艾静靠坐在床边,凝视着床上熟睡的男子。此时他的呼吸均匀而有力,嘴唇红润一片,看来,病确实是好了。
紧盯着那薄而红润的嘴唇,想起刚才喂药的情景,情窦初开的小女孩再次羞红了脸。这是她第一次亲吻一个男人的唇,虽然是迫不得以,虽然是一厢情愿,可甜蜜的滋味却深种在了心田。轻闭上眼,疲累了一天的女子沉沉地睡着了。
“嗯。”一声轻轻地低吟,惊醒了熟睡中的司徒艾静。
司徒艾静揉了揉朦胧的睡眼,发现天已经大亮,自己竟然就这样坐着睡了一夜。
“水。”
听到声音,司徒艾静立刻跳起身,倒上一杯清水,轻轻扶起司马庆宇,小心地喂给他水。
喝过水,司马庆宇终于恢复了意识,缓缓地睁开了干涸地双眼。
“你醒啦!”司徒艾静见司马庆宇睁开了眼,开心地询问道。
“你是谁?”刚醒来的司马庆宇还有一些迷糊,看着眼前陌生的女子,警惕地问。
“我是司徒艾静啊。”
“司徒艾静。”司马庆宇想了想,终于想起那个手拿猪肉的小女孩,这才松了一口气道,“我怎么在这里?”
“你已经晕了两天了。”司徒艾静提醒道,“孙伯说你前不久刚受了重伤,再加上前日淋了雨,伤上加伤,病的很重呢。”
“两天了?”司马庆宇一听惊地想要坐起身,可是四肢却不像是自己的般,完全不听使唤。
“你别动。”司徒艾静连忙拦住他,将他按回床上道,“你现在还很虚弱,不能乱动的。”
司马庆宇不相信她的话,而且他也没有那个时间再耽搁了,他再次挣扎着想要坐起身来,无奈不管怎么努力,手脚仍旧使不上任何力气,他有些绝望地躺回床上,痛苦地闭上了眼。
“你别急嘛,再急的事也要等身体好了才能去办啊。”司徒艾静看着他痛苦的模样,心也跟着疼了起来,“再说,村口的大水还未退去,你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啊。”
“你让我静一静。”良久,他终于开了口,只是语气却十分的不善。
“好。”司徒艾静张了张嘴,还想说些什么,可是看到他难过的样子,最终没有再开口。
起身,走出房间,轻声关上房门。司徒艾静靠在房门上,静静地听着房里的声音。想着一门之隔的男子,红了双眼,此时她与男子的关系不就像这扇门一样吗?她想要推门进去,而他却冷冷地赶她出来。
老天总是这么爱捉弄人,我爱的不爱我,爱我的我却不爱,不爱的却死命地拉到一起。缘由天定,份在人为,司徒艾静相信,只要真心诚意的对他好,他有一天总会看到自己的真心的。
思及此,她仰头将眼圈里的泪水逼了回去,抿嘴一笑走进了厨房。
司马家“找到没有?”陈秋莲焦急地问着刚走来的司马楚谦。
司马楚谦摇了摇头,无力地立在一旁。
“这可如何是好?”陈秋莲一听,脸色顿时煞白一片,对跪在一旁的司马宝儿骂道,“看你做的好事,如今找不到你哥哥,我们都得人头落地。”
“娘。”司马宝儿不满地看着陈秋莲,皱眉道,“你怎么也不关心下大哥的身体?大哥死里逃生,身体还未恢复便独自漂泊在外,你可曾担心过他?”
陈秋莲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双手用力地绞着锦帕,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明日便是迎娶公主之日,今日宫里的崔公公便来视察相关事宜,还说要见见你大哥,被我以他身体不好为由婉拒了,可是明日该怎么办?无论如何也是瞒不过去的呀。”良久,陈秋莲才愰愰地开口。
“大不了将司马家献给皇上,我们重新来过便是。”司马宝儿抬起小脸,一脸的绝决。
“你真是太幼稚了!”陈秋莲啪地将桌子拍的震天响,怒瞪着小女儿道,“抗旨可是要杀头的。”
“我不怕。”司马宝儿嘟起了小嘴,不理会母亲的怒火。
“啪。”清脆的声音响起,司马宝儿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母亲,那个视她如珠似宝的母亲。
“娘。”司马楚谦见小妹被打,连忙上前拉住盛怒的母亲道,“唯今之计,您还是赶快进宫向大公主解释下,先求得大公主的谅解吧。”
陈秋莲狠狠瞪了司马宝儿一眼,背转过身,思量了片刻后,转回身道,“先这样吧。”
“我先且进宫。”陈秋莲手指着司马宝儿警告道,“你个死丫头好好跪在这儿,我回来之前不许起来。”
说罢,便由赵妈妈扶着向大公主府赶去。
等陈秋莲走后一会儿,司马楚谦上前扶起妹妹,看着她白嫩脸上的红印心疼无比。
“你也是的,怎么也不跟二哥商量下呢?”司马楚谦责备道,“我们三兄妹一条心,有事也要一起承担不是吗?”
司马宝儿红着眼圈点着头,脸上火辣辣的疼痛让她想起刚才母亲的狠心来,委屈之极下,抱住二哥痛哭起来。
“司马家有今天,全靠娘舍命打拼。如今眼看着司马家要毁了,娘自然不能接受,你也别怪娘。”司马楚谦知道妹妹委屈,轻拍着她的背,安慰着。
唉,从今以后,司马家将迎来怎样的风雨,司马楚谦真是不敢想。他只能希望老天能给司马家一条活路,至少不要有人为此丧命才好。
醉香楼,位于圣龙国国都中最热闹的商业街中最黄金的口岸,不知有多少生意人眼红着这块宝地,垂涎着。如果他们知道几天后,醉香楼便真的如他们如愿的关门闭业了,他们将会是怎样欢心雀跃,鼓掌欢迎呢。
然而此时,醉香楼仍然是圣龙国第一大酒楼,酒楼的第一管事司马楚谦正坐在包厢里独自喝着闷酒。
“扣扣。司马二哥。”随着敲门声响起的还有孟乐欢清丽的声音。
“欠儿。”司马楚谦醉眼惺忪地打开房门,将房外站着的孟乐欢拉进了屋,并端起一杯酒道,“你来的正好,陪二哥喝一杯。”
“司马二哥。”孟乐欢见司马楚谦醉的不轻,拿过酒杯放到一旁,扶住摇摇晃晃的男人的问,“怎么我回了一趟峨眉,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司马楚谦看着孟乐欢,看着这个跟大嫂七分相像的女人,再也压抑不了心中的苦闷,抱住她痛哭了起来。
孟乐欢一下懵住了,印象中坚强、幽默的司马二哥,怎么能哭的像个小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这般无助?
“楚谦,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轻拍着男人颤抖的双肩,焦急地追问道。
司马楚谦被孟乐欢的问话惊的一下清醒了不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趴在孟乐欢的肩头哭的那么悲惨,想自己堂堂男儿,竟在女子面前落泪,他狠狠打了自己一巴掌,怎么可以让人看到自己这么脆弱的一面,特别是在孟乐欢的跟前。
“你别这样。”孟乐欢见司马楚谦打自己耳光,心疼地捉住他的手,温柔地道,“见你这样,定是家中发生了大事吧?告诉我,我也不是外人哪。再者,我的心意你也不是不知道吧?”
“欢儿。”司马楚谦看着孟乐欢真诚而深情地目光,深吸了口气,缓缓地开了口,将心中的痛苦全部告诉了她。
孟乐欢张大了嘴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怎么会?自己才走了多久啊,司马家竟然发现这样的事情,堂姐居然失踪了,如今连姐夫也没了踪影,而司马家面临着欺君之罪,随时可能家破人亡。
“不行。”孟乐欢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气愤地拍桌而起,“我不能坐视不管,我去找堂姐和姐夫。”
“欢儿。”司马楚谦握住孟乐欢的手,感激地道,“原本我打算亲自去寻找大哥的,可是家中还有母亲和妹妹,实在不敢走开,这事儿急的我夜不能寐。如今有你出马,我的心便可放下大半,再怎么说你也是峨眉亲传弟子,一身武艺也不会有何危险。”
“放心吧。”孟乐欢反握住司马楚谦的手,眼神坚定,“我一定尽快将他们寻回,二哥你只管操心家里便是。”
司马楚谦内心感动万分,千言万语突然硬在了喉咙里,唯有将孟乐欢紧紧地搂在怀里,久久不愿分开。
孟乐欢告别了司马楚谦,本想立刻上路的,可是一想到好姐妹司马宝儿,不知这个单纯的小丫头经过这样的变故会伤心成什么样,决定临走前去瞧瞧她。
“宝儿。”孟乐欢走到司马宝儿的房门前,敲了敲门。
“谁呀?”司马宝儿打开门,红肿的眼睛看着门外的孟乐欢,怔怔地呆了片刻,才如梦初醒般地抱着她大哭起来,“欢欢姐,大嫂不见了,小梅死了,大哥出门去找他们了,我该怎么办啊?”
孟乐欢见着瘦了一大圈的司马宝儿,悲从心中起,不禁和着她哭了起来。
也不知道哭了多久,两人终于哭累了,相拥着走进屋里相对而坐。
“我要去找堂姐和姐夫。”孟乐欢道。
“真的吗?”司马宝儿原本趴着的身子猛地坐直了,双眼闪着亮光道,“我也去。”
“你乖乖地呆在家里,说不定明日你家便会发生大变故,你要在夫人身边照顾她啊。”孟乐欢抚摸着司马宝儿的脸庞,神色万般凝重。
“不要,是我私自放走大哥的,娘现在恨死我啦。”司马宝儿红唇一扁,眼圈又红了起来。
“别哭了。”孟乐欢见样,连忙拍了拍她的手安慰道,“再怎么样也是你的娘不是嘛,过一会儿就好了。”
“不行,我呆在家里会疯的。”司马宝儿站起身,拉着孟乐欢的双手不停地摇晃,哀求着,“欢欢姐,你就带我去吧,求求你了。要是呆在娘身边,我真的会被她逼疯的。”
孟乐欢见司马宝儿如此坚持,如此可怜的模样,心一软,最终咬着牙点头同意了。
“谢谢欢欢姐。”司马宝儿开心地跳了起来,连忙转过身打开衣橱开始打包行李。
孟乐欢摇着头看着忙碌的女孩儿,心中有些后悔,真不该一时心软答应她,前方的路也不知是吉是凶,万一让她身陷险境可怎么办才好?
她甩了甩头,苦笑了下,算了吧,都已经答应了,她自信自己不会让宝儿出事,如果打不过,逃命的本事她还是有的。
“走吧。”司马宝儿将包袱背在背上,拉起发呆的孟乐欢飞似的向外跑去。
大公主府内陈秋莲紧抿着嘴唇,面色凝重地跪在大厅正中,锦秀则满脸的怒火,圆目怒瞪着陈翠莲。
“你们不怕被父皇砍了头吗?”锦秀伸手指着陈秋莲,手指因为过于激动而颤抖着。
“老身来找大公主,是想求大公主在皇上跟前说说情,容我一些时间,我一定将那逆子寻回来。”陈秋莲深吸口气,稳了稳心神。
“笑话。”锦秀用力甩了甩衣袖,转过身往前踱了两步,背着身冷冷地道,“你以为父皇的威严是任由你们亵渎的吗?你们以为本公主真是没人要了吗?你们就等着为司马庆宇可笑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吧。”
“大公主。”陈秋莲闻言,惊地不顾身份地匍匐上前,抱住大公主的脚,苦苦哀求道,“请大公主息怒,一切都是老身的罪过,要杀要剐就让老身一力承担吧,望公主不要放了小儿和小女吧。”
“滚开!”锦秀厌恶地踢开陈秋莲的手,转回头,阴冷的眸子微眯着,她呵呵笑道,“放心吧,本宫不会让你们这么快死的,本宫会帮你找回司马庆宇,要让他亲眼看着他的母亲和弟妹们死掉,本宫要让他自悔而缢。”
锦秀此时的神情仿佛恶魔般狰狞、可怕,她的每个字仿佛一把尖刀狠狠剐着陈秋莲的心,陈秋莲恐惧地摇着头,几十年未流过的泪水此刻似决了堤的洪水疯狂地涌出眼眶。
“请大公主开恩啊。”陈秋莲尖叫着再次抱住锦秀的腿,全身因为恐惧而剧烈地战栗着。
锦秀见陈秋莲扑上来,连忙向前跨了一步,厌恶地躲了过去。
“你还是回去好好吃一顿吧,等本宫禀明了父皇,你可就要受苦了。”锦秀说完后,没有再停留转身离开了。
陈秋莲看着大公主决然离去的背影,彻底的绝望了。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外表看起来温婉、贤淑的大公主,会是如此冷血的魔鬼,亏自己当初还想让宇儿迎娶她,真是瞎了眼,这样的女人要是真的进了府,宇儿还不知道会生活在怎样的痛苦里。
她撑着虚弱地身体站了起来,恍恍惚惚地往外走去。看来古话说的对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司马家兴旺了这么多年,是时候散了吧。
锦秀出了自己的公主府,坐上马车急急地往皇宫而去。想到司马庆宇居然会为了逃避与自己的婚礼而离家出走,从小大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锦秀彻底地疯了,她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创,强烈地屈辱感让她头痛欲裂。
司马庆宇,我会让你会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吃过药后的司马庆宇感觉好了许多,再睡了一天一夜后,又出了一身的大汗,病已好的七七八八。
身体好了,他背上包袱准备继续出发。
“林大哥,洪水没退,您怎么出去啊?”司徒艾静劝慰道,“不如再等等吧。”
“不能等了。”司马庆宇已经耽隔的太久,心里焦急万分,“我翻后山出去。”
“那可不行。”司徒艾静一听立刻急了,“后山山路险峻,猛兽奇多,不安全。”
“那我也要试一试,不能坐以待毙啊。”司马庆宇紧了紧绑在背上的包袱,抬起脚向外跨去。
“林大哥。”司徒艾静看他固执的模样,一咬牙上前拉住他的手往村口跑去,“我有办法带你出去。”
司马庆宇听她这样说,心里疑惑不已,不明白她会有什么办法。
“你在这儿等等。”到了村口,司徒艾静松开司马庆宇的手,小巧的身影风一般往前跑去。
司马庆宇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始终没见司徒艾静回来,心生奇怪往防洪堤走去。
“上来吧。”临近防洪堤,司徒艾静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条小船,只见她混身湿透了的站在小船上向他招着手。
司马庆宇跳上村民临时搭起的渡头,小心地走上小船。
“你哪里找来的船?”坐在小船上,他奇怪地问。
“这是村里唯一的一条小船,主要在洪水缺粮时到外面买粮用的。”司徒艾静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心里一个劲儿地向老村长道着歉。
“如今我们拿走了船,村民运粮怎么办?”司马庆宇一听也是愧疚万分,连忙道,“把船还回去吧,我还是从后山走。”
“没关系的。”司徒艾静憨憨地一笑道,“今年村子里收成不错,村民们的粮食足够撑过一个月,不要担心啦。”
虽然司徒艾静这样讲,司马庆宇还是过意不去,心里暗暗发誓,只要司马家能过的了这一关,以后一定把村子的泄洪渠修好,再也不让村子淹水了。
“我来吧。”看着司徒艾静吃力摇桨的样子,司马庆宇想要接过船桨。
“你坐着吧,身体还没好完,不能累的。”司徒艾静紧握住船桨坚决不给。
司马庆宇无奈,只好老老实实地坐回船中的小凳上,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发起呆来。
也不知划了多久,终于到了另一个渡头,司徒艾静擦了擦额头细密的汗珠,将船靠进了岸。
“这里是青风镇,我们可以去镇里顾辆马车,大约一天的光景便可到国都。”司徒艾静指着前方的牌坊说道。
“嗯。”司马庆宇点了点头,急不可耐地往镇中走去。
刚进青风镇,司徒艾静便在路口找到了一家租赁站,刚跑进去没多久便一脸沮丧地走了出来。
“怎么了?”司马庆宇见状连忙问道。
“要二百两纹银呢。”司徒艾静拿出干瘪的钱袋,将里面的钱全倒在掌心里,数了数道,“我这里只有二十两。”
司马庆宇摸了摸怀里,都怪自己走的太匆忙,也只是拿了一些碎银而已,摸遍了全身只摸出了五十两。
“还差一百三十两呢?”司徒艾静拿着银子,凝眉想了想,终于,她咬了咬嘴唇,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定般,将手腕上带着一个翠绿的玉镯子拿了下来。
“你去哪儿?”司马庆宇见她转身要走,不知她什么意思,急忙拉住她追问道。
“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就回来。”司徒艾静推开他的手,一个转手便走进了涌动的人潮。
“走吧,我们去顾马车。”不一会儿,司徒艾静走了回来,笑着扬了扬手里的银票。
“你哪里来的钱?”司马庆宇不明白她怎么这么快弄到这么多钱来,一百多两银子,可够她在小村子里生活一年的了。
司徒艾静没有回答问题,只是俏皮地冲他眨了眨眼,便走进了租赁站。
不一会儿,一辆小巧的马车便出现在了他眼前。
“上来吧。”司徒艾静掀开门帘,冲仍在发呆的男人招着手。
司马庆宇一头雾水地上了马车。马车很小,恰恰容的下两人,两人肩并肩地坐着,身体随着马车的晃动而不时接触在一起。司徒艾静不禁羞红了脸,而司马庆宇也颇为尴尬地努力往边上靠。
“饿了吧,吃块饼吧。”沉默地气氛让司徒艾静有些紧张,为了打破沉默,她从包袱里拿出玉米饼递给他。
“等等。”司马庆宇接过饼,无意中撇到司徒艾静的手腕,他清楚的记得,那里应该带着一只翠绿的玉镯子的,这会儿怎么不见了,为了证实心中的猜想,他迟疑地问,“那个银子不会是你当掉镯子换来的吧?”
“呵呵。”司徒艾静慌张一笑,急忙将手抽了回来,低下头默默地啃起饼来。
“你不是说那是你娘留下的唯一信物吗?”他捉住她的手,眼神里满是内疚,“你怎么能为了帮我回去而当掉呢?”
“没关系啦。”司徒艾静努力微笑着,“那些都是身外物,没有它,娘也一直活在我心中啊。”
他哑然失声,沉默地低下头,紧捏着手里的玉米饼,心里五味陈杂。
司徒艾静对自己的情意,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可是心里深爱着孟乐喜的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另一段情。
看着旁边女子纯洁如水的眼眸,他愧疚的无与伦比,为什么老天爷要让自己遇到这样一个璞玉般的女子,他要如何才能偿还她的一往情深呢。
“谢谢你了,以后定会赎来还你的。”为了不让司徒艾静越陷越深,他不得不对她冷漠,希望她看到自己坚决的态度后,会回转心意。
看着眼前瞬间变了神色的男子,司徒艾静不知所以,前一刻还随和有礼的他,这一刻怎么变的这般冷漠,接受不了这样的待遇,司徒艾静转过头悄悄红了眼圈。
马车飞驰在路上,迎面而来的风将车帘吹起半高,一直穿着****衣裙的司徒艾静被风一吹,禁不住打了个哆嗦。
司马庆宇这才发现司徒艾静还穿着湿衣服,恼怒自己的粗心,连忙脱下外衣罩在她瑟瑟发抖的瘦弱娇躯上。
马车马不停蹄地往圣龙国国都而去,天气渐渐暗了下来,车外原本喧闹的街道安静了下来,不知不觉已经跑了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