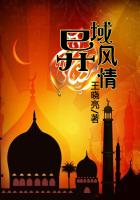对课程目标的探索,始于课程编制科学化的首倡者博比特。他认为,20世纪已进入科学的时代,而“科学的时代要求精确性和具体性”,因此,课程目标必须具体化、标准化。博比特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课程目标的来源问题。在他之前,对课程目标的思考,用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Carnap,R·)的话说,是一种“表达”——对研究者的某种情感愿望、主观价值取向的传达,缺乏相对客观的依据。这在博比特看来是有问题的。他从事课程编制工作的特殊经历,促使他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我们不知道,我们首先应该根据对社会需要的研究来确定目标。我们以为教育仅仅是由教一些熟悉的学科组成的。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显露人们潜在能力的过程,它同社会条件有特殊的联系。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学习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没有认识到,在这种显露过程中有效的所有工具或经验,是正确的工具和经验;在这过程中无效的任何东西,无论它在当时如何神圣、如何广泛地被使用,都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教育是为学生将来的成人生活作准备,因此,课程目标应来自对广泛的人类经验和现有社会职业的分析。在1924年出版的《怎样编制课程(HowtoMakeaCurriculum)》一书中,他曾基于对人类经验和职业的分析,提出了10个领域中的800多个目标。今天看来,博比特的课程目标取向显然是偏颇的,但他明确提出了目标问题,试图给目标的确定一种实践性或某种形式的科学客观性,从而使课程目标的确定成为应该进行批判、探究的问题,而不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这样,对课程目标的探究随着课程探究的科学化而走上了科学化的路程。
1·行为目标
行为目标是随着课程研究领域的独立而出现并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课程目标模式。它是把学校要达成的教育目标,以具体的行为方式的形式加以陈述,指明教学活动结束后在学生身上发生的行为变化。行为目标的设计,旨在目标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用泰勒的话说是为了“有助于选择学习经验和指导教学”。
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系统发展了博比特所提出的问题。他认为,课程目标应由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对学生的研究、对学科的研究等三种来源而得出,并要通过教育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筛选。在目标确定之后,泰勒强调,应当用一种最有助于学习经验的选择和指导教学过程的方式来陈述目标。这样的方式,在泰勒看来,应该是“既指出要使学生养成的那种行为,又指明这种行为能在其中运用的生活领域或内容。”这样,目标实际上包括“行为”和“内容”两个方面。泰勒批评了三种常用的陈述目标的方式:一是把目标作为教师要做的事情来陈述,如介绍进化论、演示归纳证明的性质等;二是列举一门或几门学程所要涉及的课题、概念、概括或其它内容要素;三是采取概括化的行为方式这样的形式,但却不能比较具体地指明这种行为能够运用的生活领域或内容。这些陈述方式都没能做到“内容”与“行为”的有机结合,因而提出的目标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对课程编制的其它环节指导不力。泰勒的努力,即是试图通过以行为方式陈述目标来改变这种状况,因此,泰勒是行为目标的创始人。
真正将行为目标发挥到极致的,是泰勒的学生布卢姆(Bloom,B·)以及克拉斯沃尔(Krathwool,D·R·)、哈罗(Harrow,A·J·)等人所建立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布卢姆从课程评价的角度出发,首先将教育目标划分为三大领域:认知、情意、动作技能。在每一领域中,根据能力的复杂程度和品质的内化程度,找出具有递进关系的层次,形成目标的阶层。而对每一阶层,都指出适宜的行为动词,以使目标切实落实到学生的行为方式变化上。这样,课程目标被表述得相当具体,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便于教师把握并用于课堂教学,便于对课程进行评价。行为目标模式因“教育目标分类学”得以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成了一项国际性的普及。这种目标模式曾于80年代在我国的教学实践中产生一定影响,引起一些人的研究兴趣。行为目标的提出,引起了诸多争议。早在20年代初期,89岁高龄的哈佛大学名誉校长埃利奥特(Eliot,C·W·)就指出,教育目标的标准化是与真正的教育过程相悖的,“真正的教育目的是使个体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不仅是在童年期、青春期,而且在整个人生中都得到发展。在劳动、学习和家庭生活方式中固定的标准,是人的身、心和精神充分发展的敌人。”这一评价可谓一语中的。行为目标的实质是追求教育过程的可控制性,其特点是简单明了、易于把握,它对于保证一些相对简单的教育目标的达成是有益的。但是,如果试图用行为方式陈述所有课程目标,显然是不适合的,因为教育的真正价值,绝不仅仅是形成一些可以观察到的行为。意识不到这点,行为目标就会成为强加于教学过程的枷锁,师生的主体性都会在其框束下泯灭。
2·生长性目的
我国有学者把“生长性目的”译为“展开性目的”。我们认为,英语“evolving”一词尽管也有“展开”的意思,但“生长”和“展开”的汉语意思略有不同,前者是一个有新质的东西生成的过程,而后者则是仅把原有的东西开发、展现出来的过程。特别是从教育史上看,确实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儿童发展观:福禄培尔即是典型的“展开”论的代表,他把发展看作是把儿童既有的潜能运用适当的方式加以引导而开发出来的过程;而持“生长”说的杜威则有所不同,他认为发展是儿童既有经验与环境相互作用而不断实现的动态平衡。因此,我们使用“生长性目的”可能更为严谨一些。
生长性目的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杜威“教育即生长”的命题。如所周知,杜威反对把某种外在目的强加于教育,在他看来,教育是儿童经验的不断改造,是儿童的生活和生长,生活、生长以及经验的改造本身即构成了教育的目的。只有这样将目的融入教育过程中,才能真正促进儿童的生长。因此,在杜威看来,良好的教育目的应具备这样几个特征:(1)它必须根源于受教育者的特定个人的固有活动和需要(包括原始的本能和获得的习惯);(2)它必须能转化为与受教育者的活动进行合作的方法;(3)教育者必须警惕所谓一般的和终极的目的。这样,目的就不是一种指向遥远的未来的结果,而是引导着现在的生长和发展的手段,它是从各个特殊的现时状态中自然引发、生长出来的。
斯腾豪斯的过程模式给出了生长性目的的另一种意义。由于目标模式招致了太多的批评以及其本身的缺陷,斯腾豪斯放弃了“目标”一词。而从彼得斯那里吸收了“过程原则”(principlesofprocedure)。他主要考察了训练(使学生获得动作技能)、教学(使学生获得知识信息)以及归纳(使学生获得以知识体系为支持的批判性、创造性思维能力,这是使学生进入“知识的本质”)三种过程。他认为,训练和教学过程可以用行为目标来陈述,而归纳的宗旨却恰在于其不可预测性,故不能用行为目标表达,因为这会导致“质量标准的形式化而降低质量标准”,也会使知识工具化而丧失内在价值,而且其所走的分析途径还会使知识变得支离琐碎。
不仅如此,在斯腾豪斯看来,与批判性、创造性的思维能力相比,技能和知识信息都是次要的和工具性的,故训练和教学理应服从于归纳的过程。因此,与泰勒不同,他主张课程编制可以规定教师要做的事情以及规定要处理的教学内容,关键的是,教师不能把这些规定看作教育的目的或结果,用以评价学生的成绩,而是在处理这些事情和内容的教学活动过程中,对学生的发展持一种审视、研究、批评的态度,从而引导其不断深入发展。这样看来,斯腾豪斯实际上是用一种一般的发展目的(批判性、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取代了行为目标,把教师从被“防备”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斯腾豪斯明确指出:“没有教师的发展就没有教育的发展,而且发展最好的手段不是通过明晰目的,而是通过批评实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斯腾豪斯提出了“教师是研究者”的命题。与行为目标相比,生长性目的突出了课程的价值取向。行为目标把注意力放在目标设置和陈述的技术上,避开了课程的价值问题,或者说,它把所处时代要求的科学效率化追求看作是课程编制理所当然的价值取向,无需予以审视批判。这决定了行为目标的“技术性”特征。生长性目的则重新抓住课程中的价值问题,强调教育的内在价值,即教育是为了促进儿童身心某种“形式”的发展。在这点上,它超越了行为目标的即时的、功利的色彩。某种程度上,这是向博比特当年反思批判过的关于目的思考的回归,因而从技术角度看,它又从追求具体性、可操作性的“目标”(objective)层面,回到了具有一定概括性的“目的”(purpose)层面上。但是,作为课程目的,特别是吸收了行为目标的积极因素,生长性目的不再停留于哲学思辨,而是致力于课程目的向课程实践的靠拢,用理想的目的引导实践过程。总之,生长性目的注重学生批判反思能力的发展,并把这种追求用以规范实践过程,要求课程的实施应当以不压制学生的批判反思为准。这里,学生主体性的培养被看作是目标,而教师主体性的发挥则是手段,是目标得以实现的保证。
3·表现性目标
表现性目标是美国课程学者艾斯纳(Eisner,E·W·)提出的一种目标形式。受其所从事的艺术教育的启发,艾斯纳区分了课程计划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教育目标:教学目标(instructionalobjective)和表现性目标。
教学目标旨在使学生掌握现成的文化工具。它是在课程计划中预先规定好的,这种规定明确指出了学生在完成一项或几项学习活动后,所应习得的具体行为,如技能、知识条目等。它通常是从既有文化成果如各种学科中引出,并以适合于接受它的儿童的方式进行表述。教学目标对大部分学生来讲是共同的。艾斯纳认为:“在一项使用教学目标的有效课程实施中,学生最后形成的行为,与所给出的目标是一样的。”
表现性目标则与教学目标殊异,它旨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强调个性化,因而超出了现有的文化工具并有助于发展文化。表现性目标不是规定学生在完成一项或多项学习活动后准备获得的行为,而教育“遭遇”:指明儿童将在其中作业的情境、儿童将要处理的问题、儿童将要从事的活动任务,但它不指定儿童将从这些遭遇中学到什么。“一个表现性目标既向教师、也向学生发出了一份请帖,邀请他们探索、追随或集中争论他们特别感兴趣或对他们特别重要的问题。一种表现性目标是唤起性的,而非描述性的。”表现性目标意在成为一个主题,学生围绕它可以运用原来学到的技能和理解了的意义,通过它扩展和拓深那些技能与理解,并使其具有个人特点。因而,使用表现性目标,人们期望的不是学生反应的一致性,而是反应的多样性、个体性。艾斯纳曾给出了这样的表现性目标作为例证:解释《失乐园》的意义;考察与欣赏《老人与海》的重要意义;通过使用铁丝与木头发展三维形式;参观动物园并讨论那儿有趣的事情。
艾斯纳强调,这些目标并不期望指明学生在参加这些教育活动后能做什么,“而是识别学生将遭遇的形式”。这样,对表现性目标的评价就不能像行为目标那样,追求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对应关系,而应该是一种美学评论式的评价模式,即对学生活动及其结果的评价是一种鉴赏式的批评,依其创造性和个性特色检查其质量与重要性。在艾斯纳看来,两种目标模式对课程来讲都是需要的,且也都存在于课程实践中,但它们需要不同的课程活动和评价过程。教学目标适合于表述文化中已有的规范和技能,从而使进一步的探究成为可能;表现性目标则适合于表述那些复杂的智力性活动,已有的技能和理解是这种活动得以进行的工具,并且,这类活动有时需要发明新的智力工具,从而导向创造性的活动,这使文化得以扩展和重构而保持勃勃生机。因此,艾斯纳提出,应该研究这两类目标在课程理论和课程编制中的恰当位置,分别指明它们在课程中的适用范围,找出它们以何种方式相关联才能最有利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学生、不同的学习活动以及适合于不同的学科。
艾斯纳的课程目标观与斯腾豪斯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他们都反对把课程目标技术化的取向,明确提出教育及课程本质上的价值问题。这反映了人们对课程研究的科学化追求中把人作为物、作为工具加以控制的反思与批判,与整个时代精神对科技理性的批判是一致的。与此相关,其次,他们都以人的自主发展作为课程目标取向的根本,注重人的自主性、创造性、个体性,注重课程情境的具体。在学生个人和社会既有文化的关系上,他们都强调个人接受既有文化时的个性化,强调个人对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再次,在前两点的基础上,他们都不主张完全取消行为目标,或者说他们都注意吸收行为目标所表达的内容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只是认为行为目标只能概括人的较低层面的素质,因而强调用高层次的表现性目标或过程整合行为目标,使之为总体上的人的发展服务。第四,鉴于高层次目标和人的发展的本质的不应控制性和不可预测性,他们所主张的目标表述都采取了一种开放式的形态,不强求统一的规格和标准,而重视课程活动及其结果的个体性、差异性,一切视教师、学生和教学情境的具体情况而定,因而,在关于课程评价的问题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主张一种批评、鉴别式的评价方式。
他们之间也有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课程问题把握的切入点不同,因而对“目标”一词的理解有所差异。艾斯纳是从评价入手来看待课程问题的,所以仍然沿用了目标一词,以利于评价的相对可操作性。而斯腾豪斯则是从课程实践入手来建构一种新的课程模式,因而他强调过程,主张把目标一词作为“不受欢迎的累赘假设”而抛弃,代之以“过程原则”。但是,这种区别显然不能掩盖他们在课程目标取向上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正反映着课程理论的主体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