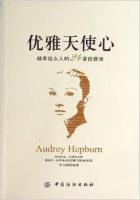但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似乎太容易了,更多的困难留给了革命之后。由于清王朝不是由长期的剧烈革命斗争推翻的,也就没有为革命派在战争中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创造条件。当时,虽然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南方的一些省份,独霸一方的实力派们曾纷纷站到革命一边,但对于手中没有什么实力的南京临时政府来说,要控制和指挥这些军事力量是相当困难的。这种情形也反映在领袖的影响力上。孙中山个人的威望和影响是形成临时政府权威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革命的例子都表明,领袖个人的魅力和感召力是形成革命后新的政权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轻而易举”的辛亥革命无法为形成这样的领袖提供舞台。孙中山虽具有相当的威望,但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主要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参与多少实际的策划、组织和指挥工作,这与历史上那些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革命英雄式的领袖”是不同的;而且,孙中山的大部分革命活动是在海外进行的,因此,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威望要远高于国内。种种迹象表明,利用领袖个人感召力来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权威基础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上述条件下,南京临时政府只维持几个月,就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袁世凯,这就毫不奇怪了。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斗争梦寐以求的就是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武昌起义和全国响应为这个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机会。经过独立各省代表的讨论酝酿及孙中山的回国,1912年1月1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终于诞生了。对此,孙中山高兴地说: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但是,这个南京临时政府却实际上并未能如孙中山所愿的那样成为一个强固统一的政府,它从一开始就软弱无力,对独立的17省政权从未实现过真正的号令权力。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过程中,独立各省就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和畛域观念。在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活动中,就出现过武昌和上海两地相争的现象。1911年11月7日,湖北都督黎元洪以“义军四应,大局略定,唯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为由,向各地军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电。越二日,便通电各省代表赶赴武昌,筹组临时政府。对于黎元洪的这种做法,江浙革命党人与立宪派首领立即起而抵抗。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提议在上海开会,筹建革命政权。理由堂而皇之,即上海既是位居交通枢纽,又是列强各国注视之地。陈其美随即于11月13日通电各省代表来沪。11月15日,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七处代表在沪集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这样,便形成了武昌与上海两个争夺建立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心,直到孙中山回国到沪,武昌、上海两地的争吵与矛盾才算告一段落。
同时,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运作过程中,独立各省并不听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际上成为一个对外名义上的代表独立各省的共和国中央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宣誓说:“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于此誓于国民。”他还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但是,要真正实现上述任务谈何容易。在民国初建、内忧外患、困难重重之时,要求临时政府的中坚力量同盟会加强统一领导,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但同盟会却恰恰相反,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反而更加涣散了。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章炳麟就宣布正式脱离同盟会,而与立宪派、旧官僚联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月14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因不能容许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在自己的禁脔之内活动而派蒋介石将其暗杀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湖北革命党人孙武由于未能取得南京临时政府中的部长席位,便愤然脱离了同盟会,转而联合湖北的立宪派另行组织“民社”,拥戴黎元洪为领袖,与同盟会作对。革命尚未成功,南方政府内部就已经四分五裂。
不仅如此,孙中山回国到沪之所以受到东南各省民军的热烈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光复各军是把他当作财神来迎接的。当时盛传他“携华侨捐款数十百万以来饷军者”,江浙联军的将领们轻视黄兴而支持孙中山,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当日,即有将领前来相问:“公携华侨捐款几何?诸军望之如望岁焉!”但是孙中山当时既没有华侨捐款,也没有借到外债,回答只能是那么空洞无力的一句话:“我携归革命精神耳!”这不能不使他的威信大受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的号令就被大大地打了折扣。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手中无兵、无将、无钱,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但是在革命后,江苏省政府也常常是不买孙中山的账。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因财政上的困难无法维持下去。当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在后来回忆中说:“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指孙中山)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到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孙中山为了摆脱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窘境,乃谋求日本的支持,甚至不惜将东三省租给日本为条件,希望取得日本在经济方面的支持,但日本方面根本就不买他的账。孙中山在后来解释这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尤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无可奈何心态溢于言表。
历史进程往往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实际上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受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制约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也与当时交错的各种因素相关。袁世凯作为一个有能力的汉人官僚,也占尽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排满心理、呼唤“强人”出现的希望的便宜。当时,企盼权威,喁喁望治的“马铃薯”社会的典型政治心态,并非民族资产阶级所独有,希望汉族军事强人入主政治中枢,不仅是一般人的“民意”。甚至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也曾有过类似的看法。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在给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咨文中就说过,“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成,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孙、袁会谈,讨论国家大政方策,孙中山回上海发表演说又指出:
“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袁)莫属。”
另外,在当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西方列强的作用和影响。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凡属重大的内政措施,不得到列强的支持与认可是难以行得通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众多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瓜分的基本国情,大大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列强需要的是对其俯首听命,但又能以高压手段维持社会治安的强人。袁世凯正是当时合适的人选。
正因为此,各国在华公使公开扬言:“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显示出他的治理国家的才能比当代中国任何政治家为高。”“任命像孙中山或黎元洪这样的领袖为民国总统,决不能指望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
列强支持袁世凯上台的力量是强大的。
列强的这种态度无疑成为时人对局势观察的重要参照和依据因素之一,这对于国人的盼袁心态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心普遍厌战并害怕列强干涉,从而一致强烈要求列强挑选的代理人袁世凯出面解决时局问题,自然也就成为当时一个无可挑剔的选择。
列强的支持,为袁世凯的成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以后,由谁来担当治理国家的重任一时显得十分的迫切与重要。
治理国家远非进行革命斗争所能相比,需要有一批真正具有治理国家经验的人马。
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革命党人实在难以胜任。
以同盟会为其最广泛组织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前的年代里没有能够始终保持团结一致。它的全国性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融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尤其要命的是,他们害怕持续的分裂和战乱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更害怕自己因为无钱、无声望而不能坚持下去。随着这种恐惧心理的蔓延,当解决全国性基本问题的时机来临时,他们因为没有能力,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
同时,革命党人虽然有着高度的革命热情与建立一个富强国家的美好愿望,但他们长期流亡海外,缺乏实际从政经验、执政能力与为各方所一致接受的资望。
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这就是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
关于这一点,黄兴在1912年6月就说得很清楚。他说:“事情很清楚,没有行政工作阅历的青年人不能忽视那些(旧人)的国务才干,尽管那是旧制度的才干;军队应该留下一批行家,尽管他们先前为清朝卖过命;外交方面,需要在欧洲有影响的人物,尽管他们的活动与清朝有联系;无论制度破坏得怎样合理,我们没有旧制度有经验的官员却是不行的,姑且这样说吧!”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袁世凯及其党羽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巨大政治资源,已经成为当时人们需要和倚重袁氏集团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然的话,为什么在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共和政见,孙中山提出辞呈之后,南省临时参议院马上就“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并且会“满场一致,选公(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呢?“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当日的国民代表对袁世凯的重望,史实俱在,足以说明这一客观历史问题了。
袁世凯心子黑得不够彻底,那么他的脸皮是否厚到了足以成大事的程度呢?
历史事实表明,袁世凯的脸皮还没有厚到不顾别人的嘴巴吐唾沫星,只管做自己大事的程度。
在可以称帝开国的重要时刻,袁世凯却顾及世人的舆论,瞻前顾后、婆婆妈妈地再三声明自己受过恩,不忍从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这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政权,再三观望,等到中华民国成立,共和体制已经诞生于中国,他遂失去了这黄袍加身这一千载难逢的重要机会。
当初,在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如乘天下大乱之际,亲率精锐虎狼之师,破汉口,下汉阳,占武昌,然后,北扫清穴,利用无人可阻、民无所归的大好形势,传檄各省,开朝定尊,建立一个新人新气象的中华大帝国,造成既成事实,帝业之脉谁能说不能在中国延续下去呢?退一步讲,在平定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之时,袁世凯逐孙、黄,定长江,四方拥戴,民心所望,如果在此时以雷霆万钧之势,由共和一转而为帝国,估计反对派也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可惜,袁世凯既想挂羊头,又想卖狗肉,最终因为犹豫不决,丧失了机会,时过境迁,又想在错误的时间里复辟帝制,最终失掉了民心。
巅峰之处不胜
寒袁世凯是在巅峰状态中倒下去的,高处不胜寒,如何才能防止巅峰现象?
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是在最终战胜对手后,嘴里还高唱着大风歌时,却不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很快就走向了败亡之路。
常言道:日满则坠,月满则亏。
袁世凯在当上了终身大总统时,他的人生与事业已经达到了巅峰。
巅峰状态其实是一种危险。没有人能够在巅峰上长久地停留。
长期以来,各种有关清末民初的历史书籍,无不把袁世凯的面目刻画成“窃国大盗”、妄图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的民族罪人,将他说成利欲熏心、狡诈阴险、机关算尽的小人,其实,这种概括并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