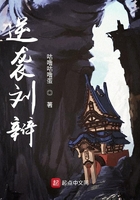7、校长故事
晓非收了小孩们画的长短不齐的麦穗或麦稻穗,放在办公室里,就飞车远去。等来到小镇边的那所中学母校时,天快黑了。晓非与迎面的昔日同事打了招呼,就径到东北角的那两间房前。
其中一间是在教室边镶接的房子,为青砖灰瓦,青砖已渗出了无数粉渍,瓦上长满了蓬勃的艾蒿与绿毯样的青苔,房后茂密的古木把繁富的枝叶尽情地倚卧其上,如同仙女的青丝慷慨散落。另一间是用麻秸编搭的草棚,为校长自家厨房,墙上的泥有很多早被雨淋冲涮殆尽,露出灰白的秸杆好似白骨,屋顶上的麦草也早已又腐又黑,薄薄的粘在那儿,如同带了多日没有光泽的假发。在那间瓦房里,有患右腿灰质炎而跛了的校长。终年要吃一种祖传的秘方治疗残疾。这是因左手的僵硬而导致的连锁症,据医生说这左手的失灵又是因为右脑曾在某一瞬间缺血缺氧造成的后遗症,幸好大脑仅仅在某一瞬间混乱,如果那一时间稍多一秒,躺在床上的校长也许早就已成了植物人。当然更让校长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个乡医院老中医还继续说这右脑的一度失血又是源于左心房的某次贫血所致。就在老中医还准备不急不躁地继续逆向推理时,那个心脏病患者早不耐烦了,直嚷到好了老师俺求你快点开药吧,等你妙手回春时,学生再与你详解病理。后来白胡子的老中医像给其他病人一样开出了祖传秘方:当归、茯苓、苍耳子、牛黄、兔丝子、甘草。并嘱咐每日三煎或会有救。校长在那个滂沱大雨的假期中一直吃这副通用的中药,并且吃上了瘾,一吃几年,至今如故,还在原来的疾病基础上又多了个嗜药症与足不出户症。本来说在那个暑假要改选校长的班子会议也就从此延期,似乎也无人提及或不曾有过一样。校长的鞠躬尽瘁与积劳成疾有目共睹,药费当然全部报销。乡里并且接受其代病工作的要求还特许可不须参会,可指派任何一个教师去参加县乡各级会议听取精神,乡里还派专人每日把各级文件口头传达给校长。校长的公务只须管好那枚红色印章即可,所有的财务发票、自拟帐单、介绍信、药费单、新生通知书、毕业证、五花八门的函件等等,必须有这枚专用章,方为正式的可生效的。校长有了这场柳暗花明的续任后,就整日像烹饪师似的精雕细刻起那副永不变质的中药了。他会把张瞎子(一个会算命会唱书的活神仙)看过摸过的虎骨用小钉锤轻轻敲打,像钻石工人似的每次只敲下一片猛虎的影子,放在药里作为药引之一。他也会把校园的几丛细竹上的粉紫竹黄采下来掰开投到药罐里作为药引之二。他会把张瞎子说过的人形何首乌捏得软软的如印泥压在那团干草里作为药引之三。在作了这些事之后,他有时跟自己开玩笑,把其中的竹黄替换为牛角尖,或者又把何首乌扔到塘里用一种他命名的气骨代替。总之,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想象来炮制这份中药,这份改变了那个夏季沉浮的中药。想着这味药的苦涩,一位老教师一次给他几粒小糖说是邻居家娶媳妇时分发的,让校长甜甜嘴,整天捣药罐子的嘴大概是麻木了,吃点糖看甜味可否重来。但校长拿了糖,吃了没有没人知道。还有一回夜里,一个疯子扛着大扫帚摸到了校园,看见校长在烛光里炼丹,旁边摆着个酒瓶,说校长一边嚼甘草一边喝小酒。疯子说的也没人信。晓非在那工作时对这些传说也只是一笑了之。但校长住室里那股特有的污浊沉闷气息是货真价实的。校园外马路上都能闻到。但象所有的同事一样,从不会因此而不进校长室的。如果不进后果谁都明白。谁都知道校长整日熬药,熬得像八宝粥一样,但校长吃药有个怪癖,就是门窗紧闭。有人说校长怕人们看见他狼吞一肚苦水而怜悯他,说他最怕那同情的目光,他从小就是打斗长大的,又向来未惧唬过任何人包括可恶的乡长。
校长本就是个诙谐成性的人精,虽然那些幽默不比老百姓的粗俗笑话文雅多少,但因其毕竟爱读书爱看报,有些幽默倒也有曲折的长度,不致太短太板。比如这副中药就是他的大幽默之一。他会说这下好了,有了这副万灵丹,我就会参看麻蚁上树时,可以不时弯腰给煤炉吹两口气,在对牛弹琴时可以掀下土罐盖子看药好了没有,在小酒喝得晕糊糊时用药气引一引,免得酩酊大醉。他说到做到,每天早晨起来先烧一堆报纸把煤块架上,待第一块煤燃着放回炉中后,再把第二块架在纸火上,待第二块也熊熊燃烧放入炉中后,再堆上第三块,待第三块也绿焰如画时,他就把土把罐子从床肚里捞捧而出,架在炉子上。然后看每日专递的报纸、文件、信件、假条、帐单、肉票等并一一加章,每加一章都歪着头深深地呵一口气以便每一个印章都鲜红如发廊女子的唇或酒鬼的眼睛,如此精致正是他对加章这一手艺的追求。有时诗意上来时,他情不自禁地把报纸也盖上一排排的印戳,无数的印戳又绘成一个扩大的圆章,然后他一边抹着额头的淋漓大汗,一边还歪着头欣赏这诗意动作。有一次,他先用图章朝手心盖,试试一夜的印泥可否冻着了,因为梦里他冻得缩成雪团,以至于醒来就摸印章。谁知印章依旧红艳艳的,他看着手心中的红章,不自觉地在另一个手心上加盖了一个,这下并未停下来,他接着先左腕后右腕,先左臂后右臂,又脑门、眼皮、鼻尖、嘴唇、牙齿、颈项、肩膀、胸脯、后背、屁股、大胯、左腿、右腿、脚趾,趾头缝里的污垢,还有空中那个怪兮兮的活动的影子,都给盖上了鲜红的大鲺,然后既疲惫又心花怒放地睡下了。醒来后,那罐药早已糊成灰了。第二日又让专职送信工去白胡子中医家拿回第二副中药,继续煎熬。在熬药时,继续永不厌倦的加章工作。直到醉眼朦胧的酒鬼校工来喊他吃早餐时,方才一跛一跛地去烟熏火燎的厨房用餐。早餐过后,是中餐,中餐过后,是晚餐。当然像老百姓一样,想与众不同都没门。要么一天不吃饭,要么一天不停地吃。校长尝试过如此做法,但效果不好,一天不吃饭,那中药气味熏得他腿差点直起来跑操场投篮去了。这冲动把校长惊吓得只好一天24小时吃,可吃过以后,他不能不像陀螺一样在厕所与厨房间旋转,比世纪初的幻灯片胶卷倒转还快。校长腿扭得又差点真得要断了。二度失败,只好继续与校工同步进餐并佐以美酒,那是校门口铁皮棚店里卖的小老头酒。当然校长不去开会,不代表上级不莅临指导工作。除了他校长是个特例外,其他一切照旧,校长说这叫照斗不误,那话听起来总酒气熏熏酒气熏熏的。如同他那药气总像暮色一样笼罩着东北角的那间灰屋子。
校长虽然腿不灵了,但脑子一点也不受影响,甚至还更加发达了,把腿上功夫也汇聚了。他一上任就三下五除二把几件棘手事都抹平了,还以残疾之躯矫正了学校风纪。
第一件事是平衡校园门口两家饭店相争。每回乡教管站领导下来,总是报怨说真的他×的没鸟法,屁大的事也要我们亲自督导。不督导吧,一旦上面来人查访或下面有人上告,吃不了兜着走。而陪着说话的老会计就笑说要是把教委的大楼削去一层,也许会少些公务。而校长依旧老话重提,比张瞎子的古书说得也流利,您们领导不与民同乐怎么行,再说您们的莅临将使敝校蓬壁生辉。我代表全校师生热烈欢迎各们领导莅临。每回乡教管站领导来的第一句话总是说今儿个不在这吃饭,现场办公到晌午也不吃。但校长总会说绝对执行命令,不在此地吃。
他这话是对的,但也不对。因为在学校不远处的路口两家饭店早已锅碗瓢盆鱼龙飞舞了。一家是校长的远亲开的。另一家是一位老师的爱人掌帐的。每一家饭店都有一个小女孩整日坐在门前择菜,择那没完没了的死菜叶,或把死鸡毛拔成活鸡毛都一样。下雨天也要在雨雾中择,头顶的花伞仿佛一朵佛祖的莲花又好看又能提供遮风避雨的梦。因为她们从不看手上的菜叶里有多少蛆虫,从不数那眼镜会计从哪个村庄里临时捉来了多少只乳鸡。她们只专注地盯着校园的大门,要像数码相机样录下每一个进出的人影,在那些人影中寻找每晚电视上出现的县乡级大人物的脸,谁最先看见那熟悉的永远金光闪闪的朝天鼻孔,谁就会为老板推销又一桌古典大餐,就会为自己挣得次合影留念的小费。为了平衡,校长规定,两家饭店公平竞争,谁先打电话报告有贵宾驾幸敝校,谁就会有挣得开支消费单的机会。那家饭店的女服务员们就有与这些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大人物们合影的难得机会,那是比歌星照要有威力的照片啊。事实也确实公平,在校长的无数同意单据上,两家饭店的数目总是相差无几,最多也只是一家饭店的女孩多照了几次相。人们就说那个女孩的笑容太好看了,没有一个顾客不为之倾倒,包括来校推销梦幻记忆法的温州商人也不得不免费给了那个女孩一套透明词典,学术论文报的主编来采稿时也不能不把预领的版面费不惜花了一张,给女孩买件雨衣披在风中,说是风衣穿在这女孩身上衬托漫天的秋雨是绝对的大地心灵的无声歌唱。只要不是钞票的悬殊,两家的老板当然不会对女孩的受宠斤斤计较的。他们早已达成了共识。几年前的原来两家老板挥刀相向而震动县城造成恶劣影响,使两家承包人纷纷退出,不知从何处又冒出这两家,虽然这两家都与原来两家有千丝万缕的瓜葛。但牌子一定要换,长征要换成长安,红楼取代红都,在同一时间燃放了再开业鞭炮。这两家饭店成了校园门前的装饰性标志。
第二件事就是坚定不移地辟谣。在饭店的上面一层,原来是几个年轻老师夫妇的一人一间住房,炉子在阳台上;另有几个单身汉也共住一间。晓非那时因参加工作晚的原因是没房子的。校长大会上高声喧讲这几间房子租赁给一年轻私企的庞大利润后,就让那几台缝纫机在那儿默默踩响了,那响声只有整日一副醉眼感伤的老板与同样富有想象力的校长能听到,只有那几个从生产队招来的少妇与少女能听到,她们做梦也没想到在那一年做了一回工人。虽然一天十几个小时不抬头,只准看机针,只准做同一尺寸的校服样品,但她们无怨无悔,甚至沾沾自喜。那将有的三三五五,那将会在烧砖的丈夫面前的扬眉吐气,还有那在学校老老实实羞羞怯怯混毕业的的女孩也有了自己挣的钱,爹妈已说好的一分钱不要都归自己买套把衣服与化妆品的钱,或许还可以找个好婆家的未来,至少会有出门打工的路费了等等灿烂梦想就是她们欢喜的动力。又一次大会,校长辟谣,现在小镇上正流行‘正校长抓不住基建,抓小钱,围着老板屁股转;副校长没实权也不管,只管乡下养鸡蛋;教导主任半夜起五更睡,小饭铺里特劳累;一级教师开饭店,厉害老师开商店,普通老师麻将日夜干,还剩下小孩捧着书本当画看’,这些话全是什么东西啊,全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基建由乡长负责我当然不能狗拿耗子,说我挣小钱是歪曲,我是想利用那两间破房为单位创收,完成任务;副校长家里爱人种地,一儿当兵,一儿种地,一女儿上高中,如此负担,一月三百多块钱怎能维持。爱人养鸡,他趁空搭一把,在没课时去卖一会儿鸡蛋是情有可原的,而且他每次都是四十分钟一个来回往返学校,签到簿上签四次名的,这比有些年轻人坐在办公室里,竟然半日不去校长室签到要认真的多。再说,我们同行为什么不同情一下呢,人家那大学博导可是在家上班上课呢,甚至课也不上的,一月拿我们好几年的工资,为什么我们非要对领导鸡蛋挑骨子呢?教导主任积极改善学生生活,使学校冗员裁减,又使几位老师家属在服务学生同时有所报酬也是大功一件,我多次说过,只要各位教有余力都可开饭店的,经济时代放开搞活吗?乡长去年不是让我们不出门创收了半月工资吗?乡长那辆标致车可是有我们所有人的汗水的。还有今年春季的捐款、市茶叶节、奥运会、县敬老院(插一句,听说十年后每乡建一个,那时我首先进去)、乡教管站大楼,这几项不是又让我们创收了半月工资。据传县教委又要盖楼,我们可又要准备好无偿献血了。因此,我趁今年全省全乡大批上马企业之机,搞个校办工厂学习人家大城市,也为老师们谋福利,我们也是人,只不过不是圣人,要吃饭要养老婆孩子,除了比老农民少干点农活之外,跟他们一样穷。我们在座各位男教师大多数的另一半可都是纯农民一个,我们有些老教师至今可还是每天风雨无阻地在123国道上奔驰比学生骑得还快,但那辆车可是老式加重二十年了,儿女结婚了穷富不管,没考上学没交差的还得啃这老骨头,老伴吃了一辈子苦,还在生病,我们为什么不给创点收入呢?因此,有人说,我围着老板屁股闻骚,攻击我个人就算是,但摸摸心口,如果我说是为了我们大家还算合理的话,那有些人的谣传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反正我已签订了贷款协议,五万元在我们学校是天文数字,但一旦校服大量生产的话,五万元就会变成庞大的利润源泉,我们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还有,我们每学期除了开头的学杂费外,还有四次收费,几乎一月一收,民怨沸腾,上面要查,下面要告,让我们怎么办?还是创收,唯有发财才是硬道理。我们清水衙门,圣洁的天堂,如果能金光闪闪,即使有铜臭之骂名,我们也要顶住压力,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我们的一级教师爱人利用精湛的厨艺为我们学校招待数不清的领导宾客,更从过路的客人袋中挣回养家的费用,这是值得我们去颂扬的。至于说厉害教师的话,更属诬蔑,甚至是耻辱。在遭到一些特痞的学生攻击时的正当防卫竟然被告到县委县教委,惹得全乡全县沸沸扬扬,只得我们公私共同花钱消灾,这不是我们教师的羞愧吗?那横行镇上已有老婆又另娶一房,公然对抗婚姻法,可逍遥法外,孰个厉害谁个非,自然不言而喻。这些谣传中唯有最后一条货真价实,我多次讲过,我们不是不要娱乐,而是要找准时间和地点以及合适人选,才可以玩两把,解解馋也就算了。可有些教师就是不能克制自己,我倒有点怀疑在课堂上是如何向学生传授纪律的。那讲话时一本正经不脸红。在办公桌上竟然把一桌牌摸得都油黑黑的了,不是天天摸,能脏得那么个样,也不怕细菌感染皮肤病,不怕我们可爱的学生搂作业时看见偷笑,不怕我们的乡长视查时瞅着,在乡教育大会上点名也怪丑的。人有脸树有皮,何况被称为人之楷模的各位先生。是的,有些同志又要发历史癖哲学瘾了,钻牛角尖了,说什么县城往东三十里的三省交界处可是天天旌歌,夜夜舞平,并能说出某某大人物周周必到云云。这纯属为自己虚构理由,第一,人不能比,人比人气坏人。如果我残疾也去比县残协主任,能比上吗?第二,中国人爱制造小道消息,拿当官的开心。有些人一次没见过局长什么样,可就能堂而皇之地说在某某地方与局长吃过饭,言之灼灼,全不像假的。此外,说什么本来就是人格分裂二重生活,嘴上一套心里一套。这其实似是而非,因为这是思想认识论不是实践论,实践是尽量使我们心口合一,理论联系实际。说到这,我又想起某些人说的,什么自古至今,理论从未与实际相合,以此为自己开脱。是这样,我承认,正因如此,我们文人才有意义,我们要躬耕实践显现人对自己的塑造与想象,这才是人本质。本质在过程在论证,不在于前提的认识。好,不哆嗦,有些小孩早在拼了,乖乖,全搞不懂大人事,只知道小猪样吃,不知爹妈在受啥罪。好了,这次辟谣就到此为止,以后,我们不许传这些闲言,至少不准在校园里传了。前年发生的在乡政府院墙贴纸条写黑板的事件,诸位都知道,都是扯不清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而我们学校虽不是圣地,至少我可感觉,没这回事。有,也只是相互的没说清的误会,误会。今日掏心后,就不许再有此误会了。另外,我还想补充一下,我一向主张老师们不管借也好贷也好,把那间窝往上搭一层,一家三口住上面,下面一间与小厨房不都可以租给我们边远村子的小孩了吗。每月多挣个百儿八十,可也抵个把月工资了,邻乡都这样让老师们致富的,我也双手赞成。我们穿不起西服,吃不到什么汉堡,没影院去看,还有什么清高的啊,生存才是第一要素。让我们为了生存,不欠债,不择手段吧,不要清高,不要清贫,我们要财富与苦闷,这可都是富人的病啊。我们大部分教师可是连一分钱的药费都没报销过的,即使报销过的,还要匀一半给那些手握公章的人的,这我们人人都清楚。我是特例,吃多少销多少,但其实我只开一副药,也不值两钱。
有关校长的情况先预报几句。也就是在晓非去省城继续寻找档案之后的几个月,学校又开大会,校长被调到了另一个学校。而新来的是同样病患者,在那校被查欠款达几万。而校长自己几年内竟在县城富人区有了一套小楼,老婆孩子住在城里,他早晚回家象乡领导一样,俨然城里派下来的。到了这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吃药校长补窟窿,用老师们的话是擦屁股。服装厂的小老板破产跑了。服装厂的几台苏联机子也被拍卖了,被那个满脸皮笑肉不笑的会计带来一帮妇女疯狂投拍了。更象是抢,因为封条门的钥匙在会计拿着。他头天夜里就已回村卖弄这次辉煌的掌权资本了,几位妇女就很机智地说,会计教师你要多多照顾,过几天俺们去把你那块油菜给砍了,那也快黄了,我们早就想跟你说了,正好今晚你有空就这样定了。你爱人整天在小学代课也忙不过来。像你会计这样接了班后能一直担任不出事的聪明人是少有的,邻村的某某不是干一年就耍下来了。还有,你又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不像俺们没文化上不了台面,就是给了机会也干瞪眼,别说还没机会呢。去年去上海拾垃圾,捡了半口袋,但摸了两夜黑,吓得我自认是没命去大城市了,在那里拾破烂也要有文化。我们这一代人是废了,垃圾一堆烂在乡下了。
当日乡信用社把所有的贷款单都转到校方。新校长拒不签字,他说刚来就又成了债主,这不可能。他只在拍卖缝纫机的文件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