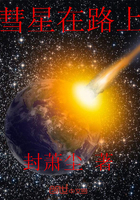要说寄奴也真是倒霉,皇帝说是让他“不爱写字就学剑”,真实的说法是“不想写字的时候你就学剑,学累了你再接着写字”,非但没把原来唠唠叨叨的老师赶跑,过两天行了拜师礼,还得多一个全雍阳最可怕的老师徐玄策。这心理压力得有一千斤重,压得他连去未央宫拜见母妃都跑不起来,顺着墙根慢慢地走。
和苏召两个人经过未央宫墙外的夹道,看见一个内监领着几个服色统一的小孩往皇宫北门走,想必是往监栏院送。见着寄奴和苏召两个,内监慌忙引他们路边跪下。这群小孩小的八九岁,大的也就十三四,都灰白脸儿,想是才刚“办完手续”。宫里实权实职的太监都有自己住处,但没有一个不是从最底下的监栏院里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只不过不是谁都爬得上来罢了。
小太监里有一个很有些眼熟,寄奴还盯着看了两眼,也没想起来。这些小人物也长了一张小人物的脸,平常谁能记得住他们?一闪念就走过去了。
走到未央宫,隔着前殿就听到深处箫鼓不绝,琴瑟叮咚,箫鼓为主调,节奏一下下敲在人心上说不出的震颤,琴瑟萦绕不绝声音却极细,只给这箫鼓伴个过场。其中有人曼声高歌,男女不辨,却很有几分高阁临江渚般的豪情。
玉台之上,有人在跳舞。
她舞的是剑。两泓青光如龙似电。舞者腰身如折,美目顾盼,身姿曼妙如斯,剑意却沁骨霜寒,交织漫天,让人忍不住看却不敢眨眼,仿佛一个大意松懈了神智,就要给那两柄青霜斩下项上头颅。
没有一个观众。那舞不为给任何人看,似白鹤傲然飞舞于云层之上,纵然无人欣赏,也已绝世。
满场的宫女仆从都低着头做恭顺状,不敢窥视。就是玉台下边鼓瑟吹笙的乐师和歌者也是眼观鼻鼻观心,目视前方一无所取。要是李青莲这个风流翰林在此,肯定要骂这些人一句煞风景,不懂得欣赏。
剑意逐渐收拢,舞姿也缓上一缓,一首清歌正到了尽头。苏召和寄奴只赶上最后两句,唱的是:千载胭脂泪色绯,刺得龙血画眉红。
这诗出自上京一位惊才绝艳的少年,名叫江南。此人笔下锋芒直如名剑,风采卓然,朗如日月,更是胸中沟壑纵横之人,写有一本《缥缈录》,读得无数人心弛神荡,恨不得热血相酬。却有爱好者说,若以“缥缈”为真英雄,其中诗歌,才是真绝色。
单这“刺得龙血画眉红”,便能让李青莲的“三重美人论”羞愧致死。
歌声渐绝,一柄剑却“唰”地脱手,青虹贯日一般掠去,直取旁边肃立的一位老太监人头。众人中忍不住发出几声尖叫。本已收拢的剑意一瞬间如闪电炸开,倏然间却又断绝。剑尖距离老太监颈间皮肉只有一寸之距,却给雪一般的纱卷住,舞了一个完美的四分之一圆,回到舞者手中。
云妃白染傲立于玉台之上,犹如仙鹤收起洁白的羽翼。她将手中的剑“呛”地抛在地上,冷冷地说道:“告诉你的主人,不必派你来刺探,更不必妄想控制我在这皇宫中的所为。”
老太监垂首弓腰,不动声色:“老奴不知道娘娘的意思。”
白染冷笑:“你不必装,既然效忠了云家一辈子,就该回云州去养老,留在宫里,早晚死在宫里。”
老太监目光惊动,仍不敢抬头,却低低说道:“毕竟是娘娘的亲眷……”
“亲眷?”白染绝美的脸上笑意充满讽刺:“我入宫之前,怎么没有人当我是云家的外孙女?计划失败,我困在深宫,忽然就有了这许多亲眷?”脸色冷到极点:“滚!再敢来未央宫,我那一剑就不会再收回来。”
老太监也不禁冷汗涔涔,快步倒退着出去。
白染看见两个孩子进来脸色便柔和许多,走下玉台。苏召跟着寄奴行了礼,她也将寄奴亲手扶起来,明显是高兴的,却也并没有多少亲昵慈爱的神色。苏召不禁猜测这位皇妃是天生性子冷淡还是单单对这个不养在身边的儿子缺乏感情。但看长乐公主赵凝舞那番娇憨的样子并不像受过母亲冷落的小孩。
寄奴的兴致也不太高,是因为刚才进来受那一番刀光剑影的惊吓。校场成千上万的练兵他也见过,但那和自己的母亲手里拿着刀剑又不同。白染并不安慰他,只示意侍女拿茶水点心给两个孩子,再像平常一样问他些话。
皇宫的另一边,皇帝摈退左右,在太液池边的有风来亭召见徐玄策。两人都穿着便装,言谈也有些东拉西扯的意思。不过聊了两句一个侍卫服色的人匆匆行来,似是有话要对皇帝说,看着徐玄策却有些犹豫。赵喜滚龙袖口一摆,不耐烦道:“快说,说完便退下。”侍卫单膝跪地,道:“禀陛下,那人刚才去了未央宫。”赵喜目光一闪,道:“说了什么?”侍卫答道:“什么也没说,倒是差点给皇妃一剑刺死。”赵喜挥手示意他退下,过了片刻,面对着空空的太液池吐出一个字:“杀!”
没有人应答,也无人来去,但那老太监必定活不到明天早上。
皇帝眼望着太液池的水波,叹息道:“这事若传扬出去,朝堂上又好一番口舌。”徐玄策站在旁边眼望着亭柱,打定主意不参与这个充满是非的话题。皇帝却偏偏不放过他,看着他说:“徐卿可也觉得,我对未央宫太过宽容?”徐玄策垂首看着地板,摆明了屁都不想放一个。整个雍阳皇朝能干出这种事来的也就他了。有些话你要接了口,保证接下来怎么说都是错。
皇帝看着他,说道:“我召你两次,你都说在家生病。一个将军好好的做什么跟那些酸腐文臣学?”徐玄策淡淡地应道:“横竖臣近来也没什么要紧事。”赵喜苦笑道:“果然是为了诸葛雷云代你去往离国北境的事。”徐玄策单膝跪地,道:“离国虽无甚紧要,但紧接我国北境,雍北的蛮兵上次突破北长城,便是攀着离国的山峰过来的。此次布防作战对我大雍事关重大,臣一向和诸葛将军并肩作战,怎能在此时放任不管?”皇帝摆了摆手低声说:“离国的事还不算什么大事,朕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
徐玄策沉默不语,半是不服气,又不便顶撞皇帝;还有一半,则是觉得赵喜这话还有下文。
成帝赵喜忽然话锋一转,悠悠说道:“先帝起用你,到如今也有十多年了吧。”徐玄策道:“十五年了。”
“我封你为‘天策上将军’,觉着也是很久前的事了。”赵喜伸手将徐玄策从地上扶起,缓缓说道:“其实我知道,你这个天策上将军我父亲早就想封,他是特意留给我做个天大的人情。父皇既然信你,难道我不相信?让诸葛雷云替你带兵,是有更重要的事要你做。”
不知道这“重要的事”,包不包括跟着皇子和离国的质子当保姆?
徐玄策心中才暗暗琢磨,赵喜却看穿他的想法似的,将手按在他肩上说道:“征战沙场,扩土开疆是尽忠皇室,辅佐皇帝。但难道辅助便只有这一种?皇帝只有这一位?当年的雍始皇帝如今又在哪儿呢?”
徐玄策蓦地体会到他话中的意思,不由得一惊,待要说话皇帝却伸出一指做个噤声的姿势,低声道:“这有风来亭的风可也是长耳朵的。”
徐玄策怔了片刻,踟蹰道:“皇帝要舍云妃?”
赵喜苦笑道:“我为何要舍她?”
“朝堂里议论纷纷,一怕云妃流着云维扬的血,对陛下再行不轨。最怕的,却还是云家借她的手图谋大雍的江山。如今……怕是还要多怕一层。她究竟是六皇子的生母。”
“天下名将出云州,云维扬的后人,暗中也蓄积了很强的力量。若想让这股力量今后能为我大雍所用,这未尝不是最好的办法。”成帝说道:“至于立子杀母……若我赵家的子孙需要靠杀戮女人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才能坐稳阳极殿上的龙椅,这样便不配做我赵家的男儿,更不配做这天下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