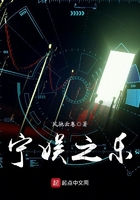金坑上的红瑶女子很会打扮自己,很懂得利用颜色配伍的协调穿穿戴戴。银子的饰片,亮闪闪地缝在头帕、衣服和腰带上,何等美丽。因而,她们身着流行了几百年的传统民族裙装,美丽一如既往。尤其是美发长盘术,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我喜欢美发,每个星期要到美发屋里去修修剪剪头发好几次,常见美发师为盘好一个女子的头发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再看金坑红瑶女盘发,她们的头发长如瀑布,不知要比都市里的女孩头发长几倍。可她们盘起来,真的就是眨眼间的事情,好像变魔术。
不过,在金坑最能展示红瑶风情的不是那些花季少女,而是皮肤松弛、眼睛昏暗的迟暮老人。她们的头上依然美发长盘,头帕紧裹。松松的耳垂上挂着漂亮耳环,腕上戴着镯子,身上色彩鲜艳的裙装纹丝不乱。此外,腰间的腰带缀满银饰,梳头的梳子还镶着银子。所有饰物,据说大都从祖上流传下来。
中年以上的红瑶女子也爱穿她们传统的民族裙装。而且春、夏、秋、冬、种田锄地、砍柴、采茶都穿。不同的是,以蓝色为基调的上衣裙装是劳动装,以红为底色的上衣裙装是节日盛装,黑色裙装是孝服。家里亲人故去,她们要穿三年孝服寄托自己的哀思。她们穿的裙装,大都自己织、自己做、自己绣。乖巧的女孩十来岁就会自己织布、自己刺绣了。通常,她们晚上要织、绣到半夜三更时才去睡觉,很是辛苦。绣时在肩膀、胸前和腰带部位绣得特别精致华美,细看是鸟、老虎、麒麟等吉祥物。束腰的带子绕着一圈一圈的五彩图案和漂亮银饰,非常迷人。我看了又看,并在征得她们同意下摸了又摸,依依不舍。当然,由于外来文化的碰撞,金坑半数以上的女孩现在都穿起了时尚衣服,但仍有半数以上女孩喜欢她们传统的民族装束,这是令人可喜的。我问那些正在刺绣的女孩:“绣这些吉祥物需要事先绘图吗?”她们说:“有些要,有些不要。一般来讲心中怎么想就怎么绣,很简单的。”“那你们织成一件衣服要多长时间呢,几个月吧?”女孩大大方方地抬起头来告诉我:“几个月。”我喊起来,“那衣服不是脏了!”“不会。”女孩平静地笑了,“你看,我们绣成一个图案就用布覆盖住一个图案,等所有的图案都绣好了,再把覆盖在图上的布揭去,一件衣服不是新的了吗?”好聪明的红瑶人。
梯田上几个挖田唱歌的红瑶女子吸引了我们。小雨中,她们一律没用雨具,赤脚挖田。看见我们停下来不走,就不好意思地停止说笑。我们恳请她们唱唱歌来听,她们说:“不会唱歌怎么唱”,话毕继续站成一排挖地。她们挖地很有功夫,翻起来的泥土平整干净,没有一根杂草。王教授一心想听她们唱歌,因而开口先唱。她们听得乐了,就一首一首唱起来。领唱的是着便装的年轻女子,她边挖地边唱。其他人笑着,没有停止挖地。
唱歌先,功夫忙忙丢在边;哥要唱歌就唱起,陪哥唱唱蜜样甜。
唱歌要唱二度梅,一个唱来一个陪;有唱有陪才有味,有唱无陪也妄为。
问哥哪里得茶秧?问哥哪里得茶本?问哥哪里得地种?十里吃来九里香。
她们唱歌的速度很快,挖地的速度更快。挖地的速度仿佛是随着唱歌的旋律起落的。王教授高兴地把镜头对准她们,她们都说“不体面的,照起来不好看”。路过的一个红瑶女幽默说:“也有鼻子也有眼,哪个讲你不体面?”
笑声中拍完照片我们要走了,她们一起停止挖地,站直身来唱歌挽留:
哥哥走路手莫摇,摇手碰着路边茅;茅草叶叶都割手,割着哥手妹难熬。
劝哥回到妹身边,哥在妹的心尖尖;哥在外头是好耍,风流好耍才一天。
歌声中我们返回,听她们唱“六更”而不是“五更”歌:
一更得梦一思想,二更得梦二思量,三更得梦路头远,四更得梦断肝肠,五更得梦金鸡叫,六更得梦天亮了。穿衣不快拿衣走,穿鞋不快踩鞋梁。
我们问:“什么是踩鞋梁?”她们说:“就是来不及了,踩着鞋后跟走啊。”说话间见我撑伞在田头记录,就都唱着笑起来:“山歌本是心中出,哪要笔记本子载。”我不好意思地念而不是唱起了山歌: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自己进灶屋,茶缸无茶喝碗水,鼎锅无饭舀碗粥。
采访中,我们和山歌一起沉醉,和金坑红瑶这个古老的民族一起沉醉。
起伏的龙脊梯田就这样既可以用来种植,也可以用作唱歌的舞台。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是这里的拜年节,未婚男女自由对歌,寻找意中人。这神秘的土地,便愈发充满激情与活力。
早晨,红瑶女子成群结队,为夜宿金坑的客人背行李下山,同时将山下准备进入金坑的客人接进寨子。客人的行李,通常十分乐意放进姑娘嫂子们漂亮的背篓,腾出精力,巡视龙脊。也有三五岁的小孩,走不动了或纯粹出于好玩,欢天喜地坐进背篓,叽叽咕咕探出颗小脑袋来惊奇张望。
这里的女子过去不重读书,如今到了入学年龄,均去上学了。一个名叫潘云秀的小女孩告诉我,她早就想跟哥哥、姐姐上学了,可他爸爸说她还小,又说她七岁的时候肯定可以上学。说到可以上学,童真趣然的小云秀高兴地唱起《老鼠爱大米》。问“是谁教的?”“上学的哥哥姐姐啊”,小云秀高兴地说。
在金坑大寨村完全小学和金坑附设民族初级中学里,红瑶孩子的朗朗书声传得很远很远。我从窗户望向里面的一个教室,墙壁上“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训诫告诉我,红瑶孩子的无限追求正在金坑龙脊梯田腾飞。我由衷地为小云秀生在这么好的时代而高兴。
黄昏时分,我们采访归来。穿行在金坑迂回交错的石板路上,我们再次碰见了早起出门见过的、寨子里最老的那个老人。他已完全忘记我们早上采访他的事,因而举着铜烟斗问:“照相?”我们告诉他早上已为他照过了。
“不可能的,我才从平安乡回来。”他很怀疑地望着我们,反复强调他去平安的事。等我们说起他当太公的事情,老人不好意思地哧哧笑了,露出只剩一颗牙的嘴巴。一旁的红瑶女说,老人每天都是这样来来回回在寨子里走来走去,寨子变美了,谁都想多走走看看。
远处,老人的身影渐渐看不清了,没有留下脚印。一旁的红瑶女子也从长长的石板路上走了,也没留下什么脚印。但是,她红色的裙装背影,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留在金坑龙脊梯田的旋律中。
(刊《当代广西》2013年第7期,收入自选散文集《风中行走》)
面对龙脊更衣
面对龙脊更衣,在我是完全意想不到的。面朝龙脊坦然更衣的那种感觉,如同朝圣。风从窗外吹来,我的头发飘向脑后,我的体态映进远处的龙脊梯田,映进地老天荒那震慑世界的美丽。
这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金坑龙脊梯田的早晨,我的心情美丽而又浪漫得一塌糊涂。层层叠叠的梯田,包围着梦一样的楼舍包围着我。我渴望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哪怕来世在这里落生。
这里的美丽,摄人魂魄。许多摄影家的名作,都在这里诞生。春天水盈田畴,夏日田野清芬,秋来金稻飘香,冬天白雪覆盖。每个季节都是异常的鲜明、异常的炫目。而且愈往龙脊高处去景色愈是美丽、壮观。一会是云的海,一会是雾的天,一会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会露出灿烂容颜。
云来,龙脊梯田一片苍茫,虚无缥缈,难以窥视;云去,龙脊梯田面容毕现,起伏不已,层层叠叠。云来云去颤动交替的瞬间,龙脊梯田的景物幻化莫测,令人神往。落日的余辉,在水盈的田畴闪亮,增添了梯田的宁静,致福致远。远看近看,她们的古老都毋庸置疑。而你一经在此住下,就再也不想离开。
我第一次沿着古老的青石板路走进广西龙胜金坑龙脊梯田,正是这样一个落日余辉的傍晚。空气清澄、透明,梯田起伏,木楼古朴,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自然。走进这里,就好像走进遥远的红瑶历史。我的视线随着金坑龙脊梯田无限延伸,直至梯田背后的故事传说。沿着弯来弯去、上坡下坡的青石板路,我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明朝,那个带着一个部落来此拓荒的人。只是我不能更加准确地判断,哪一层梯田在哪一个世纪谁的手上诞生。
我和海涛、文艺两位一同入住在红瑶人家世代居住的、层层梯田环绕着的、梦一样的原木木楼里,楼里弥散着木头好闻的清香味道。楼下是不规则的、弯弯曲曲的青石板路。上山下山,穿林越寨,驮物的各色马匹、放牧的童叟、赶圩的姑娘、荷锄的农夫,皆由此而过。
我们发现房间里除床和一张桌子外虽然未置它物,但是善于借景。透过窗户望出去,一扇窗有一扇窗的美丽。早就被金坑龙脊梯田俘虏的我,在进入房间的第一时刻便迅速抢战了面对龙脊的床位。推窗或不推窗,窗外的诗情画意都如春风扑面而来。刚在房间坐定,就见一匹古老而又漂亮的高头大马,驮着笨重而又现代的液化气钢瓶,嘴里喷着粗气,打着响鼻从窗下缓缓而过。我坐在床上看它渐行渐近尔后又渐行渐远,忽然有古道西风瘦马的感觉。
缘于对金坑龙脊梯田更深层次了解的渴望,我们稍作梳洗后就走下木楼,在布满雕花的屋檐下寻得一个观景聊天的好座位坐下。桌子与凳子都是原木色泽,带着红瑶人家由来已久的风格。挂在屋檐下的红辣椒,使人感受诗情画意无限。我们就在这无限的诗情画意中与屋主喝茶聊天,等候晚膳。
屋主很健谈,一说起他们的金坑龙脊梯田,就像碰到了知音。她告诉我们,是桂林已故摄影家李亚石先生最先把金坑龙脊梯田推介给外面的世界。
知道我们几个是作家,她又深情地说:“金坑龙脊梯田虽然已经路通、电通、水通了,也比过去去一趟乡里单程都要走七个多小时的时候方便多了,但是仍然需要帮助,需要宣传。”
“你们过去跑一趟乡里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假如碰上产妇难产或者有人突发急病呢?”我插了一句。“看自己的命吧。”“现在呢?”我又问。“现在的接生婆差不多都已失业,产妇都知道去乡医院生孩子。社会在进步,在发展,我们红瑶人的生活也就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了。”屋主高兴地感慨。
金坑的夜晚,就在屋主高兴地感慨与三三两两的旅行者或寻梦者的陆续到来时到来。
此时大风刮过龙脊梯田,天空变暗,雨点随之而下,空气空前潮湿。随后,大雨也毫不迟疑地袭向金坑,梯田的一切顿时被潮潮湿湿的神秘包围。屋檐下围着一张木桌一边喝茶夜话,一边等候晚膳的我们,赶紧朝木楼里搬迁。
木楼里穿堂而过的山野气息,清新得醉人。夜,宁静得仿佛盘古开天。
楼主给我们送来两支闪烁不定的烛光,代替暂时停电的光明,把我平庸的眸子照亮。我看见古老的、用几块砖头垒成的炉灶,燃烧着温暖的炉火,释放出通红的歌谣。矮矮的炉灶上面,则是一个从屋顶垂下的木钩。钩上挂着几块巧克力色的烟熏腊肉,看上去又香又软又好吃。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盘腿坐在炉前,不时添些干柴进灶,遥远的故事让孩子的心灵得到满足。
旖旎着红瑶人家乡野风光的几个菜肴终于做好,与女主人头上的山花相映成趣。我们在烛光中慢慢品尝,唇齿生香。一时间搞不清自己是哪朝哪代人了——若不看彼此着装的话。
由于大雨赋予的夜晚黑得星星和月亮一起消失,所以,从我们的住处遥望其他木楼的灯光,很遥远也很温馨。
入夜,溪声滔滔,彻夜不息,悠扬的歌谣也不知在哪响起。我知道这个古老的山寨,总有一千种理由为自己、也为祖先传唱生生不已的颂歌。
睡在宜人的防潮的木楼里,枕着这深沉、悠扬、绵延了不知多少岁月的歌声和溪声,轻轻松松、蒙蒙眬眬,我长年累月的失眠,在这里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尽管楼上的人不停地走动,把楼板震得咚咚直响;一板之隔的男人说话声也很吵,但我还是一瞬之间卸下了尘世的面具,进入安然无梦的境界,沉沉睡去。
……难以觉察的黎明悄悄地到来。
一只鸟鸣,把我从沉睡中唤醒。这是一只有着非常美妙的、特殊共鸣声的鸟。它动听地叫着,声音划过低低的晨空。我把脸贴在水雾迷蒙的玻璃窗上享受,然后推窗。一个无与伦比的早晨,就这样以没有任何雕琢的姿态,把静如处子的金坑龙脊梯田呈现在我眼前。一望秀美,再望壮美,三望美不胜收!
音乐般的旋律,一层一层往上高去,一层一层很是写意。晨雾静静地围绕着梯田,围绕着寨子。天空传来的鸟鸣更多更急了,这加快了太阳的升起。终于,寨子彻底放亮,阳光照彻金坑。摧枯拉朽!
我突然产生了面对龙脊更衣的念头。因为就在太阳把金坑彻底照亮的一瞬,所有在金坑曾经出现、模糊、消逝、重叠过的影像,刹那间在我的眼前清晰无比。我看见金坑容貌妍媸、能说会道的媒婆,穿过一层层、一片片起伏不已的梯田,穿过一个个鸟语花香的四季,从这个寨子抵达那个寨子,从这座木楼进入那座木楼。她美丽的裙装随风飘动,飘动在弯弯的石径,在高高的云端。
于是,金坑梯田又有了一个面对龙脊更衣的新娘,一个吹吹打打的日子,一次隆重而又完整的仪式。以及,一个接生婆的一阵忙乱,一个新生儿的沐浴更衣。
……轻轻地,我的睡衣滑过肩头,滑过脚踝;默默地,我许下一个神秘无比的心愿。我知道,我的身体跟金坑龙脊梯田上所有的红瑶新娘一样——彼此相似。而那仿佛图腾般悬挂在屋檐下的红辣椒,早把我的面颊映得红红的。
紧接着我的另一个室友,在短时间的等待与祈祷后,面对阳光灿烂的金坑龙脊梯田,缓缓更衣。
远处,犁铧开出的垄沟,整齐而又富有活力。
(刊《广西文学》2006年8月号,收入自选散文集《风中行走》)
萝卜洲的冬天
这个初冬不太冷,连续几度到十几度的气温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特别是12月中旬到圣诞节前这些天,阳光灿烂,使得我不能再在书房坐下去了。我走出书房,走向屋外名叫萝卜洲的田野。萝卜洲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普遍成立人民公社时,当地农民用肩膀一担一担把土从远处挑来填成的。面积不小,几十年间一直是一个村里几百号人的生活、生产基地。这里土地肥沃,视野开阔,除了田地,还有一条大河从旁边经过。
洲子四季生动,一块块菜地互相连接,生长着新鲜的萝卜、白菜、生菜、芥菜、苦麻菜、空心菜等。碧绿的菜叶子,披着日光,显示出萝卜洲的自然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