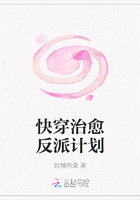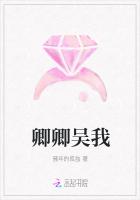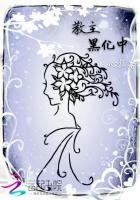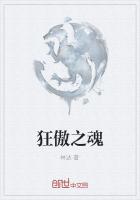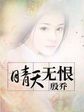当代人的意识反差
民国以来,学画者甚蕃。但诸多面孔都漫漶在滚滚红尘中,唯潘玉良硬生生挤出落魄画家方阵,平地一声吼,爆出女性最强音,真乃一大奇迹。
有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才子、才女生前享受不到自己的才华资源,甚至为才所累,死后却荫及后世。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潘玉良身上。
潘玉良生前潦倒,死后画价却日益飙升。对比如此鲜明,令人嗟叹!
无它,唯“妓”尔——“出身”乃一大噱头。“青楼”,饱蘸女性脂粉泪的字眼,极大地满足了世人的意淫心理。涉及她的文艺作品多带着暧昧的气息,投合世俗口味。而她色彩斑斓的自画像、裸体像历来有“自我炒作”之嫌:不打自招,摆足了佻的pose,含金量能不陡涨么。
身世堕入淤泥,灵魂却几度飞跃。生非绝色,却借助贵人跃离青楼;本是文盲,却操起画笔,欲与男性艺术家试比高。对于她,绘画艺术是一场漫漫苦旅,是一座太过高峻的深山,她却视之为“挣命”的唯一通道,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亦步亦趋,竟也直追同时代画杰。师友们视她为“好人”、“男人气质”、“肯吃苦”。少数同代画家,将卖画数量与才能视作正比,对她的艺术才能摇起头。岂知她将每部作品当作亲生骨肉那般怜恤,生前潦倒,迫不得已卖画,竟有“每卖去一件心爱的作品,就好像卖掉一个亲生的儿子”之喟叹。她和男性艺术家根本不同处在于,创作于她,是孕育,是分娩,有痛苦,更多的是欢欣;她一生都戴着出身的纸枷锁。她借助画笔重生。
每部作品都是她的涅?,她的图腾。那些对她摇过头的画家,只能苦笑地看着她的画价陡涨。因为,她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民国时代的一座雕像。
潘玉良人生关键词:孤儿、青楼女、艺术跋涉者、中国最高学府教授、人气见旺画价见涨的艺术家……潘玉良画展厅,有二三女倒吸一口冷气窃窃私语:“可真丑啊,长成这样咋能在青楼里混呢?潘赞化为啥单挑她为妾?感情扶贫吗?世人对潘好奇,多半是对她身世的猎奇吧……”
不禁莞尔:几位女士的喟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道出了众多观看者的心声。潘玉良的“青楼妓”身份使人对她的相貌期望值过高,及观其照片,反差太大,难免使人在感官上一脚踩空,在意识上连打趔趄。
这种感觉早些年我也有。
心中也曾纠结过类似谜团:潘玉良既为芜湖地方官向身为海关监督的潘赞化隆重推出的女色贿赂,可想而知定属当地粉黛群中凤毛麟角的人物。不说倾国倾城,最低限度,亦当属“清丽佳人”级别。但从她留下的照片来看,她却身材呆板,面容木讷。在诸多如花女生中,却似保姆、老干妈一类。对比强烈,简直就是一“美托”,专门拉来衬托其他人的美。
何至于此啊。
及至研读其身世,心中忽一片雪亮:这一切,都是潘玉良下意识使然。
相貌堪丑,身世堪怜,锦衣“女奴”做好叛逃准备潘玉良本名陈秀清,189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没有来得及伏在父亲宽阔的肩膀上看世界,便永远地失去了父亲。8岁上又失去了母亲。寄居舅家屋檐下,从母姓张。
13岁时被赌棍舅父骗卖至芜湖妓院,当烧火丫头。
张秀清能从一帮灰扑扑、黯淡淡的灶下婢中脱颖而出,全赖她的大嗓门及聪颖天资。关于她的大嗓门,和她打过交道的人都有直观感受,但受过强烈刺激、感受最深的却是林霭。女画家林霭,原籍中山市安堂乡,毕业于中国杭州国立艺专,从法国肖邦大学美术院肄业;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讲师,是《黄宾虹画集》(由瑞典皇家远东博物院出版)作者,任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副主席、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执行董事及副董事长、宝墨楼画苑顾问。林霭60年代在巴黎留学结识潘玉良,因为感佩潘的艺术才华,遂与之成为莫逆,对潘玉良的生活时有资助。潘玉良死后的丧葬费用,她也多有支付。她还替潘做了一块云石墓碑——得友如此,夫复何求!提及潘玉良的大嗓门,林霭用了一个惊悚的比喻:虎啸猿啼。有一次,她刚走到潘玉良寓所门口,忽听一声断喝:
“妹妹,你来了!”吓得她汗毛都竖起来了。抬头,见二楼窗口探出一人:
正是潘玉良。潘玉良本来就“女生男相”,冷不丁一声吼,和当年“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猛张飞有得一拼。
在一群莺声燕语的粉黛中,嗓门粗大、声震屋瓦的张秀清一吼惊人。
有特长便有市场。精明的妓院决定对张秀清优越的生理资源进行开发,因材施教,培养她学唱京戏中黑头、花脸的曲调,同时让她从师学习吹拉弹唱。天资聪颖的她技艺精进,广受客人的赞誉。“江城年少争缠头,血色罗裙翻酒污。”以才艺赚钱的清倌人自比灰头垢脸的烧柴丫头风光多了。但张秀清显然不甘于做这种锦衣苦心的“女奴”。对于她,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形同虚设,她血液里充满叛逆性和战斗性,渴望像自由的鸟儿一飞冲天。试给青楼期的她作漫画,当有着如小兽般的戒备眼神,提溜着小包裹儿,随时准备拔开腿儿叛逃。她的心长满了触角,向四面八方探伸着,机警地收集着身边的人脉资源,做好自救的准备。
1913年,当28岁的海关盐业监督潘赞化翩然而至时,她便知道: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恩赐。
潘赞化这人也好生了得,参与过多起历史事件。祖父潘黎阁曾任清廷京津道台,举家迁居天津。潘赞化1885年出生于天津,幼年父母双亡,由伯母戴氏抚养。纵然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究竟不像在自己父母膝下那般自由——父母俱在的家才是一大片紫云英田,供孩子怡然地在上面躺卧扑滚。或许正是因为同有一个察言观色的惨淡童年,他对被舅舅拐卖的张秀清有着深切的同情。
潘赞化字赞华,号世璧,晚号仰聃——晚年的他在信仰上皈依道教,深得黄老无为而治的精髓。但在少年时代,他却是一个心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抱负的十足少年狂。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16岁的潘赞化同堂兄潘晋华与陈独秀、柏文蔚等人,在安庆北门藏书楼组织“青年励志社”,从事反清宣传活动。“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的行动被清廷列为大逆,四出搜捕,潘氏兄弟被迫流亡日本。
潘赞化入东京振武学堂学军事,并加入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兴中会”。
不久,受孙中山派遣,他潜回安庆,进行民主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捐躯,安庆起事失败,当局加紧追捕革命党人。潘赞化再次出走日本,弃戎从医,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兽医。
和早他五年学医的鲁迅一样怀抱医学救国的初衷。辛亥革命时回国。
1912年,潘赞化青年时期的挚友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委任其为芜湖海关监督。这年,潘赞化28岁,年富力强,魅力四射。命运便是这样离奇,让他远兜远转一步步走近张秀清。
潘赞化身上有着早期同盟会员的赤子之心与霹雳作风,到任后他整顿关卡,严禁偷税漏税。所有税收悉数上缴上海同盟会,支持革命。孙中山曾当面称谢。
潘赞化是披着一身璀璨星光走向张秀清的。
实则,张秀清身边的姐妹个个比她美慧,个个都比她更有机会获得潘赞化的欢心。为什么最后的胜利者反而是貌不惊人的她呢?
潘赞化耿直却并不道学,应酬场合也同意叫局,但他只是单纯地想听人唱唱戏、弹弹琴,并非真的是寻花问柳之辈,所以他总是和青楼女保持距离,以免授人以柄。张秀清中人之资,反而让对女色抱着戒备之心的潘赞化放松。张秀清的短处反而成了长处。身边的人多会察言观色啊,凡有潘赞化,必叫张秀清。那些个以美色悦人的姐妹反倒没机会亲近他了。
可想,怀抱琵琶坐在潘赞化身后的张秀清一时羡煞多少江城姐妹!如果可以选择,她们或许会一致选择张秀清那样普通的面貌、那副大嗓子、那种直性子吧。
一来二去,张秀清和潘赞化便熟了。潘赞化了解了张秀清的身世,有“惺惺相惜”之感。智慧的女子并不鲜见,但善于运用自家智慧的女子可不多。身在青楼的张秀清当然知道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或许是唯一一次机会!我想,凭她的直肠子,大凡有人灌潘赞化酒,她一定二话不说,端过来,像喝凉白开一样咕咚咕咚灌下去,然后哇哇大吐。她的热心肠一定打动了多年辛苦辗转的潘赞化的心——亡命天涯的他其实缺少真正的关爱。潘赞化同情张秀清的身世,肯定她的才艺,欣赏她的个性。好感日增。
男人必须动了“我见犹怜”之心,才会乐做救美英雄。因为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需动用一笔结结实实的银子。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可知,对试图为自己“女儿”赎身的客人,老鸨会怎样狮子大开口。何况潘赞化又是红透江城的海关盐业监督,老鸨不狠敲竹杠,更待何人!虽然张秀清并非一等一的青楼专业人才,且刺猬性格常让老鸨暴跳如雷,但潘赞化还是花了巨资才将她赎出。张秀清的成功,一依赖潘赞化的人品,一是她自家造化。两人初交,便直见性灵。
不做养尊处优的少奶奶
1913年,潘赞化将张秀清从妓院里接出。据潘家后人回忆,潘赞化初时并无纳妾之念,但禁不住张秀清一再请求,便暂时让她在家里帮工。
张秀清表现出积极主动的人生姿态,愿意以身相许——青楼娜拉真的走向广阔的社会,凶险系数还是相当大的,长她10岁的潘赞化当然是她最好的归宿。在四顾茫然的她的意想中,潘赞化娶她,简直是义举。这年,她已年满18岁。
恰在这时,袁世凯派倪嗣冲为安徽都督,潘赞化遂卸任,携张秀清寓居上海。两人在上海补办婚礼,由唯一的来宾——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证婚。潘赞化替她改名张玉良。张玉良从时俗加夫姓,为“潘张玉良”,但不久即自署“潘玉良”,直至去世。
潘玉良将“潘”作前缀,当代有人批评为拖一条旧式女人的劣根性尾巴。但我想,那其实是高擎一感恩牌子,每写一次“潘玉良”,或别人每呼一下“潘张玉良”时,便要对潘赞化礼敬一次。她以女性特有的方式或曰权利,表达着女性特有的柔情。这个前缀,不仅没有降低她的人格和尊严,反而使她更女人,更中国化,更可亲、可敬。
潘玉良终于凭着她的才艺及智慧借助恩人潘赞化完成了她的一级跳:由艺伎到少奶奶。
潘赞化是潘玉良的启蒙老师。自古以来,“红袖添香夜读书”就是中国文人的理想模式之一。但潘赞化与有红袖情结的文人不同处在于,他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真的想将她培养成“以美的思想悦人”的一代才女。见她在绘画方面颇有天资,他还请了一位法国教师教她学画。
和潘赞化在一起的岁月活色生香。婚后不久,潘赞化辗转到韶关,秘密进入云南,参加蔡锷护国军的讨袁活动。
潘玉良一定感到特别骄傲,因为她得遇的是一个英雄,一个道义上、思想上及行动上的英雄。她比小凤仙要幸运得多。
据说,非常时期,为了使潘赞化睡得安稳,潘玉良曾持枪站在床前为其警戒。我想,这种新鲜刺激的生活,在素有男儿之风的张潘玉良心里一定激荡起了别样的豪情,她做这种事,享受多过惊惧。
喋血生涯让他俩有夫妻共患难之感。她和潘赞化的感情在相知相惜中得以升华。
令人感叹的是,潘玉良并未以养尊处优的少奶奶为终极目标。留守上海的潘玉良跟随邻居——在上海图画美术学校任教的画家洪野学绘画。起初,洪野以为作画只是闺阁寂寞的少妇打发余闲的消遣,看在邻居份上客客气气敷衍一下罢了。但他很快发现潘玉良氤氲在粗拙线条上的灵气。出于爱才的本能,洪野一面指导她作画,一面鼓励她进美术学校深造。
洪野的溢美之词让潘赞化格外高兴:潘玉良是他的成绩,他当然愿意她向更高远更开阔的艺术道路奔去。1918年,潘赞化动用和陈独秀的私交,在刘海粟处多次斡旋,终使潘玉良插班进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即后来的上海美专。潘赞化主张男女平权,潘玉良初期艺术路上,有他尽心扶携的姿态。他对潘玉良的救助和支持,有个人感情,但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
这种信仰和道义,在早期中国同盟会会员身上时有闪现。
潘玉良其实是潘赞化三民主义思想的实践与成绩。她是他的壮志之一。
她当然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可以想象,得知自己可以和诸多名媛同窗共读,狂喜之余,她一定会用大嗓门吼一出拿手戏。
潘玉良没有受过严格的“淑女”教育,犹如大地之女,保持着一颗“自然心”。一次,她和同班同学、画家刘苇一起在杭州山上写生,一时内急,躲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她快出来。她却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这样的话,一定多次响彻在潘玉良的心空,从而练就了她顽强的心理素质,这样的她才能够昂首挺胸行走在礼教残存的师生中。
在精神上,她还是那个逃跑的女奴,充满叛逆性和战斗性。
潘玉良在学业上突飞猛进,终于可以和潘赞化把酒话诗书了。两情相悦,潘赞化几乎很少回桐城老家。潘玉良格外考虑到:潘赞化最想拥有的是他俩的爱情结晶,如若生孩子,自己势必从此成为整天纠缠在奶瓶与尿片中的庸俗主妇,她的艺术将会梦断。怎样既让潘赞化享受到天伦之乐,又能保证自己心无旁骛地向艺术殿堂匍匐前进呢?潘玉良策划了一起关乎家计民生的大事。
1919年,潘玉良以潘赞化的名义给桐城方氏发去邀请函。方氏接到信高高兴兴赶赴上海。潘玉良让出主卧室,潘赞化的感情在潘玉良这儿,一时无法接受这种安排。潘玉良极力说服他,一再表示:方氏生下来的孩子就算她的孩子。
关于潘玉良力劝潘赞化一事,潘赞化在1956年7月24日致潘玉良的信中再度提及:“潘门之后是你一手培植出来的,从牟出世起,老方是你未经我同意,私自作信叫她到上海来,你还记得吧?你到亭子间去住,逼我与她同居,我本来决意不肯,因你的诚意感动,再三苦劝我,不要因你使我断后,否则,不从你,你就活不下去的样子。”
甚至潘玉良出国后,她情切的言辞、腮边的清泪似乎仍在潘赞化的耳眼边。
身为女人,潘玉良岂无母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生孩子,对小妾身份的她来说几同自断后路。但为了不中断学习,她只能这么做。
多少个无眠之夜后,她才做出这一决定?
一步步实施着预定计划,她的心想必流着血吧。可一拿起画笔,一捧起书,她便不后悔了。
舍得舍得,不舍怎么会得?她清醒地看到,由于出身,由于知识漏洞太多,自己的艺术路比常人更坎坷多艰。但她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
戴着纸枷锁,求学路坎坷多艰
潘玉良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没有陷入“忠诚的妻子、贤淑的母亲”等普通女性的窠臼。她从那广大的庸妇队伍中走出,没有将才华与智慧空掷在闺阁中——古来多少有才华的女子终逃不过生育这个劫,而她,终没有辜负上天赐予自己的才智。这是潘玉良之幸,亦是艺术之幸,更是潘玉良对潘赞化最大程度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