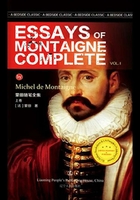在当今的某些作家看来,文学若写现实生活、写大众、写时代社会的重大问题或表现主流意识形态,就包含了社会目的和社会功用,就是浅薄、缺乏艺术;只有写个人体验、主观幻想而毫无目的意义,才可算作文学。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盲目的时髦,或可谓之文学的“时代病”。别林斯基曾这样说过: 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能够依赖自身的痛苦或欢乐而伟大,他只有植根于生活、时代、人民之中,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这也就是说,只有个体实践本身作为社会实践的表现、组成部分和浓缩,他的社会意义才可能存在。为人们所敬佩的文学大家鲁迅先生正是这样。鲁迅的创作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为了促进人民的觉醒和祖国的富强。面对当时“宁蜷伏堕而恶进取”的死气沉沉的现实,他发出“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的呼喊,并且身体力行地通过自己的文学活动为社会发光发热。他创作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药》等优秀作品,目的在于通过文学活动“引导国民前进”。鲁迅并非轻视文学特性,而是十分强调“诗美”和“技巧的上达”,并且明确指出:“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美的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的愉悦的根 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的。”应该说,鲁迅的文学活动堪为我们的一面镜子,他的创作以理性思想的巨大含量融入到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中,但并没有影响其艺术技艺,相反,鲁迅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巨匠。
在当今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在人们积极从事物质生产的实践、努力推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文学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袖手旁观地躲在一隅咀嚼个人的精神悲欢,还是积极参与到伟大的社会历史之中?这是需要每一位作家面对的。当然,我们并非把文学同其他事业刻板地等同、划一,要求其直接地变成具体的、在现实实践中如何行动的知识和方案,而应该以优秀的作品表现积极进取的精神与催人奋发向上的理想,从而能够使人们感奋起来,改造自然和变革社会推动历史前进。要发挥文学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性作用,我们的作家就必须从“象牙塔”中走出,投身到广阔的社会实践中。今天的生活变化多端,从事精神生产的作家自然有一个重新体验生活、认识生活的问题。
任何停留于忧伤、愤世嫉俗或超脱的创作心境,都不可能创作出真正反映时代生活的作品。而文学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重铸民族精神,就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以现实的生活和人生经验作为文学创作的根基,这不仅是当今文学走向新的生机的必要,也是创造时代文学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真正融入到人民群众伟大广阔的历史创造中,才能获取创作的活水,得到丰富多彩、新鲜浓郁的题材主题、诗情画意;只有努力到现实生活中去观察、认识和体验一切,才能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联系中达到对事物的正确体察,使个体实践经验成为普遍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只有把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建构同伟大的物质实践联系结合起来,努力描述当今现实运动的波澜壮阔,并从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发现新事物、新人物, 塑造富有时代精神的艺术形象,才能真正创造出既富有文学价值、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优秀作品。
1997年6月
文化的本体性与文艺理论重构
审视近三十年来文艺理论学科研究的深化,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即是对以往文艺理论体系逻辑基点的反思和质疑,提出文艺学理论的重新构建。然而,有两个瓶颈始终牵制着它的付诸实现:一是近年来本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相对薄弱,许多问题提出后一直呈悬置状态;另一是流于宏观泛论的层面,难以真正找寻到文艺理论的逻辑基点。诚如2006年《文艺理论研究》上方兢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我国文学理论界探讨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然而遗憾的是,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迄今尚没有实质性的成绩,基本停留在空洞的设想上。”此文有三个提法应特别引起文艺理论学科的重视和深究:一是对来自于苏联的统领我国思想领域几十年、作为我国文学理论原理基础的“大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起点的质疑;二是指出“走老路”的问题——即所找到的逻辑起点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某个结论来定义为文学的本质及忽视“中国特色”,三是强调应“从文学实践中寻找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诚哉斯言。的确,只有当我们不受制于任何一种金科玉律式的教条的束缚,不是从某种先在的理论观念预设和预定事物对象,而是真正从实际的审美、艺术活动现象本身出发,方可能有真正新的突破和建设。
本文拟通过诸多文学艺术实例反思既往“大哲学”理论的困惑与局限,并力图尝试从中寻找文艺理论的逻辑基点,具体探讨文化对审美艺术活动的本体意义及文化哲学、文化价值论对文艺理论建构的本体意义。
一、种种复杂的审美艺术现象与20世纪“大哲学”文艺理论的困惑
任何一种学说、理论,它的生命无疑在于解释对象事物时的合理性和信服力。某种理论可以只有某方面的解释功能或局部合理性,但如果作为普遍的释义原理而又陷入解释的困窘时,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反思20世纪美学、文艺理论的问题,一个最大的困惑和尴尬,显然在于以唯实践(劳动)论、经济基础决定论来解释种种复杂的审美和艺术现象,特别是由此出发把文艺的起源同文艺创造混为一谈的本质论、动因论。
例如众所周知的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劳动实践说”,自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前的文艺理论教科书和各种专著全部都持此说,之后亦有不少著述仍沿袭了很长时间。正是因为用劳动实践解释不了不同文艺种类的起源密码,例如一些与劳动生活无甚关涉的神话、歌谣、传说、绘画、雕塑、舞蹈、装饰等等,在思想解放的春风下理论界才重释了文艺起源问题,补充了人类生存多方面动因及审美意识自觉等因素的作用。这已是共识,在此不再赘述。但它却引发我们的再思考,究竟如何认识文学艺术活动的根源性因素,是什么对其构成本体的、内在的机理作用的?
这里主要想提出的是另一些审美与艺术现象的解释问题。
譬如当代美学家周来祥有一次讲到他的这样一个发现和思考:即汉画像石、画像砖上所绘图画保留了非常古老重要的商周时期楚文化的神话传说文化,山东、四川、河南均有,所绘之图是一个高大的神处于中间、两旁挟两个小神(当然都是人的形象),并且有题榜曰:一边为伏羲,一边为女娲。这样的艺术形象创造引起了周先生的注意,他寻思这个形象究竟是从哪来的?诸子百家、汉代文献中都没有记载,后来他发现可能是从《天问》中来,标志着从楚文化到中原文化的接续转化。他认为,一般说希腊神话传说有谱系,其实中国也同样有谱系,只是周代理性文化的强大断了神话系统,如《论语》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周文化中,其英雄都脱离了神话,而至汉代,汉高祖刘邦因为是楚人而可能把楚文化带过来了,于是汉代艺术中神话题材特别多。显然,面对这样的艺术现象,如何能以实践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解释得通呢?
又比如在戏曲方面近年掀起的“昆曲《牡丹亭》热”。本来,从20世纪伊始的反封建反传统已对传统戏曲构成了一次大的冲击,经过“文革”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舞台的横扫构成了又一次冲击,而在当今高科技电子影像审美泛化的强势下再一次被冲击,戏曲的危机早已频频告急,甚至有人极端地认为戏曲已死,然而,事实上呢?不仅没死,反而生机焕发,吸引了大批观众,像昆曲《千里送京娘》《琵琶记》等,尤其产生于明代的《牡丹亭》,重新排演后进大学校园演出获得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此可谓真正的一个文化事件。这并不是今天现实的生活实践,那么,这又如何能以实践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解释得通呢?
再以处于同样社会现实实践或经济基础条件下的文学创作来说。例如20世纪90年代文学,有新都市小说、新状态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私人化小说、女性身体写作、青春痛感小说等等,其不同的题材、体裁、审美追求,其互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美学征象和艺术风格,也是很难简单以实践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解释得通的。
所有这些艺术现象,显然都无法用过去“大哲学”模式化的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它们本身所展示、所表现的东西,以及艺术家的创造冲动、目的、心理机制,都未必一定直接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实践、现实实际生活的反映相联系,相反,倒更多是来自某种历史积淀或文化原型等等的心理、意识、情思之类精神文化,来自它们与时应和所激发出的想象、幻想、虚拟、象征。而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对这种种的复杂的审美艺术现象的解释,却基本囿于单一的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与反映论的解释模式,认为一切美与艺术的创造都来源于一定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是作为其反映产物而存在的,以至与所释现象本身显得颇相隔膜。诸如下列类似理论界说,是当时普遍的解释模式:
美既不是物的自然属性,也不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它的根源深深地蕴藏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因此,要探究美的规律,把握美的本质,……应该到人的整个社会实践,首先是到人的劳动实践中去寻找。
进行美的创造,是离不开人们一定的审美理想的,……一定时代的审美理想其表现形态尽管十分复杂,可是只要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它总同一定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美术,同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样,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发生发展,归根到底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作用,表现在美术的发生发展上,是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美术的主要内容和形态。
艺术既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只能来源于实际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
问题是,这种“大哲学”文艺理论很长时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也不允许有任何的不同看法或其他解释。历经了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和那场美学“大讨论”,无论吕荧的“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高尔太的“美是人感受到的存在”,还是朱光潜的“美的主客观统一说”,均被视作唯心主义而遭到批判贬斥,最后只有蔡仪的“美是客观的,不在于我们的意识作用”、“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被肯定下来。那么,既然对于审美、艺术活动的认识属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重大思想斗争和立场问题,其结果便只得群体一律地搁置起审美与艺术的复杂性而尊奉唯物主义一说。如聂振斌先生所指出的:“由此产生了一种简单化倾向:以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作为美学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因而把历史上许多有价值的美学观点及美学派别否定和排斥了。”在这样的特定语境之下,许多审美、艺术活动的复杂现象自然无以探讨,文学艺术的真谛也就只能屈从于政治意识形态了。而这也正是20世纪“大哲学”所带来的文艺理论的困惑、困局所在。
二、文化本体对审美、艺术活动的“规定和规划”
自20世纪文艺理论成为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人文学科以来,先是西方哲学话语范式对传统“国学”整体文化观的冲击和取代,而后则是苏联文艺理论体系的完全照搬,“上面的问题出自一个更深层的思维背景,就是来自于苏联的‘大哲学’观念,认为哲学是对整个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最革命的哲学。因此,哲学成为了一切科学的基础,所有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上;具体地说,也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这个‘大哲学’观念,统领我国思想领域几十年了,至今还没有丝毫的松动,成为人们思维模式中的一项公理,天经地义,不需要论证,也没有人提出过应该对这个原则进行论证”。不能不说,这种僵化思维确乎严重地束缚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深入推进。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回到审美与艺术活动本身,仔细体察和研究构成其本质联系的相关要素、机制性因素,就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作为历史的与现实的共时文化结构系统(或曰文化语境)对于审美和艺术活动的制衡、规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