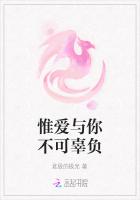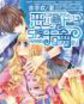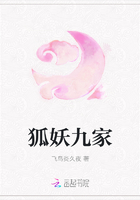近年来,通识知识对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得到了政府和法学教育界的认同。通识课程的设置、通识知识的传授在各法学院校中都受到一定的重视。但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等同于通识知识的课程炒作,因而并没有真正达到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目的。一方面,知识的爆炸和专业化的需求使得通识教育的空间很有限,在现有的学分制度下,严重受到学分制瓶颈的束缚。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例如美国,有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大学的通识课程在大学课程中的比例呈逐渐降低的趋势:1914年通识课的比重为55%,1939年降为46%,1993年再降至33%。如何在大学中使通识教育有一定的位置已成为有些大学教育的保卫战了。另一方面,有关人文方面知识的实际教学效果并非令人满意。原因在于受工具主义法律传统的影响,大学教育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培养工具型人才的摇篮。各大学从新生入学起就作了严格的专业划分,法学专业就是众多狭窄专业的一种。这种过度强调法学专业性的外在条件,必然使学生将认识的视野局限于专业知识范围,从内心深处排斥通识知识。很多学生并没有认识到人文知识的重要性,只是把对这些知识的学习当做获得学分的手段,当做外在的客观化的知识记忆,因而人文知识并没有真正内化为学生的智慧。在这种状况下,实现培养具有较高人文素质法律人才的目标非常艰难。
(二)重规范知识轻方法知识
我国法学教育界长期以来将法律知识传授的中心定位于规范知识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以法律规范为核心的部门法不仅占据课程体系的绝对优势,而且部门法的教学内容集中于对现行法律规则的注释,教科书的内容甚至体例都以某一种法律文件为主线并贯穿始终;教师授课也拘泥于对法条含义的解释,而对于本学科的基本法律原理很少有人问津。另外,我国法学教育中还存在着轻视对于法理学、法史学、法社会学等训练学生理论思维、夯实学生理论基础等方面知识的课程的问题。因为在注重条文主义法学教育的人看来,法理学等课程所研究的问题属于法学中抽象的、一般的问题,不能直接参与法律实践,也就是说它不能被用来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
这在将法学作为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工具理性的人来说,似乎是无直接用处可言的。法理学研究的问题对那些具有常识并需要挣钱养家糊口的人来说,也许连一分钟都懒得思考。有人形象地将重条文轻理论的教育概括为“条文主义的法律教育”。“而这样的法律教育只能训练出‘谨愿之士’(即墨守成规、不知活用)、‘偏倚之士’(即除条文外不知有其他学问)、‘保守之士’(即对于现行法令,不解善恶、惟知遵守)、‘凝结之士’(头脑中充满了现行条文,对于新发生的事实、思潮,格格不入,毫无汲取进步的可能)。”这就是以规范知识为中心的教学定位所带来的危害。
(三)国内法知识与外国法、比较法知识配置不尽合理
建国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在国内法知识和外国法知识等资料的选择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前。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法学教育全面学习苏联,包括讲授苏联法学、采用苏联教材。1951年教育部制定的《法学院、法律系课程草案》规定:“阐述新法制的进步性及优越性”是贯穿各课程的主线;“讲授课程有法令者根据法令,无法令者根据政策如无具体材料可资根据参照,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苏联法学教材及著述为讲授的主要参考资料。”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法学教育的知识资料大都是苏联法律理论。例如,教育部在1953年规定的法律院系的统一法学课程,包括苏联国家与法权史、苏联国家法、苏联民法、苏联刑法、土地法与集体农庄法、人民民主国家法、中国与苏联法院组织、中国与苏联民事诉讼法、中国与苏联劳动法、中国与苏联行政法、中国与苏联财政法。在教材方面,从1952—1956年,我国翻译、出版了165种苏联法学教材。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法学教育复兴到目前。这一时期法学教育知识资料的特点主要集中于本国法的授受,“以讲授政策、法律的条文为根本,为制定出来的政策、法律作正当性的注释”。外国法律知识资料只是少量的、以批判为目的的选用。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外域法律知识所占比重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国内法知识与外国法、比较法知识配置还不尽合理,学生的视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种状况是不利于全球化时代开放型法律人才培养的。
(四)价值知识的边缘化地位
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价值观的偏误,事实知识在我国法学教育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价值知识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我国现有的知识教学中,价值知识与事实知识的比例严重失调,特别是关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或价值教育几乎是空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客观化的、具有极强操作性的科学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成为知识的典型形态,而价值知识的地位则相反。美国学者贝拉认为,价值知识的边缘化地位的原因是在“科学知识的文化范典”下,价值系统及观念被视为不是“知识”。自然科学领域如此,社会科学也在这个范典下,也只重“客观性”,视一切社会问题的本质主要是“技术”性的,而非道德性或政治性的,至于关乎什么是好的人生、好的社会的伦理教育则不再是高等教育的重点。第二,受我国文本主义教育传统的影响,在教学中专注于规范条文的注释,而对于事实知识所蕴含的价值则是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因此,很少有人主动开掘事实知识之中所隐藏的价值内涵。第三,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不成熟、不完备,是法学教育中至今没有专门的旨在训练学生职业道德修养方面的课程的客观原因。在我国,人们对法律职业规范意义的认识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有关法律职业道德准则的出台也是近些年的事情。因此,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种知识还没有成熟的理论体系,自然价值知识在教学中就成了可有可无的内容了。法学教育的这种状况大抵上就是人们于内心深处将法官与传统的咬文嚼字的刑名师爷联系在一起,将律师等同于刀笔讼师的教育根源。只重视规范知识,忽视价值知识的文本主义的教育模式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或许只关注一堆抽象的规则和规章,或者说他们只知道尊敬法律,而遗漏了他人是作为完整的、真正的人这一现实,同时也丧失了自身对善恶判断的能力和对正义孜孜不懈追求的精神动力。
二、知识传授误区的矫治
我国法学教育知识传授中所存在的误区亟须矫治。因为学校知识配置情况关系到学生知识结构是否合理,进而关系到法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培养高素质法律人能否实现的根本问题。根据前面对现存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矫治现存误区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专业知识与通识知识的融合
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要真正实现对学生的人文精神的塑造,除了重视通识知识课程,确保通识知识课程授课的质与量以外,最重要的措施是真正将非专业知识浸润于专业教育过程之中,实现专业知识与通识知识的融合,消除学生对通识知识轻视的心理。笔者认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措施之一,是解决过早进行专业划分的问题。
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赫钦斯曾详细分析了对大学专业性过渡重视的危害,并且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减少专业划分。他将大学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部分,相应地,大学分为形而上学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和自然科学学院。“未来的牧师将毕业于形而上学学院,律师将毕业于社会科学学院,医生和工程师将毕业于自然科学学院。我们还应该期望在形而上学学院发现未来的哲学家,在社会科学学院发现未来的行政官员、法官、立法人员、政治家和公共事务专家,在自然科学学院发现那些将毕生致力于科学探索的人。”其结果是“未来的律师应该具备和牧师及医生一样的普通教育训练。他将学习形而上学,因为没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会毫无意义。为了他所从事的这一重要职业,他将接受这种哲学的训练,掌握法理学,而法理学是由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建立在上述学科基础之上的法哲学组成的。他还将学习有关社会的一些经验性和历史性的知识、法学史和法律机构、经济学和经济史。他将对物质世界有一些了解,但仅仅局限于形而上学给他带来的那些东西。”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赫钦斯否定专业(职业)训练的大学自由教育思想并非完全赞同,但是他修改大学专业观的建议,对解决我国法学教育中存在“有学识、无教养”的问题是有启发性的。另外,日本在专业设置方面的做法对我们也有借鉴的意义。众所周知,日本是十分重视学生教养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些大学的新生在第一年先进入教养学院学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等大学基础知识。现在有的日本大学如东京大学,本科生入学时只分文1、文2、文3,理1、理2、理3等不同的大班级。其中文1班的学生将来有资格进入法学院,但是两年后,也可以选择进入其他学院,但其他班级的学生不能进入法学院。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必须重构专业教育观,实行“大平台”招生,在学生接受充分的通识教育后再进入专业教育阶段,这样可以使学生真正受到人文精神的浸润,因而对实现培养既有学识又有教养的人才的目标是有借鉴意义的。
(二)提升方法知识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
目前,加强对方法知识重要意义的认识,提升方法知识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是矫治我国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误区的对策之一。我们应当看到,方法知识虽然不具有直接的实用功能,但其蕴涵了说明具体案件处理是否能够说服人,或解决问题的理由是否成立等问题的理性根据。
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一书中揭示了法律一般理论的特性及其与法律实践的密切关系:“正如关于礼貌和正义的一般理论那样,法律的一般理论肯定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旨在阐释法律实践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结构而不是法律实践的某一具体方面或具体部分。除了具有抽象性外,它们是建设性的阐释:它们力图充分地说明整个法律实践,同时还力图在探明法律实践和对这种实践的最佳论证之间保持平衡。因此,在法理学与判案或法律实践的任何其他方面之间,不能划出一条固定不变的界线。法哲学家们对任何法律论证所必须具备的一般要素和阐释基础展开争论。我们可以从反面来谈。任何实际的法律论证,不论其内容多么具体和有限,都采用法理学所提供的一种抽象基础,而且当这些对立的基础产生矛盾时,法律论证就只能采用其中之一而反对其他。因此,任何法官的意见本身就是法哲学的一个片断,甚至是哲学被掩盖、人们只能被引证和一系列事实支配,其情况也是如此,法理学是判决的一般组成部分,亦即任何依法判决的无声开场白。”这说明法律一般理论是判案或法律实践的理论依据和思维方法。在司法实践中,解决涉法问题的方式大都是理智的、说理的、理性的,而采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质上是解决者运用特定的逻辑思维形式,根据法律规定来论证某个行为正当与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职业者的理性思维能力是创造性地适用法律的关键。历史上的优秀法官和律师都是具有创造力的人,而他们的创造力的源泉就在于他们充满了理性的智慧,具有形成出色法律意见的理论思维能力。获得这种能力的进路,就在于法理学等方法知识。所以,“未来的法律工作者还将比以往的法律工作者更加熟悉那些使法律判断力得以增强的法的哲学、历史、经济、国际及社会基础等方面的知识。”“因为大学按其本意来说,能够提供的恰恰不是对实践经验的介绍,而是对理论知识的传授。对法律实践来说,理论知识的传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所以应该首先通过理论知识性的教育来使从事实践的法律工作者能够进行专业的、独立而有条理的思考,并且使其获得必需的法律判断力,从而能够正确认识新的法律问题,对法律教义的基础结构进行回顾,同时找出正确的答案。只有理论知识性的教育才可能使他们有能力应付现今法制的巨大变化。最终也只有理论知识性的教育能够避免产生只会机械适用法律的实证主义者,也就是只会进行手工劳动的法律工匠,并且促进有文化、能够独立思考、行动有责任意识、通才型法律人的产生。”总之,理论性知识使我们能够系统地理解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来源和气质,使我们能够养成批判地看待以往的、既有的法律知识的习惯,也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判断问题、形成法律意见的严格的法律思维能力。因此,方法知识应成为法学教育的关键。这在成文法的国家和判例法的国家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