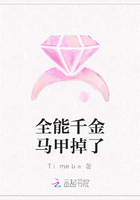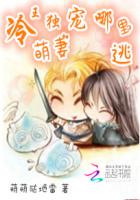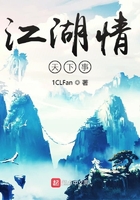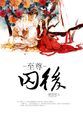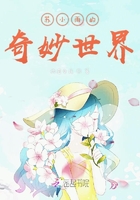(二)设置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有助于学生掌握法律职业伦理知识体系通过设置法律职业道德课程,传授法律职业伦理知识可以使学生掌握法律职业伦理知识体系。张志铭教授将这一知识体系具体分解为四个方面:(1)对道德评价的认知:善的存在。法律职业道德评价是存在于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活动中的有关是非、善恶的评价。道德教育就是要使人们在辨认法律职业道德评价独特性的基础上,认识到自己行为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这种自觉,是要求人们包括职业者负责任地行为的第一步。(2)对道德准则的认知:善的含义。道德上的善具体表现为社会所承认和遵从的一整套道德准则。不了解这些道德准则,就不能把握道德上的善的具体含义。因此,法学教育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准则作为传授的目标之一。(3)对道德根据的认知:善的理由。即道德教育在道德根据认知方面的任务,在于为分析各种道德论点提供工具。(4)对道德冲突和道德理论的认知:善的实现。道德实现的关键在于解决道德冲突。道德冲突实际上就是不同道德理由的冲突。要解决道德冲突就需要将不同的道德理由整合为连贯一致的形态,形成道德理论。因此,道德教育在道德冲突认知方面的任务,就是要借助道德理论为解决道德冲突提供经验和各种选择方案。学生对法律职业伦理知识的掌握是实现对学生道德品格教育的前提。只有学生了解法律职业道德准则、把握法律职业活动的是非评价标准,才可能将其转化为内心信念,并落实在行动上。
二、寻求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修养
法学教育中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认知只是实现对学生道德人格教育的前提。从根本上说,将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内化为学生的道德自觉,培养学生高尚道德品质即由知之到信之的态度或情感的养成,才是法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因此,职业道德教育的成效决不在于学生掌握了多少法律职业道德知识,而在于将道德知识内化为学生的品质。“道德知识对于个体的多少价值不仅在于实现从‘不知’到‘知’的跨越,更在于从‘知’到‘信’的(信服、信念、信仰)的提升。单单靠一般课程的教学和校园文化的影响,显然不足以形成学生坚实深厚的关于道德价值的理解。”其实“任何人都不能被灌输或施加条件来诚实地讲话或公正地判决,因为实施这些美德都要求一种自觉意识和自由选择的品质。”因此,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只能“提高学生‘进行反思性的道德判断能力’,在道德推理方面提供系统的教育,并尝试间接地影响律师在职业道德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无疑,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修养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关键和难点。
根据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将知识、技能、态度领域中的教与学的差别简化为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那么法律职业道德教学应归属于态度或情感教学。态度或情感教学与伦理规范知识教学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可以以口授的方式直接地教;而道德作为一种态度有别于普通的知识,也不同于普通的技能,只能间接地教。学生在情感或态度上的“所知”、“所会”即认同感的形成。需要诉诸学生在学与用中对于所学和所用的知识和技能价值的一种亲身体验。伦理学研究表明,道德本身所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彼此理解对方的需要、愿望和观点是建立合乎道德的关系的根本,只有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每个个体才能产生合乎他人、社会观点、期待、利益的道德意识、判断和行为。而要理解他人的态度,意识到他人的思想感情,只能在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在社会角色的承担中才能完成。
法律职业道德涉及的是法律职业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即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等不同角色的伦理关系。正如美国学者杰姆·E.默里特诺教授所言:法律职业道德领域与其他实体法领域不同,它们对于律师来说是经验的东西,它们建立在由某种关系引出的信息上,律师是这种关系的一方。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大部分内容与律师和客户、律师和立法者、律师和社会的关系不可分割。换句话说,大量的职业道德规范通过律师亲身经历的关系形成,不像在其他实体法领域,律师只间接感受法律。从这方面来讲,职业道德本身的规则在某些方面与比赛规则类似。如果不遵守比赛规则就不能参加比赛,选手虽然也遵守比赛规则,但他的表现实际上是对一种特性的反应,似乎与任何规则毫不相干。选手要赢得比赛(做一个道德的律师),不是通过学习比赛规则(虽然必须知道),而更多的是通过经常训练(从事律师活动)。就教学方法而言,学习比赛规则可以和比赛分开。选手可以通过阅读和讨论比赛规则很好地了解规则的基本含义和背景,但是要领会微妙之处,必须自己亲身体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独特性决定了法学教育必须寻求一种不同角色交往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情感体验的情感场,才能使学生将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判断和推理能力,并最终促进学生道德人格养成。
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体制比较成熟的美国,寻求有效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方法一直是学者讨论的重点。在美国,常见的法律职业道德教学方法主要包括课堂讲授法、渗透法、问题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示范、体验角色的代理活动等。这些方法在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教育中具有不同的作用。
(一)课堂讲授法、渗透法、问题教学法的价值
课堂讲授法、渗透法、问题教学法具有实现法律职业道德认知的价值。
课堂讲授法或讲演式教学法可以有效地实现对法律职业历史和法律职业伦理规则的传授,而且也使学生对“特别适合解决律师的道德困境的哲学观点”有了背景性的了解。渗透法是把道德规范教学与其他课程的教学联系起来,在其他课程的教学中渗透关于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的教育。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促使更多的教师关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问题,“让更多的教师作正面的角色示范,并为教师提供模仿有责任行为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接触因各种不同实体法产生的法律职业道德问题的实例。问题教学法是利用法律实践中的问题和难题来讲授法律职业道德。问题教学法注重解决律师在执业中面临的各种困难,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冲突和道德理论认知,使其形成敏锐的判断力和推理能力。
但同时也有人对这些教学方法提出批评。“讲演式教学法除对一些有限的教学目标会起作用外,在课堂上的这种苦心规劝不是培养律师对个人行为负责的责任感的一种方式。单纯说教的作用是有限的。”渗透教学法在实践中存在的弊端除了缺少激励教师运用这种方法的机制外,更重要的问题是,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与特定实体法领域的理论基础没有什么密切联系,而且只能根据其他课程的安排来决定道德规范课程的安排,使得这种方法不能完整和连贯地展示法律职业道德的认知内容。问题教学法即把职业道德课描述为解决一系列问题,会使学生误认为道德准则是一套解决律师面临问题的规则,事实上律师并不总是生活在困境中的,法律职业道德也不都是关于如何解决难题的技巧。法律职业道德对法律职业的最大影响在于回答如何处理职业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如律师应该怎样对待客户?在日常交往中如何保持诚实和谨慎?
(二)案例教学法、示范和体验角色法的价值
案例教学法、示范和体验角色的代理活动在学生法律职业道德人格的养成方面具有间接的价值。这些教学方法之所以能够促进学生的道德认知的内化,使之由知之向信之、为之的转化,关键在于这几种方法都为学生提供了“角色体验”的机会。
1.案例教学法的角色模拟体验价值。案例教学法对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价值在于为学生提供了角色体验的机会。一方面,案例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了法官角色体验。在案例教学中,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该判决都必须首先从法官的观点即从诉讼意见出发来探讨问题。要求学生以一个法官角色从公平的司法角度重新审视这一案件,并就该案的判决智慧发表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案例教学法为学生提供扮演律师角色和当事人的机会。它提供给学生一系列的具体争论,强迫学生扮演原来争论的双方和他们律师的角色,并重新演示这些争论。通过不同角色的扮演,使学生亲身体验到了法律职业中不同角色的道德要求,有利于其道德认知的内化即法律职业道德情感和态度的养成。具体来说,法官角色的扮演,可以加强“学生对同情的理解力和为了法官谨慎的中立而压制一切同情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它增加了他对于在这些不同的态度的情形中来回摇摆迷失方向的忍耐力。这样,案例教学法通过培养我早就称之为最基本特征的特殊的两面性成为道德想像力的坚实基础。”因为法官的角色迫使学生对于有疑问的案件也要以推理和公众认可的方式作出最终的决断,这就阻止了学生不断接受价值领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上的趋势,也避免了学生养成独断专行的品性。案例教学法为学生营造的在道德模棱两可的情形下作出推理,“结果是彼此对立的两种态度融合在了一起:扩大了的同情理解能力与用最冷淡、最疏远、最法官似的眼光看待每一个诉讼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对多种不可调和的人类利益的宽宏大量和即使对道德的希望全部落空,仍参加争论,听取辩论,作出判决,把支持判决的理由有机地组织在一块的不屈不挠的意志结合在一起。这组复杂的态度虽然互相矛盾,然而却描绘了一个公认的道德理想为公众着想的坚忍精神的一种理想。”通过律师角色的扮演,强迫他们为不信任的或者他们认为是违背道德的立场进行辩护,可以促使学生暂时把自己早先的信仰搁置一边,努力揭示它的长处并清楚表述出来。“这样,学生就能习惯于用友好的眼光去看待甚至他们个人反对的观点,不久,他们就能获得区分任何一项摆在他们面前的主张的长处和弱点的某种技能,这些主张既有他们认可和赞同的,也有他们不熟悉或者道德上感到厌恶的。”另外,案例教学法也将学生置于对客户利益的忠诚和对法律忠诚的道德两难境地,使学生在解决道德两难的问题中,领悟法律职业中的伦理关系,形成谨慎和热心公益又保持正当限度对客户忠诚的法律职业道德品格。“案例教学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培养这些品格,为学生的法律实践做准备。”
2.角色示范(包括学习律师代理的案件和指导人的角色示范)的模仿价值。角色示范主要包括真实角色示范和讲故事两种。美国学者杰姆·E.默里特诺认为,模型越接近要学习的角色,示范就越有效。最有效的模仿律师的行为是模仿律师角色。学生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模仿律师:间接地通过讲述律师案例,直接地在真实或模拟的客户服务中同律师一起工作。讲故事这种方法在课堂上展示的活生生的道德,使学生通过观察体现正直、信誉、关心人权和职业群体意识的示范行为获得间接的角色体验。而与律师一起工作会比讲故事或一般的示范作用更大,因为它直接涉及学生参与和情感交流,并与被模仿的行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3.诊所教学的真实角色体验。诊所教学对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价值在于将学生置于一个真实的人与人的关系:律师与法官、律师与当事人、律师与律师的关系中,使学生亲身体验了律师角色的活动并使其面临法律实务中出现的、更复杂的、更有创造性和更令人尴尬的道德问题,学生在试图解决这些道德问题的过程中,领悟道德规则在实践中的微妙之处。例如,当一名学生以律师的身份谈判时,学生就会体会到诸如禁止向他人虚假陈述等有关律师从事这种活动的道德规则,这种体验对于学生道德情感或道德态度的养成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体验角色的代理活动不仅提供有关事实(这些事实使许多控制律师行为的规范发生效力)的重要知识,而且提出了恢复学徒制的优点的最大希望——通过指导者的影响使遵循道德的律师适应法律职业。”同样,学者们对于这些方法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价值也有不同的看法。堪萨斯大学法学教授菲利浦·C.凯萨姆(PhilipCKissam)认为:案例教学的“严谨”和“非人格化”以及法学院的考试、评分和班级排名系统带来的激烈竞争,无形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隔阂,此外还使得对人与人关系的限制变成正式的、非人格化的和等级化的术语。然而,对于道德的有效思考要求在人们中有一个更开放、更平等的、冒险的和相对不受限制的对话,而且这种思考使人处在与他人相关的风险中。对于这种对律师和法律中的道德问题的考虑和反思,案例教学加期末考试的法学院没有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威廉玛利学院法律职业技能项目主任詹姆斯·E.默利特诺(JamesE Moliterno)透彻地分析了诊所教学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方面的缺陷:校内法律诊所提供了相对较短(通常是一个学期)的实践机会。在此期间,学生开始与指导人和合作者建立关系并为一些客户提供服务。但通常学生接手的案子是前一个学生未完成的工作,新手除了从案卷中获取有限资料外,并不熟悉他的前手建立的关系,因此使得新手所了解的有关客户的信息可能是错的。同样,当新手与客户建立一种关系后,又将此案传给下一组同学时,也会发生类似的无知或错误。而早期建立的客户关系对最终结果的影响直到很晚才知道,最早接手案子的学生不能从早期建立的客户关系中学到经验教训。另外,他还分析了诊所教学利用真实的客户作为训练工具,可能会伤害无辜,这也是很不道德的。对于模拟示范,詹姆斯·E.默利特诺亦分析了它的不足,即不当的行为也可能成为模仿的对象。在态度性或情感性的道德教育中有三项基本指标:教育者有无情感——人格资质与技能、是否形成情感交往关系或“情感场”、受教育者是否有情感经验的积累和改组。根据这三项指标考察法学教学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课堂讲授法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中,缺乏情感交流的情感场和受教育者情感经验的积累,因而在培养学生道德认知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对学生的道德品行,影响甚微。案例教学和体验角色的代理活动等则可以为学生创设情感场、为学生积累情感经验提供机会。这些方法对学生从道德认知向道德品行的转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如何根据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特殊性来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是法学教育实现其应有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价值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