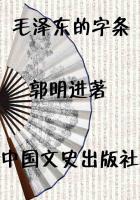忧郁与成长同在
我的好学生时光一去不返。初潮的成人礼后,我迎头痛赶,渴望再次力争上游。然而,小马过河时,冰冷的河水无情地侵蚀了它奔腾的骨质,看起来四脚俱全,其实,已伤入骨髓。日后,当别人日行千里时,它只能折价为半。年轻时的倔强、稚嫩,最后都化作了成长过程中的一路忧伤,原来,即使再有勇气和信心,一切都会来不及。初三毕业,我以中下游的成绩考入一个中下游学校的高中。高一的时候,我清秀善感,给自己取了此生第一个笔名,名曰“五百里”。
我那时已经有了一米六的身高。我在街上偶遇了廖华。一个矮矬的小胖子,还是很黑,笑起来努力睁大一线天的双眼,满脸雀斑跳跃。他不再背书包。廖华说,他爸爸所在赫赫有名的大瓷厂被改制合并,廖科长开了一个私人瓷器作坊,廖华开始学画瓷器。“我画的是花鸟”,廖华说。但他再次送给我的一张画,是人像画。画纸上一个清秀的女学生,齐耳的学生头,短发在耳际弯成一个好看的月牙弧度,鼻梁上架着一副微微往下滑的眼镜。画的是我。
再后来,我高考落榜了。我在市中心的中山路商业街给浙江的私人老板看店卖鞋子。星期天的时候,驾一张钢丝床当特价车摆放在店门口,“哦,价廉物美的温州男女牛皮鞋便宜卖哦,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温州男女牛皮鞋,价廉物美便宜卖哦……”
廖华站到我的鞋摊前时,我正举着一只硕大的假牛皮男鞋当街起劲叫卖。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笑,一线天的眼睛因为满脸严肃,仿佛真的变大了一些。“呃……廖华,你要不要给你爸爸买一双牛皮鞋?”我还是戴着眼镜,眼镜还是时不时顺着鼻梁往下滑。
“叶卿卿,你应该好好读书,你应该是要当作家的。”廖华的语言,已经完全成人化。我还是举着那只硕大的假皮鞋,呆呆地望着他,再也说不出半句话。
“你跟我来学画瓷器,画花鸟,天上自由飞翔的小鸟,和枝头盛开的鲜花,好不好?”廖华说。他的话语,似乎有了一丝真正恋爱的含义。我不说话。但我还是觉得温暖。我顺从了我的温暖感受。
廖华的花鸟已经画得很好。他总是画极鲜艳的花儿。花瓣层层叠叠,绵密鲜红。偶尔添上几颗露珠,仿佛伤心的眼泪,洇血而成夺目光华。他画的鸟儿总是成群结伴,却有总有一只形单影只,独立枝头。那只独立枝头的鸟儿,总是保持一个回首的姿态,大睁着又黑又圆的眼睛。鸟儿的眼睛里,透露着满腹心事。
“我画虫子和鱼儿。”看了廖华画的花鸟之后,我对他说。我先是在那种半透明的玻璃纸上印着摹本描画,小半年以后,再丢掉摹本,独自在玻璃纸上画。我画完了整个寒冷的冬天后,有一天,廖华将一个干净的白胎瓷瓶摆在我面前。“你现在开始在瓷器上画。”他说。我不敢动画笔。
“你就想,春天来了,虫子从冬眠中醒来,蠕动着身子,从芬芳肥沃的土壤里抬起头来,河水解冻了,鱼儿摇头摆尾,在水里自在地游来游去……”廖华的语言,已经文学得很是了得。他已经不背书包很久了。那些瓷器,和瓷器上变成花鸟的油墨粉彩,将他熏染得如此意境唯美。
我亲手敲碎了我画了一条鱼的瓷瓶。一切都和我想象中的大相庭径。那不是河中欢游的鱼儿,反而令我联想到刀俎。瓷器碎裂的清脆声响后,我又“啪啪”拗断了手中的画笔,掀翻了颜料盒。廖华家瓷器作坊的后院里,有一棵常青树。瓷器的碎片、斑斓的颜料,断折的画笔,满地狼籍令树木戚戚。它哗哗摇着树叶,以一种不败之绿,安抚着我的哀哀哭泣。
郭小若就在这时朝我走来。我一直忘了说,郭小若也在廖华家的作坊里学画瓷器,比我更早。
“卿卿,是应该要当一个作家的。”郭小若,手抚着我伶仃的肩头,这样说。她一直和廖华心有灵犀。我喜欢她。
我在喝了廖华与郭小若的喜酒之后,整理行李去了上海。我的父亲,在替我装了满箱子的书之后,突发脑溢血,就倒在我的箱子旁边。我的箱子里有《红楼梦》、《乱世佳人》、《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茶花女》,还有三毛的《万水千山走遍》和萨冈的《你好,忧愁》。
从此,我与书,书与我,天涯常伴。
第一次立足在上海站,有一个身型清瘦高挑的男人来接我。他穿着藏青色中长呢子大衣,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看起来,没有什么故乡人的气息。
“秋秋,小若说,让我来接你。”他是郭小沫,他又随意替我改了名字,从不问我,愿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