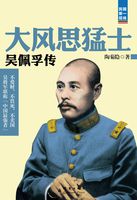御史台监牢,黑夜沉沉,羁押房内,刑具陈列。一高一矮两个衙役正在威逼苏轼。高个衙役对苏轼说:“此门进来容易,出去却难!”苏轼说:“我未犯王法,如何不能出去!”矮个衙役说:“就算你明日出去,今日也须掉层人皮。”苏轼笑道:“哈哈,今日我虎落平阳,你就来欺负我!”高个衙役说:“就是摆明了欺负你!”举棍要打,想了想,似乎没有理由,抬起的手又放下了。
矮个衙役忽然说:“哥哥,他骂你。”高个衙役脑筋似乎不灵,疑惑地说:“他没骂我呀,他怎敢骂我?”矮个衙役说:“他骂你是狗。”高个衙役怒道:“你才是狗!我长着耳朵呢,他骂我,我会听不见?滚!”矮个衙役急得抓耳挠腮,说不出话来。高个衙役对苏轼说:“苏轼,听说你是个才子,可我这里只认钱财,不认文才。”举手欲打。
这时,范镇大步进来,“啪”地将一包银子扔到地上:“你不是只认钱财吗?看看这些够不够。”两个衙役一惊,急忙跪下说:“小的给范大人磕头!小的哪敢收大人的钱!”范镇说:“罗唆什么,叫你收你就收。”两个衙役连声称是。范镇厉声对他们说:“你们给我看好了苏轼,若是少了一根毫毛,我让你二人不得好死。”苏轼说:“恩师何必助长牢狱的索贿之风!”范镇说:“姑且保全了,其余日后再说。明日朝堂我会据理力争,保你出来。”
颐心殿中,仁宗正在翻阅殿试的制策,内侍张茂则递上苏轼的制策,仁宗高兴地阅读着,口里还称赞着“苏轼乃进士中第一才子”。当读到“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宫中贵姬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仁宗转喜为怒,轻轻拍了一下龙案,站起身来。张茂则吃了一惊。
迩英殿外,王珪和欧阳修在殿外等候。张茂则走出殿外,向二位大人行礼。张茂则说:“王大人,皇上宣你进殿。”王珪向欧阳修点头示意,跨进大殿。欧阳修也欲入殿。张茂则为难地说:“欧阳公,皇上没说要见您。”欧阳修一惊。
迩英殿内,仁宗高坐。王珪奏道:“陛下,御史台因苏轼所呈制策中有狂悖言辞,并忤逆圣上,现已将苏轼羁押牢中。”仁宗仔细观察着王珪,做出愠怒的样子,说:“羁押得好!朕以为他该被羁押。”王珪听了,十分高兴,从袖中掏出百官联名书,向仁宗禀报:“陛下,这是百官联名签署的奏章,称苏轼一再诬贤欺圣,目无君主,罪为大逆,该当处死。”
张茂则将长长的奏章呈给仁宗。仁宗细看奏章,暗暗吃惊。王珪察言观色,急忙对仁宗说:“陛下息怒,苏轼年轻无知,陛下也不必与之计较。但据臣所知,联名百官却群情激愤,都说苏轼狂悖无道,上次撰典之事已得陛下宽恕,却不知悔改,如今竟藐视起圣上来了。百官还说,若再纵容苏轼,则引天下读书人效仿,视教条规范如无物,风气败坏,朝纲大乱。陛下,微臣虽然试图劝服,但百官之愤慨不平非臣过往之所见。”王珪以为仁宗会大怒,但仁宗却并不表态,只是说:“朕知道了,此事明日上朝再议。”
第二天上朝前,众臣站在崇政殿外等候,纷纷窃窃私语。有人说:“太过分了!如此狂生,从未见过!不杀不足以正朝纲!”王珪沿台阶而上,微笑着对大家说:“诸公好。”众臣说:“王大人好。”欧阳修和范镇走上台阶,却无人理会。范镇对欧阳修说:“欧阳公,今日上朝,我二人要为苏轼辩护,无论如何要说服皇上。”欧阳修沉重地点头。一会儿,张茂则从殿门里走出来说:“皇上有旨,今日不朝。”
众官哗然道:“这苏轼实在大逆不道,定是他使得龙颜震怒,皇上连朝都不上了!皇上还从未缺过早朝,这都是苏轼所致。苏轼沽名钓誉,狂悖无理,目无人主,罪该处死!”王珪并不说话,悠闲得意地从群臣之旁走过。欧阳修和范镇呆立在那里。
御街上,刘几率众太学生走来,黑压压的一片,他们穿着统一服饰,其状悲愤,正游街抗议。引得行人纷纷驻足观望。行人议论纷纷:“新科进士苏轼制策直言犯君,太学生们不容,要皇上处决苏轼!”刘几振臂高呼:“苏轼诬蔑圣上,罪该处死,以正视听!”众太学生齐声应和。
御史台监牢里,地上一只小蚂蚁在推一块饭团,推而不动。苏轼凝神观察。欧阳修疾步走入,苏轼急忙起身施礼:“恩师,您来了。”欧阳修着急地说:“唉,子瞻,怎么样,没有受苦吧?”苏轼回答:“恩师,苏轼无事。”欧阳修说:“唉,你也太冒失了,何必如此呢?文风改革还未告成,太学者正环伺左右,此时最忌急于求成。他们一旦抓住这个机会,就会置你于死地。”苏轼却坦然地说:“恩师,学生若能以一己之躯,促成文风改革之变,倒也死得其所。”欧阳修眼眶湿润了,动情地说:“子瞻啊,你若有个不测,老夫如何向你父亲,向天下读书人交代呀!你放心,老夫当会据理力争,尽力保你出来的。唉,可是这次终究不像上次啊!”苏轼躬身施礼说:“无论如何,苏轼都终身铭记恩师的大德!”
汴河酒楼,夜色沉沉,餐桌上空无一物。曾巩、章惇等人都没有胃口,曾巩叹道:“皇上连欧阳恩师都不见,子瞻兄这次恐怕难逃大劫了。”章惇说:“苏轼实乃我等进士中的楷模!试问我等之中,有谁敢像他这般正言直谏,不计个人得失,而以国家社稷为己任!我等须再为子瞻写道奏章,劝说皇上。”张璪却颇不以为然:“皇上连欧阳恩师都不见,更别说我等了。唉,这个苏子瞻,太过惹是生非,矫饰虚名,连我等功名都陪他一块葬送了。”章惇生气地说:“邃明,子瞻连命都快丢了,你还在这儿计较功名。”张璪低头不语,曾巩等人沉着脸,焦急而无奈。
迩英殿外,范镇欲举步入殿,被张茂则拦住。张茂则说:“范公,别进去了。”说着指指里面,“皇上从来没发过这么大脾气,摔了许多东西,谁也劝不了。我劝你还是别进去为好。”范镇想一想,又待硬闯,还是被张茂则拦住。范镇说:“张公公,那你跟我说,皇上究竟要对苏轼如何?”张茂则沉吟良久,说:“要么杀,要么不杀。”范镇急了,“你……你这不是废话嘛!”
深夜,仁宗于龙床上酣睡,鼾声大作,睡得十分香甜。
御史台监牢内,苏洵、苏辙与苏轼隔着牢中栅栏相对而坐。苏轼明显消瘦憔悴了许多,但仍精神饱满。苏洵和苏辙神色悲怆,不知该说些什么好。苏轼平静地对他们说:“父亲,子由,我听衙役说,百官已联名上书皇上,要问我的死罪,太学生们也在御街示威。”苏辙不答,苏洵却忽然豪气冲天地说:“轼儿,莫忘了你立下的鸿鹄之志。你跟为父不一样,你是干大事的人,就要经得起大风浪。轼儿,你若死了,老夫也为有你这个儿子而感到荣耀,老夫要在汴京亲自为你送葬!”苏轼激动地叫了一声“父亲”,父子俩的手隔着栅栏紧紧相握。
范镇府上,范镇和欧阳修正在对弈。范镇拿着棋子默默地思考,却久久不落子。忽然,范镇将棋子丢在棋盘内,棋盘大乱。他站起来,生气地说:“唉,不下了,不下了。永叔,你说下棋能静心,对老夫却一点用也没有,现在心头仍是一团乱麻。皇上就是不见你我二人,我等又能怎么办?满肚子的话都无处说去。”欧阳修仍坐着,也十分忧虑地叹道:“树欲静而风不止,难呀!只怕因为此事导致文风改革失败,我等前功尽弃。我是上愧对皇上,下有负新进们呀。”范镇吼道:“你说,皇上到底什么意思?杀就杀,不杀就不杀,干脆说个痛快话,为何要避而不见呢?”
这时,房外一声长吟,远远传来:“我欲寻你无躲处,你觅我时无处寻。”范镇听到吟声,知道是老乡吴复古来了,忽然一拍脑袋,惊喜地对欧阳修说:“高人来了,高人来了,子瞻有救了。”范镇赶紧向外迎去,尚未出房门,吴复古一身道袍,手执拂尘,在院子中悠然现身。范镇急忙施礼道:“吴道长,想煞我也,快里面请。”吴复古也不答礼,直向房中走去。范镇对吴复古说:“吴道长,这是欧阳修大人。”吴复古对欧阳修倒是蛮有礼数,客气地说:“欧阳大人,久闻盛名,贫道有礼了。”欧阳修起身施礼道:“道长多礼了。”吴复古悠然坐下。范镇忍不住地问道:“道长是闲云野鹤,从不轻涉俗世,猝然来访,不知有何见教?”
吴复古微微一笑,也不说话,从袖中掏出一只小木盒,轻轻放在桌上。范镇和欧阳修将目光集中于木盒之上。吴复古转眼飘然而去。范镇转眼不见了吴复古,往外一看,只看见了院子中吴复古的背影,急忙喊道:“吴道长,请留步--”只听远远传来吴复古的声音:“送得宝盒金銮殿,抵得二公千万言。”二人看看桌上的木盒,木盒显得古朴而神秘。二人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
颐心殿中,仁宗手拿木盒,缓缓打开,内有一张纸,仁宗展纸阅览,小声读道:“群雀聒噪尘嚣上,风来谁可负青天。圣君当朝士有语,戒碑犹立岂无言。”
仁宗一惊,对张茂则道:“‘戒碑犹立岂无言?’张茂则,当日朕登基之时,独自入密殿读戒碑立誓,戒碑上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此句当是讲的这个意思。”看着张茂则迷惘的神情,仁宗十分纳闷地自言自语:“可是奇怪啊,戒碑上的话,别人都不知道啊。为何……为何……难道世上真有神仙?”
这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子孙立下的戒碑,新皇登基时,可一个人前往拜谒发誓,遵守戒碑上的规定。据说戒碑说的是不杀上书言事的士大夫,柴家子孙即使犯了大逆之罪也不得弃市等。当时就有这样的传说,直到后来金人破了东京汴梁,才真的发现了这个戒碑。内侍张茂则在一旁,讪讪地说:“陛下,微臣鲁钝,不知道。”仁宗好像忽然顿悟,微笑道:“时机已到。好,张茂则,宣旨下去,明日朕要上朝。”
第二天,崇政殿内,仁宗高坐,韩琦、欧阳修、范镇、王珪、胡宿、吕诲等人分班左右。仁宗装病,以手支颐,以热手巾敷住额头,说:“这几日来,朕称病未朝,众卿的奏章都快堆满朕的御书房了。今日朕精神略有转安,众卿对新科进士苏轼的殿试策论有何看法,都据实说来吧。”韩琦道:“陛下,万请保重龙体。至于苏轼,评官以为苏轼专攻人主,为大不敬!”欧阳修缓步出班,慷慨奏道:“陛下,臣有话要讲。”仁宗佯装咳嗽了一声,有气无力地说:“准。”
欧阳修说:“谢陛下。微臣不敢苟同韩琦之论。臣以为,苏轼制策,指正朝廷得失,无所顾虑,持论至公。虽语涉皇上,实乃是循天地之正道,遵人臣之大礼,为国朝以来第一人,应列入殿试的最高等。”胡宿环视周围,出班奏道:“陛下,苏轼在制策中,抨击陛下,狂妄至极,闻所未闻,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仁宗说:“嗯,继续讲。”胡宿说:“陛下,似这等举子,当治大不敬之罪,必当严惩!”
崇政殿中,大臣们继续辩论。范镇说:“陛下,胡宿之言谬矣!苏轼直言朝政,乃我朝之幸也!有善纳直言之君,才有直言之臣。过去唐太宗善纳直言,才有贞观之治;我主乃善纳直言之君,才有而今祥和之气。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包拯弹劾外戚张尧佐,朝堂之上,吐沫乱飞,竟至我主龙面。但陛下仍能听谏言,维持正义,接纳弹劾,成为美谈。微臣以为,苏轼虽有激切之言,但出于忠君爱民之心,并无私意,岂能杀之,请陛下明察。”吕诲反驳说:“陛下,苏轼目无人主,当杀。”多数大臣跪于地下齐呼:“陛下,苏轼当杀!”只有欧阳修和范镇站着。
欧阳修高声道:“陛下,不可!制策求直言,而直言者被杀,此为失信天下之举,参政之言不可取。”很多大臣愤怒地看着欧阳修。
仁宗调整了姿势,慢慢坐起来,说:“众卿,朕若不杀苏轼,又当如何?”王珪一愣,警觉起来,立即调整策略,决定静观其变。吕诲跪下说:“陛下,苏轼杀也要杀,不杀也要杀!”众臣听吕诲这么说,有的一愣,有的响应。
仁宗忽然暴起,将热手巾掷于地上,病态全无,声如洪钟:“够了!你等都是朝中大臣,言称孔孟之道,对一个少年进士,岂能说杀就杀!此一来,何谈我朝仁政!苏轼直言了朕几句话,朕就杀他,朕是何等胸怀!岂能叫后人耻笑唾骂!朕虽只见过苏轼两次,但已深知苏轼文章治才、德行操守俱佳。现在国家吏治不振,亟须新锐之才。朕告诉你们,朕不仅不杀他,不黜他,朕还要让他越级受官,让苏轼到翰林学士院供职!”
吕诲等人大惊。吕诲大声道:“陛下,不可。即使状元,初次授官也不过六品、七品,翰林学士乃三品朝官,如何能授给一个榜眼!”胡宿附和:“按照祖制,吕诲所言不差。况且苏轼多有狂悖之语,也不能说德行操守上乘。”殿内气氛越来越紧张。王珪仍不说话。
宰相韩琦忽然说:“若是授苏轼翰林学士,不知陛下是否要将这宰相之位授给状元曾巩!”
仁宗拍案而起:“大胆!开口祖制,闭口章法,只有循规蹈矩,你们才觉得舒心安宁,唯独不见大宋陈陈相因,积弱不振。朕每办一件事你们都要横加阻拦,说得冠冕堂皇,实是满口空话。今天竟然敢当面责问朕,若是曾巩有宰相之才,你当朕不敢授他宰相之位吗?”韩琦急忙跪下:“微臣只是一时着急,微臣失言,微臣知罪!”吕诲等人也急忙跪下。
仁宗厉声喝道:“你一时着急,你为大宋着急了吗?”韩琦一时犹豫:“这--”仁宗说:“朕即位以来,每遇大事,必招群臣共议之,但行之收效甚少,每每适得其反,致使国力日削月弱。朕有时都怕,怕百年之后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众臣慌忙跪倒:“陛下,臣等知罪。”
仁宗怒气未消,斥道:“知罪知罪!你们整天就知道知罪!今天,列祖列宗在上,朕要朝纲独断一回!今日朕要宣布两件事,其一,殿试放榜,名次与礼部试相同,特授苏轼翰林学士之职,殿试制策三等,翰林院拟旨吧!”范镇、欧阳修等跪下,齐声道:“陛下圣明。”
仁宗大手一挥,继续说:“其二,太学体百无一用,国朝文风之坏,多源于此。当下朝廷需要的是干练的治才,太学体中如何出得国家栋梁!从即日起,废黜旧太学,提举新学,昭告天下!”群臣十分惊讶。欧阳修和范镇惊喜万分,而王珪似乎要瘫软在地。
宫外,刘几他们还在振臂高呼:“杀苏轼,杀苏轼!”一大臣悄悄跑出来,向他们招手示意停下。刘几等人见状停止呼喊,莫名其妙地左顾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