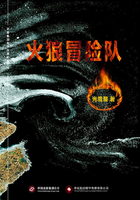我说,多可惜,你应该多上几年学。我日他娘,我在心里想,就是上学又能咋样呢?就像我,我是大学毕业,我现在跟他又有什么区别呢?可我却口是心非像正人君子一样对他说,你应该多上几年学。
黑脸说,俺爹不让。我上到二年级俺爹就不让我上了。那个时候我在家没事儿,就学匪了。
你家是哪里?
黑马。
噢。这使我再次想起他的外号,他的外号叫黑马。我说,黑马是不是离红马还有二十多里路?
是。还有二十五里路。
黑马这个地名我听说过。可当时我没有想到他的外号也叫黑马。我说,黑马也是个镇子,你回去可以做点小生意。
黑马说,没本钱我啥都不说。妈那个×,逼急了我还去偷。
还去偷?那你不是白劳改了几年?
黑马说,劳改算个鸡巴!我看劳改场里也挺有意思,我这已经是三进宫了。妈那个×,下回再进去就不能去陈城了,去新乡。陈城太累,整天在窑场里干,累死人,一天我一个人就得推一百二十车子土。
上哪儿劳改还能由得你?
咋由不得我?只要有钱,有钱送点礼就能干轻活,喂牲口,看个庄稼。可是我没钱,我在劳改场里几年,俺爹一回也没去看过我。
想他们吗?
黑马一听这话就不言语了。刚刚兴奋起来的神色悄悄地消失了。
我说,你结婚了吗?
结了。
有孩子吗?
有。我进去的时候我儿子才三个月,可不到一年,我老婆就给我那拜把子老大去过了。他妈那个×,鳖孙真不讲义气,这回我非剥了他们不中,我知道他们住在哪儿!他恶狠狠地看着我说,可他的目光有些游离,像在自言自语。
这时列车停在一个小站上,熙熙攘攘下车的人中断了我们的谈话,黑脸沉溺在一种愤怒的情绪里。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对话已经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面对他的坦诚,我无言相对,他的丑恶就是丑恶,他没有把丑恶隐藏起来的打算,偷就是偷了,劳改就是劳改了,这次回去就是要去报那夺妻之恨,他已经准备四进宫了。我突然觉得他这人好像天生的就是给监狱给劳改场打交道的,或许,就是他们这些人才养活了国家的执法人员。比起他来,我的内心是多么的肮脏呀,我把我卑微的心理埋得是那样的深,我的内心是多么的卑鄙龌龊,是多么的荒淫无耻。可我的表面又装得是那样的高风亮节那样的坐怀不乱,真的,我比不得他对世人的真诚,可是那个时候我这个虚伪的人还在为他担忧,真是可笑,我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把握我还在为别人担忧,我真他妈的是个混蛋!我把目光移到窗外。窗外是一个正在慢慢移动的陌生的村镇。陌生的村镇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境遇。我突然感到有些茫然无助,面前的一切对我都是那样的遥远,我对眼前的道路一无所知。
我就这样有些痴呆地望着窗外,一直到列车再次启动,我在窗外行走的田野和树木之间听到了寒风呼号的声音。这使我感到在这个世间我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就像一只蚂蚁,或者像一只蚊子,或许连蚂蚁蚊子也不如。蚂蚁在冬天还知道躲进洞穴里休息呢,可是我……我真的感到了疲劳,我看了一眼依在车厢上打盹的卖木刻年画的中年妇女,也依在靠背上慢慢地混沌起来。
我一直昏昏欲睡。在昏睡中我感觉到列车在冬季的平原走走停停,直到最后一次睁开眼才看到我对面坐着的中年妇女和那个黑脸汉子都不见了。我看到那帮歌舞团的演员正在一边喊叫一边从我的身边经过。我朝站在我身边的那个小眼睛大嘴巴的女人问道,这是哪?
红马。
红马?我从她的话语里清醒过来,红马就是我要下车的地方。我站起身来,还好,我看到我的提兜还在行李架上,我把它取下来。这时那个大嘴女人又朝我说,你也下车吗?
我说,下车。
那女人朝我笑了一下,忙闪身给我腾了一个空,我就挤进了下车的人群中。由于拥挤,我的前胸紧紧地靠着她的后背,我的下颔被她的头发划得生痒。这时她弯腰去看什么东西,她宽大的屁股正好顶在我的两腿之间。尽管隔着一个寒冷的冬季,我还是突然产生了一种触电的感觉,我想和她做爱。她这时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从她的呼吸里我闻到了一种冰淇淋的气息。那气味使我想起了马响,想起我已经有二十多天没有碰过女人了。我被这种思想浸泡着一直到走出车厢,扑面而来的寒风才使我清醒过来。除去那幢孤独的高高地立在台阶之上的候车室之外,我看到四周到处涌动着雾气,雾气的出现使我面对的红马失去了本来的面目。置身于雾气之中的红马像一条没有尽头的狭窄的巷子供我行走,我看到在巷子的两侧是一些装载着无数秘密的房屋。
在越来越浓的雾气里,我告别了那座孤独的候车室和一些在雾气里时隐时现的树木沿着单薄的铁轨往前行走,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在铁轨的右侧有一道墙,墙上用朱红色书写着某种商品的广告标语。在一个用破碎的水泥楼板垒起的百孔千疮的厕所前我停下来撒了一泡尿,之后我走进了一条肮脏的街道。人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从前方传来,我抬头看到了一些隐隐约约的身影,有一些面目不清的人开始和我擦肩而过。随后我在街道的两边依次看到了如下一些名词和能使这些名词成立的实物:
几间房屋。几间落了门锁的房屋。
一片只有围墙没有顶盖的建筑。我看到有一个留长发的女人提着裤子从里面走出来,在寒冷的空气里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尿臊气。我立住脚,朝那个女人说,喂。那个女人站住了,她的手刚好离开她的腰间,她的衣服随着垂落下来。
我说,请问,你认识马响吗?
马响?
对,马响。
我不认识。说完她不再理我,径直走进一家小卖部。
一家小卖部。
一家打面粉的机房。一个落满了白色粉粒的屁股对着门口晃动,那屁股的拥有者正在机器边忙活。
一家杂货部。在雾气里我闻到了醋的气味。
一家餐馆。灰白的炊烟从餐馆里冒出来,立刻被雾气所包容。
一家挂了牌子的旅店。旅店里传来了哼哼叽叽唱歌的声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使我再次想起歌舞团里的那个小眼睛大嘴巴的女人。我听到隔壁餐馆里哧哧啦啦的油锅把那歌声摁进去炸得叭叭作响。
一家影剧院。破旧的大门前冷冷落落。
派出所。在过道的墙壁上有一个新置上去的光荣榜。有两个身穿制服的民警走出来,其中一个民警的脸上长着许多粉刺。长一脸粉刺的民警立住朝我看了两眼,而后他们穿过肮脏的街道走到对面的餐馆里去了。
邮电所。这是我在红马看到的惟一的一所墙壁被涂成绿色的房子。
一家理发店。理发店的门前有一台发电机,正在工作的发电机使得理发店里灯火辉煌,明亮的灯光使店里的那几个浓妆的女孩子显得与众不同。
一家投影厅。投影厅的门前挂着一个用棉被做成的帘子,帘子的腰间已经破烂,露出了灰白色的棉花。投影厅前的音箱里发出嗡嗡作响的声音,一个女人正在浪声浪气地对过路的人说,你来呀,你上来呀……它的电源同样来自理发店门前的那台发电机。
一家五官科诊所。
一家医院的大门。由于越来越浓重的雾气,我没法看清医院内部的结构,院子里仿佛一个无底洞,充满了神秘感。我看到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女人在雾气里闪了一下又不见了,如同一个幽灵。
一家小型的商店。
一家卖油条的小铺。
一个卖蒸馍的挑子。
一家卖胡辣汤的小铺。
一个烧饼炉子。
又一个烧饼炉子。
一家卖稀饭糖糕的小铺。
在我看到这些放置在同一道相通的棚子下的小吃时,我感到了饥饿。我突然想起从早起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吃过一口饭。我离开充满泥泞的街道走进棚子里,几张脸一同面向我,异口同声地说,你咋吃?
我看了他们一眼说,来碗稀饭,拾几个糖糕。之后我选了一条凳子坐下来,我对正在给我盛稀饭的女人说,你认识马响吗?
马祥?
马祥的名字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突然从那个女人的嘴里跳出来,使我有些不知所措,我脱口问道,谁?马祥是谁?
马祥就是马祥。
瘦子,他是个瘦子?
是个瘦子。
他也是红马人?
他不是红马人,你说他是哪里人?
我的心惊跳了几下,说,他回来了?
女人说,回来了,几天前我就见他在街上转悠。
突然出现的情况使我有些惊愕。那个女人看着我脸上的一片惊慌,用警惕的目光看着我说,你找马祥?
不是。我说,我找马响。
马响?男的女的?
女的。
噢……
你认识她?
不认识。她对端糖糕过来的男人说,你认识马响吗?女人说完又补充了一句,是个女的。
男人看了我一眼说,她是干啥的?
以前她在这里教过学,她父亲也是老师。
噢……男人说,那你到学校里去问问,前面不远就是一所小学。
我就这样不止一次地向我遇见的人们询问马响,可是他们都说只认识一个名叫马祥的人,几天前他刚从外地回来。在这里,马祥赫赫有名,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有一个名叫马响的女孩子。最后我沿着那条满是雾气的街道来到了一所小学校的门前。小学里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学校里已经放了寒假。我在上了锁的铁门前停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门边的一间小屋。我看到一捆又一捆各种各样的破烂在屋子里堆积着。我侧着身子挤进去,就闻到了一股子霉变的气息。我说,有人吗?
你找谁?
我听到一个嘶哑的声音,起初我没有听出说话人的性别,等我把身子移到屋里,在暗淡的油灯光下我才看到同我说话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女人。我对她说,我找马响。
马响?
是呀。
刚才来的不是你?
刚才也有人来找马响?
才走没多会儿。
找到了吗?
没有。
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同你一样,是个男人。
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
那你认识马响吗?
你说的是不是马泰奎的闺女?
是她,她爹就在这个镇子里教学。
老女人说,白天她不在这儿,晚上才来这里睡觉,学校里有她父亲一间房子。
你知道她家在哪儿住吗?
教堂那一片吧。
教堂?
她家离教堂没多远。前天我出去拾破烂就在教堂那边见过马泰奎。
我结束了与老人的对话,走出她那间充满霉变气息的小房子。我肩挂提包重新站在那对铁门前朝学校里观望,我再次看到一团一团的雾气在我的视线里流动,灰白色的雾气改变了雾气中的房子的颜色。雾气中的房子在我的感觉里是那样地遥远,那样地不真实,仿佛是一些在水中漂动的幻影。就是这个时候,我的手触到了挂包里的刀子。我从挂包里掏出那把刀子,我的拇指一用力,泛着青光的刀子就从刀鞘里跳了出来。在渐渐暗淡下来的天色里,我看了一眼那把刀子,然后合上刀刃又重新把它装回去。我抬头看了一眼暗淡的天色,我想我应该到教堂附近去看看,我想在天黑之前尽快找到马响。
我在雾气四游的大街上一次又一次询问与我擦肩而过的行人,最终找到了教堂。教堂里冷冷清清,但房门却洞开着,通过很深的房洞我看到了一束摇摆不定的烛光。我在教堂的门前踌躇不前,这使我感到意外,在陌生而偏僻的红马竟有这样一个教堂,我深深地感触到了上帝的力量。仿佛有一只神灵之手在烛光那里召唤我,我身不由己穿过一排又一排简单的座椅和头顶上一条又一条挂满了三角形的不同颜色的纸旗,来到了烛光前。在烛光的后面我看到了受难的耶稣。痛苦流溢出主的肉体和面容在摇曳的烛光里四处碰撞,这使我感触到了真切的苦难在时间里的飞翔。面对痛苦我感到了恐惧,我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我的孩子,你向天主忏悔,寻求他的宽恕吧。
在我的身后,突然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我转过身来,看到在我的身后站着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近我的,他仿佛上帝派来的无所不晓的智者。面对智者我无从言语。
老人说,忏悔吧,我的孩子,你现在来到这里,一定是想对天主说出你的心里话。
我说,我没有想到这里会有一座教堂。
上帝无处不在。我的孩子,你想寻求天主的帮助?
我说,我要找一个人。
只要他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一定会找到他。
她就在这个镇子里。
请说出他的名字,看天主能否帮助你?
她叫马响。
马祥?我的上帝,请宽恕这些罪恶的灵魂吧。
不,不是马祥,是马响,她是个女的。
春天就要来了,我的孩子,鲜花总是伴随着女人,去吧,你会见到她的,她就在前方等待着你的到来。
在摇动的烛光里我离开了教堂,无处不在的雾气重新把我吞没。在前面的雾气里亮着一盏又一盏毛茸茸的光团,黑夜在雾气之中又一次降临。这时,在不远处突然传来了鞭炮声,突然响起的鞭炮声使得腊月的夜晚是那样的空旷。好象是受到了感染,当第一鞭爆竹响起之后,接连不断的炮竹声便四处响起。接连不断的爆竹声让我忘记了行走的目的,我为此感到迷惑。我叫住一个从对面走过来的男人说,为啥乱放炮?
那个男人很认真地在灰暗的灯光里看着我说,你忘记了今天是啥日子?
啥日子?
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日子。
哦,要过年了。
是的,要过年了。
这使我备感孤独。我说,这附近有旅店吗?
你一直往前走,在派出所对面,有一家旅店。那个人说完,便沿着街道匆匆而去。
按照陌生男人的指点,我来到了那家旅店。这是我曾经路过的那家旅店,在旅店对面的影剧院门前亮着一盏明亮的电灯,在那里我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他们是我在小火车上见过的歌舞团的人。剧院房顶上的喇叭里,有一个奶声奶气的女人正在预告今天上演的节目,她的声音同雾气一样在镇子里四处传荡,向红马人宣告着歌舞团的到来。许多青年男女开始在雾气的灯光里晃动。我穿过他们横在空中雾气里的身影,径直地走进旅店。一个大胡子正坐在门边的桌子前写着什么,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来看着我说,住店吗?
我说,有房间吗?
有。说着他把一个本子调过来放在我的面前,把你的身份证填一下。他看我在兜里摸来摸去,又接着说,得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可不行,派出所里每天都来查夜。
我有身份证。我说,我有。我终于在皮夹克里面的一个兜子里找到了身份证,我把身份证放在桌子上对他说,你帮我填吧,我冷。
大胡子拿起身份证看着在本子上写了一阵,然后抬头看着我说,住楼上吧,楼上清静。
我说中,住哪儿都中。
大胡子把身份证还给我说,住几天?
先住一天吧。
现在结账还是明天结账?
我想了一下说,明天吧。
你上去吧,204房间,里面已经住了一个人。
等我离开桌子,大街对面喧闹的声音又陡地一下涌进我的听觉里。我回头朝那里看一眼,满街里都是被灯光照亮的雾气。在暗红色的雾气里,我看到那个在小火车上卖门画的中年妇女走过来,她对大胡子说,大哥,你就让我住下吧,天这么冷。
不中不中。大胡子连声说道,没有身份证不中。男的还好说,你一个女人家,不是不让你住,要是派出所半夜里来查店,我吃不了兜着走。
我就住一夜。女人哀求的声音从潮湿的空气里传过来,听上去有些打颤。
大胡子说,你去教堂迁就一夜吧,那里有椅子,还有煤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