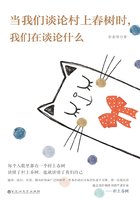文学巨人评述以此庆祝冰心先生创作七十周年
回首度过的岁月,有过欢愉,也曾蒙受厄难,但多半是平淡的。生活的路曲折坎坷,当然也有迷惘。我庆幸,文学于我爱抚有加:于肷道人心信念的不曾泯灭,茫茫风雪中总怀有冀企,这多半受惠于文学的启迪。
文学诚然脆弱,而未必无用文学可以丰富,却未必万有;在严酷的寸代,文学又往往是悲剧的。但文学铸造人的灵魂,在铸造尺的灵魂这一奇妙工程中,文学默默地生发着它的伟力,它把人导向崇高与丰富。
友朋聚坐、偶语往昔,我总怀着感激谈起少年时代成为挚友与良师的两本书:巴金的《家》,冰心的《寄小读者》。(在那样的年龄,虽知待迅,却不能理解他的睿智与辛辣。)两本书中,前荇给我热情,后者给我温暧;前者教我抗争,后荇启我爱心。生爱书,年龄渐长,所爱日多,但始终如星光辉耀着人生之旅、讦成为血般的热情涌流于心间的,大抵还是这两本书渊厚的人也许会因而笑我,但我都以未曾忘却而慰。也许如人们的不忘自己的童年,人们也轻易不忘童年的友与师。我甚至窃喜,就是这样两本平常的文学作品,却深刻地引导我走上人生的追求之旅。
最早接触《寄小读者》,已是近半个世纪前的事。记得当日,童稚的心灵中,宛若吹迸了一阵清婉的风。太平洋舟中斜阳映出的波光,慰冰湖四围的秋叶,深山万静之中、病榻旁的友情与乡思,凝聚于大自然绮丽景色中的万种柔情。它们第一次开启广童年的梦境一一文学康来竟有这般奇能,它揭示和再现世间万物的奥秘,它昭告人们,世界有着难以曲尽的美丽与丰富。
冰心的文笔十分优美,她源自中国文学的深厚与蕴藉,又融进她自有的清丽和婉转。中国文化传统的沉积和生发,加七西方文化的融汇,使冰心成为中国最有素养的一代学者和作家。她的丰富和创造性未必都能为她的小读者所领会。但是,洋溢在着作中的那神高雅的情调,那种纯净的心境,也已征眼了万千童稚心灵。
作为当时的一位少年读者,我始终未能忘怀的是流动于一封封通汛中的那股友情和母爱的温流。她把女儿对于母亲的爱恋写得委婉缠绵,这是一种绵延古的永恒之爱。但她昭示于小读者的,原不只母爱一端,她有着客居异地病中静中搅得心绪不宁的家山乡国之恋。由此推开去,她同情于一切弱者的病痛与哀愁。
在沙穰,冰心当因病休养的所在,她为许多异国女儿的病苦煎心。她由一隅推而远之:“撖界上的幼弱病苦,又岂止沙穣一隅?小朋友,你们看见的、也许比我还多。扶持慰藉,是谁的责任?见此而不动心呵,空负了上天赋予我们的一腔热烈的爱!”冰心的爱不仅无限,而且博大。默默地诵读,潜心地领会,久而久之,这位女作家的一片冰心,溶入了幼小的血脉而奔涌。从此,我确认那一片爱抚之心已成了生命不可割离的一部分。
少有间隙的战争的烽烟里,我告别了少年时代。我带着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巴金与冰心的作品所给予的心灵的陶冶,跨进丫一个陌生而又为当时所倾心的社会的门槛。教科书告诉我最初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告诫我务必割断与“永恒的”和“抽象的”爱的联系。矛盾和痛苦纠结在“思想改造”的漫长历程中。一个无庸讳言的节实是,冰心的作品,包括《寄小读者》,自那时起受到肆虐。一些论者揶揄她的情趣与观念,甚而亵渎她对母亲和大海的爱。
但冰心给予我的,都深深坦藏于活泼的生命中,而不论外界有何等严重的磨折与威逼。人的感情世界十分奇特。就在那些失去理智的年月,当人们陷入普遍的敌意与仇杀之中,尤其当自己陷入困境、蒙受侮辱的时候,都益发思念冰心曾经给予我的柔情与慰抚。在那些混乱而变态的年代,当自己身心受到摧残,而周围是一片可怕的荒芜和孤寂,我几乎是以非常宁静和优美的心情,沉醉在冰心作品的无限丰富的回想之中。
那是一个静闲的舂夜,灯前桌下,一一只小鼠蹒跚步履外出觅食。作者因为好奇用书很容易地盖住了它,不幸为同样好奇的小狗所突然捕杀。冰心为这一“灵魂的隐痛”而在刚刚开始的《寄小读者》中作真诚的忏悔。冰心在信中叙述说,她当时因内心的不安而向一位成年人陈述过,回报她的却是冷漠和嘲讽。她只能转而寻求严正而纯洁的幼小心灵的“裁判”。
这是我在那样失去人性的疯狂岁月中自然想起的。我很难说清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想起了书中的那片挚情,是由于追念失去的人性?是由于感同身受而抗议残忍?还是由于对真诚忏悔的感念?但如下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我不能不在内心深处萌发起人类慈爱之心的渴念!
童年所经历的一切真是历久不忘的。以至到了如今,我还为园内沼泽中那只孤鸣水鸟的被猎杀而激愤,还为玉渊潭中天鹅的惨祸而无言。我依然感激冰心,是她的作品给了我足以使那些麻木心灵发出轻蔑笑声的人类的良知。当我面对愚昧、卑琐和暴虐,我总想起《寄小读者》,我慨叹那纯净的一切变得如此的遥远!但我确认它的优秀与高尚,对于那些沉沦和陷落,它也许竟是一声警号!
我现在就住在冰心青年时代生活过的环境中。潋滟湖光,俊丽塔影,每有动地歌呼发自亭阁花丛之间。这里的脉搏震颤着国人的心弦,这里的思考充满了深沉的忧患。岁月流逝,人事已非可幸周围依约还是冰心当年所见情景。
遥想当年,她海外学成归国,以青年教授执教于斯。课余推婴儿车款步柳岸,裙裾飘影于湖中,是何等的风采飞扬!而现在,当年的花树已稀,湖畔的伦敦式街灯毁没往年,我家门前的十里稻荷、彻夜蚌鸣。已随繁盛的畅春园一起被碎砖碎瓦和造型丑陋的建筑物所吞噬。即使是在旧日宫苑苇塘的死水中作最后凭吊的一二野鸭,也从世上永远地消失了。
经历了无尽劫难和猝变的人生,理应豁达、超然而从容,而私心仍不免牵会于区区。这究竟是否应当归咎于文学的滋养与教诲?如今。我只能向冥冥中的主宰默祷与祈求。而我庆幸终于还能痛苦,还能坚持,我感激文学惠予的启蒙,感激我童年的挚友和良师一一一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撤种,随时开花,将这一迳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