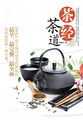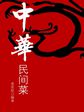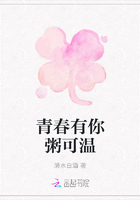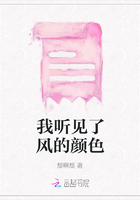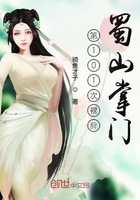后来果然找到出差的机会,去了几趟杭州,发现大街小巷,尤其旅游景点,茶室星罗棋布。其中不乏老字号。挽弓当挽强,我喜欢直奔龙井寺,先看看至清至洁犹如大彻大悟的龙井潭(等于洗洗混混的眼睛),随便嗅嗅附近双峰大队茶场飘过来的茶香,然后走进古寺中庭的那间早已改作茶室的佛殿,点一壶新茶,也算给自己圆一个梦。据作家韩少华讲述,他有一年雪后来此,寺内只有他一位茶客,茶室阿嫂递上一壶茶,说“难得好兴兴,就尝尝梅家坞的吧。”一尝,果然不同凡响。下山在茅家埠头搭船,蒙同舱一位老者相告,说龙井寺偶尔拿出的梅家坞茶,是连杭州人也难得尝到的;梅家坞处于老龙泓山麓的阳坡,此地所产龙井茶在古籍里被奉为南山绝品。这使他又惊又喜。
我也风尘仆仆地来到龙井寺,可惜却没有他的运气。这倒无妨。正好让我对那种“绝品”龙井保持充沛的想像。不能算作白来。世间能中大彩的,又有几人?
估计杭州的茶室多,跟寺庙多(极盛时约有两千多所)也不无关系。烧香拜佛,走累了,总想找个地方坐坐,喝杯茶。寺庙里或周围的茶座,叫茶馆肯定不合适,叫茶室则很相称,多多少少有一份出世的禅意。茶室就名称而言,应该很安静的。心安是福。
李叔同来杭州,爱上了这清茶淡水的安静,割断尘缘,成为弘一法师。他写过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讲述自己民国元年七月来杭州,住在钱塘门内,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去西湖边的一所小茶馆景春园吃茶:“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看。”
他还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有一回跟夏丐尊居士两人去湖心亭上吃茶,当时夏丐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作和尚倒是很好的!”李叔同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认为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近因则是由于搬到虎跑寺居住,羡慕并喜欢上那些有道德的出家人的生活。直至去灵隐寺受戒。茶和禅,在李叔同身上,表现出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杭州的茶室,更容易接近那份超凡脱俗的禅意。尤其看着三潭印月、听着南屏晚钟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身心正在变得透明……
杭州茶室旧景,很值得玩味。听老人言:游西湖者“有到码头上吃碗茶去”之口号,即以三雅园茶居为目的地,凡游人步入三雅园之木架门楣中,即觉耳根心境一清。“三雅园在湖堤尽处,外堂三楹,内堂古朴,开轩则全湖在目,南山屏列几案间。最爱其轩前小角,有垂柳大可合抱,此间容茶桌一,吸光饮渌,绝饶佳处。学士大夫,均集于三雅园内堂,间亦有闺秀名媛,由湖船起岸,在此品茗者。壁间悬楹帖一,犹忆其句云:为公忙,为私忙,忙里偷闲,吃碗茶去;求名苦,求利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陈栩语)杭州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似乎全写在这副对联里了。只是后来,三雅园茶居完全消失,昔日建筑已沦为某人之别墅。怀旧者想喝那忙里偷闲的茶,换别的地方去吧。
好在杭州的茶室,多得数不清,足够你挑三捡四,换来换去。人,就在这逛来逛去中累了,在这晃来晃去中老了。
鱼与茶叶
我想有两样东西是最需要水的,一是鱼,一是茶叶。鱼长着鳃,靠水来呼吸。鱼与水的关系,是最经典的情谊。其实茶叶也是如此。茶叶的魅力,同样需要通过水来体现。当滚烫的开水浸泡着茶叶,它就像鱼一样活过来,恢复了知觉,扭摆腰肢。或者更夸张地说:像睡美人一样醒过来,随波逐流,载歌载舞。是的,只有水才能将其唤醒。它生来就是为了等候那销魂的一吻。为此不惜忍耐长久的煎熬与饥渴。我们喝茶水是为了止渴,可却很少想到:茶叶比我们更渴,更期待与水的结合--哪怕这注定是一次性的。
茶叶在水面仰泳够了,纷纷潜水艇一样下沉到杯底。这时候它显得比水更重。水要再想拥抱它,会很吃力。哦,这一具具光荣的尸体,模糊而又清晰,躺在水做的床上。我联想起海子的诗篇:“我怀抱妻子,就像水儿抱鱼。而鱼是哑女人,睡在河水下面,常常在做梦中,独自一人死去。水将合拢,爱我的妻子,小雨后失踪。没有人明白她水上是妻子水下是鱼,抑或水上是鱼水下是妻子……”
至于茶叶,亦将死于与水的婚姻,可它却流露出任何溺水者不可能有的幸福的表情。当我们把失去了滋味的茶叶打捞上岸,丢弃在垃圾桶里,它的梦也就搁浅了。那是多么短暂而又灿烂的梦哟:茶叶在水中可模仿花朵的开放,体会到发育的快乐……
现代人饮茶,偏爱透明的玻璃杯,这样可以兼而获得视觉上的享受:观赏茶叶在水中的沉浮与动静。玻璃的茶杯,是我掌心微型的水族馆,游动在我眼前的是一条条绿色的小鱼。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狂欢的鱼群完全忽略了观众的存在,是不会受惊的。它们拥有的水域,散发着爱情的味道,青春的味道,梦的味道。
鱼与茶叶,原本没什么关系。是我的想象力使它们无限地靠拢了。鱼是江湖河海里的茶叶(钓鱼类似于茶道,同样能修养性情)。茶叶呢,是杯中的鱼,是沸水中的“热带鱼”。鱼与茶叶,都有着杂技演员一样灵活的腰,能够做出任何高难动作。惟一的区别在于:鱼在水中是要觅食的,而茶叶则是为了彻底地奉献。
当池塘里有鱼活动,就不再是死水了。
同样,当杯中泡了茶叶,水也就活了。水会伴随茶叶一起,做一次深呼吸……
水确实很软。可鱼与茶叶,都是水的骨头。
李白的酒量
无人会怀疑李白的酒量。在唐朝的诗人中,李白的酒量跟他的诗一样,是算第一的。但李白究竟能喝多少酒,这倒是个谜。
在这方面,他自己最爱“吹牛”的,经常夸耀:“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以及“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此乃酒后狂言,不可全信。只是他饮到高兴处,一杯接一杯停不下来,倒是真的。他的名言就是“将进酒,杯莫停”。并且很讲究喝酒的气氛:“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数到最后,恐怕连自己也数不清了。没钱买单,就脱下皮大衣(“千金裘”),连同自己的坐骑(“五花马”)一起送进当铺里。真够不要命的。在李白眼中,酒绝对是世界上顶好的东西。他已非低斟浅酌的酒徒,而近似于孤注一掷的赌徒了,把生命中所有的宝都押在酒上面。甚至连吟诗,都相当于猜拳喝令,添一碟精神上的下酒菜而已,解酒或醒酒用的。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以斗来计算李白的酒量:“李白一斗诗百篇”。这同样运用了夸张的手法。酒是李白写诗的成本。产生的利润也颇为可观。唐朝若有稿费的话,李白会成富翁的。只是他这样的人,即使拿到稿费,也会悉数用来换酒喝,不可能存在银行里吃利息。或者说,酒馆就是他最信得过的银行了。他原是应邀为杨贵妃写过赞美诗,所以离开长安的时候,唐玄宗赏给他一大笔钱(“赐金放还”)。估计没多久就花完了,全用来“赞助”大唐帝国的酿酒业了。酒肉穿肠过,诗篇却留下来了。其实挺值的:在唐朝,诗歌也算得上是“硬通货”。
李白好喝,但我估计他的酒量倒不见得真的能大到惊人(或“超人”)的程度。他经常醉得一塌糊涂。在长安街上的酒馆里酣睡,之所以拒绝天子的召唤,是因为头重脚轻,实在走不动路了。甚至还可能神志不清,已忘掉了天子是何物。管他那么多呢!
这是一种属于醉汉的勇气。据说有一次,唐玄宗在大明宫设宴招待李白,并亲自为诗人调羹,李白又喝多了,过量了,居然抑制不住地在金銮殿上呕吐了,把阶前舞女的裙裾弄脏。幸好唐玄宗并没有怪罪李白的失态,还命令高力士为醉话连篇的诗人脱靴子,搀扶其去休息。这倒是一位很清醒、很明智的皇帝,能包容诗人的狂放不羁。也难怪唐朝是诗歌最繁荣的时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唐诗确实为中国的酒文化锦上添花,而李白堪称其永恒的“形象代言人”。
纵观古今,再也找不到比李白文化程度更高、知名度更大的酒徒了。他的相当一部分诗篇,都算得上是无偿为酒商们撰写的“广告词”,譬如“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譬如“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譬如“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呀什么的。
诗与酒,从此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里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通过李白的诗篇而获得最密切的联系。李白是个幸运儿,靠喝酒、吟诗而成为英雄,成为“半神”(诗仙及酒仙)的形象,令后人仰慕不已。真是行行出状元啊。
正因为此,我想李白的酒量也被传说给无限地夸大了。毕竟,这也是树立榜样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往榜样脸上贴金是人之常情。并且,还“为尊者讳”--很少有谁相信李白喝醉了也会吐,甚至还曾令大明宫里的舞女们举袖掩鼻。这多丢诗人的脸呀!“此情节最好删去”。因而我们心目中的李白,永远仰天大笑、举杯豪饮,飘飘欲仙的样子。
李白出生于北方以北的碎叶城(今俄罗斯境内),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善饮是无疑的。但是否真能算得上“海量”,能像喝白开水一样喝酒,倒未必。至少,在杜甫所例举的“饮中八仙”里,李白的酒量比汝阳王李和一个叫焦遂的平民要稍逊一筹。“汝阳王斗如朝天,道逢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这汝阳王久仰酒泉(今属甘肃)之美名,连搬家去那里的心都有。至于焦大哥更厉害,必须喝满五斗后才进入状态:“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而李白,只喝一斗就摇身变成“写诗机器”了。李白比其他人占便宜的地方,是诗写得好,有煽动性。在唐朝,诗写得好就能成为大明星。更何况其酒量毕竟也进入了“排行榜”。如虎添翼。
读《饮中八仙歌》,我感叹于唐人饮酒皆以斗数来衡量。虽然说“海水不可斗量”,可这斗里毕竟盛的是酒呀。莫非现代人的酒量早已退化了?碰杯时尽用的是几钱装的小酒盅。后来去西安,我亲口品尝到当地土特产的稠酒,方知李白的时代饮用的皆是这种粗糙、浑朴、未经再加工的米酒,而非后世才诞生的高粱、大麦等谷物经蒸馏酿制的老白干(俗称烧酒)。
李白若是喝上一斗二锅头,非酒精中毒不可,哪里会有写诗的灵感呀。但我又替李白遗憾了:他出生得太早了,没有福气接触到茅台、五粮液;否则,还不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有一点是肯定的:若有茅台、五粮液陪伴,李白对生活的牢骚会少一些。
李白生前,虽然不乏“吴姬压酒劝客尝”的聚饮时光,但也经常一个人低头喝闷酒。“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只好跟明月碰杯,邀影子共舞,凑合成“三人行”。李白其实是很孤独的。在他的诗中出现得最多的,除了酒之外,就是同样寂寞的月亮:“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我寄愁心予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的一生,既洋溢着酒的气息,又散发出愁的滋味;他借酒来浇心中之块垒。有什么办法呢,酒是他忧愁时惟一的解药。他视酒为精神上的救星。不管其酒量有多大,他对酒的这份深情,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这也是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的原因。
李白非溜须拍马之辈,很少为达官贵人赋诗献媚,但他却爱屋及乌,因一位姓纪的酿酒师病逝而放声大哭。他写了一首叫《哭宣城善酿纪叟》的五绝:“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纪老头真有福气,得到了一位大诗人如此的赞美。
李白死了。我们不用替他担心。他在地狱里照样会有酒喝的。
李白是我们民族的“酒司令”,是诗坛的“祭酒”(或称“祭司”)。他仿佛为酒而生的。他确实也是因酒而死的。公元762年,李白在高高的采石矶(今属安徽)饮酒过度,醉醺醺地伸手去捞天上的月亮,结果落水溺死。对于苦难的诗人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安乐死”。瞧,这就是李白:连死都充满了诗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位诗人能这么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