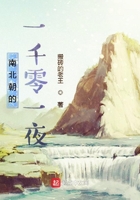我满嘴黏唧唧的糍粑,口齿不清地说:“看在吃的份儿上,等一下带你们去个好地方。”
阿奎高声大笑:“就知道你要乱走。”
宏平向来比较乖,他不安地说:“老师不是说要跟牢大部队吗?”
我说:“跟着我,怕什么。”
到了山口的河谷,带队的老师们按班级集合学生,分头重申注意事项。雨季消退,河谷里的大石头耸立如雕像,又白又干燥,只在底部流淌着清澈的小溪。我看过八月暴怒的激流,山洪裹挟着红色泥沙咆哮而过,石头们在水底一声不吭地忍耐着,连头也不冒。在这样明媚干爽的天气看来,过去的无数个雨季如同荒诞潮湿的噩梦。
我不耐烦地听老师训话,嘴里咬着一根剥开的铁线草心。草心带着淡淡的甜味,还有股草味儿。再往里走就不长这种草,山隘间有各种拖着长叶子的蕨类,高一点的坡地上长满灌木,缀着红黄纷呈的浆果。野蜂被甜味吸引过来,嗡嗡飞舞。我完全可以想象同伴们看到这一切时的快活劲儿。
更好看的还在后头,我敢保证。
注意事项终于说完了,我一改刚才的步调,噌噌地踩着河床里的石头往前走。小六在后面喊:“大头,河边有路嘛,上去吧,走这个多费劲。”
我头也不回:“有路你去走啊。待会跟不上我不管。”
男孩们哪里受得了激将法,纷纷紧跟上来。何琴在我旁边,步伐稳当。
我带他们走的方向和老师指定的路线南辕北辙。河谷向右侧弯入山区的时候,我放弃了这条不成路的路,朝左边耸入天空的崖壁进发。
悬崖像一堵和地面呈九十度的高墙,努力仰头也看不到顶。上面密密地生着马尾松,随处可以手攀脚踩,所以不难爬。我迅速地爬上去一大截,宏平在下面喊,说他还是随大伙儿走。小六也跟着他往另一边去。
两个没用的家伙。我不理会他们,继续奋力往上。现在剩了四个人。我,何琴,阿奎,海椒。其实本来有条好走的路,但那是个秘密,我不想说。
我爬到半山的台地,坐在地上喘着气等另外三个人。海椒最慢。
直到看见他的上半身从树枝间冒出来,我才想起我的包在他身上,背两个包估计很碍事。
我吐吐舌头,向他伸手要包。他直摆手。我笑着说,马上要用呢,你占着它做什么。
从这块台地出发,有条横绕山腰的小路,比肩膀宽不了多少。以前只是条路的轮廓,如今露着寸草不生的红土,清晰地盘在山间。大概是进山挖兰花的人踩出来的。马尾松密密地铺满路面以外的每一处崖壁,它们的手臂从我们的头顶、脚底和四周旁逸斜出,感觉就像站在松枝围成的洞穴里,浓烈的松树味刺激着鼻腔。我从包里拿出整捆绳子搭在肩上,他们三个跟随我循着路走。我不时停下,试图确认太阳的位置。然而草木成了天然的阻隔,无奈,我转头问海椒有没有指南针。他在班里是有名的科学少年。
科学少年的名声不虚,他随身带了指南针。但我们立即发现指南针坏了,针尖犹豫地转朝一个方向,又指向另一个。
何琴问:“我们要去哪边?”
“西南。”我毫不迟疑地说。
“再走会儿。”她说。
“你确定?”发问的是阿奎。
她点头,“那条河自西向东,我们在底下是朝正西走。然后我们往左手方向上的山,所以是南边。如果去西南,就要再绕半圈。”
我们三个一致对她的方向感表示钦佩,继续绕山,不时拨开挡在脸前的树枝。
“差不多了。”还是何琴率先断定。
我心里不太有谱,但这时只能死扛。我四下看了看,找了根粗壮的树干,把绳子往上面缠了几圈,打了个死结。
“要下去?”阿奎惊问。我在他脸上看到一抹动摇的神色。海椒何琴都没吭声。
我点头。嘴唇上方的旧伤疤倏然腾起火辣辣的刺痛。每当我惊慌、愤怒、心神不定,这道疤就会乍然苏醒,昭示它的存在。不知这会儿该算哪种情绪。
海椒开口说:“我先下吧。”
“只有我去过,当然我先,”我想想又说,“你们要是不想走,就回去吧。”
阿奎笑一声:“爬上来容易,爬下去难哟。还不如跟着你。对了,我们待会儿不至于还要从那底下爬上来吧?”
我勉强冲他一笑,“你都说了,爬上来容易。”
按照我的计划,我们只要以绳子作为辅助,从另一面山崖慢慢下到谷底,就将目睹无数奇花异草。大多是草药。这片被山崖团团围住的谷底少有人来,保持了繁茂的植被。想想看吧,从谷底往上看,头顶是蓝天白云,四面环山,外面的世界被隔绝了,没有农田,更没有人家,有的只是满眼的花草,偶尔能看见野兔,不知名的鸟在远处叫那么一两声,还有甲虫或蝴蝶悄然飞过。
学过《桃花源记》后,这地方总让我想起那篇课文。其中的静谧有如甘美的诱惑,让人想长久停留在无人的空谷。
最早带我来这里的是爸。他没明说,我总疑心他是在这里捡到我的。
要等年纪更长我才会想到,有谁会把婴儿扔在这么个荒僻的山谷?初中时代的我缺乏现实的逻辑,只一相情愿地用自己的名字把这片无人的仙境命名为“妙谷”。
事后回想,那天可能一开始就没走对方向。何琴的判断毕竟还是失了准。
不过已无从验证。我们甚至没能顺利下完一半的山崖路。我脚下的松枝不够结实,发出清脆的断裂声。本来,如果我抓紧绳子也就没事了,偏巧我正松开绳子,把手心的汗抹在衣襟上。
我的惊叫声和松枝的脆响几乎不分先后。我感到身体猛然下坠,条件反射地闭上眼。整个人一片空白。周围的松枝刷啦啦地划过我的脸上身上,却不觉痛。这一刻什么感觉都没了,我只是一个惊骇莫名急速下坠的点。
既短又长的时间之后,我感到下坠的势头停了。睁开眼,我才发现自己的手被人紧紧抓着,是何琴。奇怪的是手没有抓握感,仿佛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又过了片刻,所有的知觉忽然回来了。我的手被她握得生疼,身上每一寸皮肤都在火辣辣地痛。大概是松枝划的。我发现自己悬在空中,脚下什么也没有。何琴在我头顶上方,她的右手牢牢攀住一截枝干,左手伸下来攥着我的右手。她半侧着身子,像一只贴紧山崖的爬行动物。
“赶紧找个地方踩。”她发颤的嗓音从上面传来。
我们分别找了落脚点,稳住身体。我再次抬头,惊讶地发现不见阿奎和海椒。上面不远的何琴的脸上是一道道泛红的刮痕。估计我也同样狼狈。
我半天才挤出一个声音,飘忽得不像是自己的。“他们呢?”
何琴仰头张望,又低头看我。“不知道。你掉了好大一截。”
“啊?”我的大脑有些滞后,“那你怎么在这儿?”
“我跟着你跳下来的。”她灵巧地往下挪了两步,和我并排,仍抓着我不放。
我看看上面不见人影的松枝,又举目四顾。哪里也看不见绳子的踪影。我惊讶地发现,地面就在我们脚下不到五米。如果不是何琴,我现在多半躺在底下,死的,或是能喘气并且断了无数根骨头的。
我大概脸色煞白,何琴低声问:“还能往下爬吗?快到了。”
我闭上眼,深吸气,再努力睁开。“能。”
“我先下。”她大概怕我再掉下去。
她松开我的手,示意我沿着她踩过的松枝走。我全身软得像棉花,好不容易在意念的驱动下挪开手脚,贴着崖壁一点点爬下去。短短的距离显得无比漫长。脚底接触地面的那一刻,我以为自己会顺势倒下,结果没有。我站在何琴跟前,她轻声问:“这就是你说的地方?”
我本来正要努力对她笑着说“大恩不言谢”,听到她的话,我条件反射地举目四望,顿时感到呼吸困难。
这里不是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地方。不是什么妙谷。这鬼地方我绝对是第一次来。
我们的脚下是贫瘠的沙地,寸草不生。崖壁就像一道界限,山与地面接壤的地方,植物消失无踪,只有干涸的沙粒反射着阳光。
单调的沙地一直延伸到河边。河不宽,在视线那头从左向右流过。
河岸总算有少许绿色。对岸似乎又是断续的沙地,绿色与灰白形成遥远的条纹。
“你看。”何琴指着山谷的另一头。这里和妙谷一样四面环山,那边的山脚下有几个土黄色的物体。我有轻微的近视,眯起眼看了半天才意识到,那是房子。
有房子的地方就有人。掉在这么个凄凉得让人发慌的地方,看见房子,我们的心落到了实处。她拔脚就走,我在后面闷哼一声。
何琴转过身,我冲她苦笑:“脚疼。”
她蹲下来,掀起我的裤脚捏了下脚踝。我“哎”地一缩。
“有点肿,大概扭了。没外伤。”她判断。
我试着活动脚脖子,额上沁出汗水。“下来的时候都不疼,真奇怪。应该能走。”
“那就走慢点,”她眯眼打量远处的人家,“既然有村子,肯定有路可以出去。”
这处山谷比妙谷开阔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半个谷底沉在群山的阴影里,偏偏我们走的地方位于日光的炙烤之下。何琴又把我的包拿去背。两个人的水壶都是空的,原以为山里到处有溪流,装水不急在一时,谁想到会落在这么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现在我拖着一条伤腿,尽可能一瘸一拐地保持速度,却实在快不起来。走了快半个小时,还没到河边。
我被太阳烤得头晕眼花,对何琴说:“你先过去喝水吧,别管我。”
她把两个书包往沙地一搁。“你坐着歇一下,我马上回来。”她往河边跑去,我艰难地坐下,让伤腿保持僵直的姿势。沙地在屁股底下像块烧烫的铁板。
十多分钟后,何琴带着水壶回来了。她的脸带着湿气,大概在河边洗过脸。
“给。水的味道有点怪。还是少喝几口,当心拉肚子。”
“水清吗?”我拧开盖子问。
“清。不过没有鱼。”她的手指间摆弄着一朵带叶子的小白花,花朵有核桃大小,支棱着四片细瘦的花瓣,模样寒酸。
我毕竟渴了,咕嘟嘟地灌下几口水。从喉管到胃凉成一条线。水确实有味,从水壶的铁味儿底下透出来。我皱皱眉。片刻之后,一股热意从胃部升起,好像我刚才喝下的不是水,而是太阳光。我感到耳朵发烫,诧异地问何琴:“这个水你喝了不难受?”
她摇头。“还好,就是有种怪味。”
我不敢再喝,站起身,伴随着些微的晕眩。脚似乎没那么疼了,身子轻飘飘的。刚才喝的河水着实古怪。我来不及细想,毕竟按眼下的速度,天黑都未必能走到那头的人家。
河最宽的地方不过两米,窄的地方仅有一米左右。我们找了一处中间有石头的地方,没脱鞋袜就过了河。再往前的景色少了些荒凉。
沙地间错落生长着一簇簇的绿草,稀稀拉拉缀着小白花。是何琴从河边摘来的花。叶子和兰花相似,花形花色却差远了。我摘下一朵闻了闻,有种近似腐烂的怪味。何琴连根挖了几株,用旧报纸裹了放进书包。
我本想说都这会儿了你还有心思采集标本,又记起自己才是导致目前处境的罪魁祸首,只好闭紧嘴巴默默迈步。腿确实不那么疼了,有些僵,仍旧走不快。
我的手表显示着下午三点。山谷里的阳光早早地歇了,刚才的烈日显得近乎荒谬,只有山的影子沉沉地覆满地面。坠崖是在一点多,我们已经走了近两个小时。我想海椒他们可能快急疯了。有几次我侧耳聆听,但一无所闻。四下静悄悄的,连鸟叫虫鸣也没有。
开白花的植物渐渐少了,贫瘠的含沙黄土上出现了几块菜田。玉米,甘蔗,还有萝卜。作物们没精打采,却让我们感到某种振奋,彼此相视一笑。农家也近了。这时已经可以看出那是些土夯墙的房子,顶上连瓦片也没有,是草编的。这里的人够穷的。
田间没人。几只竹水桶扔在田头。奇怪的是没有水塘。难道这里的人得从那么远的河边挑水浇菜?我正在疑惑,突然有个尖厉的声音响起。那是个浑身赤裸的男孩,他像是从玉米田后面冒出来的,满嘴蹦出听不懂的词句,又喊又跳,还冲我们扔石头。
我们困窘地停住步子。那情形和遇到某村的疯狗差不多。你不知道该逃,还是该等主人出来收拾。
很快有另一个身影出现。那是个穿蓝布衫的女人,她把男孩打横一抱,一溜小跑地消失在高耸的玉米秆背后。男孩的叫喊声迅速移动,倏然断了。有风吹过。山谷里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活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被风撩得沙沙作响的玉米田。
我们站在原地等了会儿,何琴喊:“娘娘!”
她喊的是刚才那个女人。没人应。
又过了一会儿,玉米田后面走出一个人。这回是个老头儿。他身上的黑布马甲有点像白族男人的对襟衣,里面没穿衬衫,露着两条瘦筋筋的胳膊。裤子也是黑的,裤腿肥大,裤腰里插着木头烟杆,一头是镶铜的烟斗,看上去和镇上整日泡茶馆的老人没什么不同。
他高而瘦,背很直。等他走到跟前,居高临下地盯着我们看,我才发现这个人可能不像我最初认为的那么老。他比我爸大不了多少,是服装和腔调使他像个老人。
他盯着我脸上的疤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们是镇上的人?咋个来的?”
“我们是一中的学生,来采集标本,不当心从悬崖掉下来,我同学扭了脚。”何琴指指我的右腿。“这里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吧?”
男人从裤腰抽出烟斗,烟杆比常见的长得多。他把烟斗在手心里轻叩几下。“有。不过要天黑才能带你们走。先到我家。”
这人透着说不出的古怪。何琴和我对望一眼。她点点头,我知道那意思是“别怕,有我”,我抿紧嘴算是回答,迈开不灵活的步子,跟在男人的身后。
绕过玉米田,没多远就到了他的家。那是草顶平房中的一座,房子一侧搭了间像是灶间的小屋。没有放粮食的二楼,也没有猪圈鸡窝。
甚至没看见农家必备的水井。房前有两个陶制的大水缸,盖着木板盖。
堂屋比两侧的厢房缩进去一截,门外留了块带屋顶的空地。我们刚才见过的蓝衣女人坐在那里剥蚕豆,看见我们,她的眼睛一片漠然,019继续低头剥豆。我发现她没穿鞋,赤裸的脚粗大坚硬,像用石头雕成的。男孩不见踪影。男人从堂屋拿了两只小竹凳,我们在女人对面落座。
屋内光线昏暗,从外面只能看个大概,有张神案,有桌,有椅。没有电视。墙上挂着竹匾,没挂农家常见的年历。何琴家的清贫比起这里都要强些,而且这屋子似乎少了某种生活气息。
或许是因为没有院墙。我第一次看见没有院墙的人家。房前稍远处有片玉米田,算个遮挡。院里没有花,也没有果树,就这么灰秃秃的一片光地,让我爸看见会皱眉。黄昏的阴影覆盖下来,把贫瘠的景色染得柔和了些。
男人坐在想必是他媳妇的女人身边,长时间地咬着没点燃的烟嘴,像在沉思。他不时看我们一眼,视线似乎更多地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和我爸一样,我不擅长和陌生人说话。如果在这时被人告知,自己将来的职业会是天天和陌生人交谈的记者,我一定感到难以置信。
感觉到男人的注视,我紧抿着嘴。
打破沉默的是何琴。“阿叔,这里是哪里?”
女人停止剥豆的动作,没有抬头。男人放开烟嘴,没吭声。
黄昏似乎充满不可见的影子,灰蒙蒙地四处游移。五月的傍晚,按理该有虫声四起,蛙声呱呱。然而包裹我们的惟有不祥的死寂。附近也没有人声,甚至闻不到晚饭的气味。这地方古怪极了。
黯淡的黄昏让人昏沉,我几乎忘了刚才的问题,男人却在这时闷声说:“哪里都不是。你们出去以后,不许和别人说来过这里。”
他尽量装出严厉的表情,不算成功。我懵懂地想起《桃花源记》,这地方难道是另一个自愿被人遗忘的村落?然而后来的事情表明,一切都不那么简单。
“好多老鸹。”何琴在我旁边小声说道。这是在男人扔下那句禁令之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