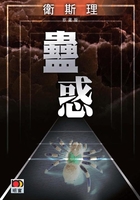一天,莘子刚刚从省城推销白灰返回,镇政府通讯员专乘来通知她,(此时公社正改成乡镇)说是镇上陈书记叫她。莘子只洗了一把脸,扬手叫过来一辆下完煤的大货车,将她送到镇上。多年来与各类人物的交往,他们心里想啥,莘子全然弄得清清楚楚。就说这销售白灰,学问可大啦!你和人家素不相识,社会上那么多白灰厂,人家凭啥用你的!莘子明白这一点,凡是她知道的基建工地,包括主管领导,工地负责人甚至包括工头,在与他们联系销灰时,她都将礼走在前边。她的礼不是自行车就是缝纫机。那阵这类商品全是紧缺的。那阵送这些东西如同当今送彩电,家电,摩托车,她送礼只送票,让人不知不觉这些礼品就到了家里,她就肯定击败了所有的白灰厂。加上这些人只要和她有了交往,那怕是一般的工人,开口要用白灰,或者给亲朋要,她都无偿送到其家,包括那些为她运石头拉煤的司机,她每每不只好吃好喝管待以外,发烟也是发条条。这样,尽管她送礼包括招待的支出不算小,但比起她的白灰多销增加的收入就微不足道了。她的事业的良性循环,使她的好人,热心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木梳湾距谷口镇仅十多里地,转眼车到镇政府门口,她思摸着陈书记大不了是给谁个要车白灰,也是几句话的事,安排司机在门口等一等。进大门,通讯员说:陈书记在办公室等!遂向她指了指房子,踅身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莘子敲门。陈书记似等在门边一样随手将门拉开。嗬,往常散乱的头发今日咋闪光闪光地贴在头上;还有那雪白的衬衣领,深红的领带,锃亮的皮鞋和笔挺的西服,被刮得眨青的下巴和满脸焕发的红光。莘子想,这个陈书记咋咧?今日似换了个人一般。坐、坐、坐,又是沏茶又是端糖盒又是拿水果,这一切显然是书记早已准备好的。最近还忙吧,销售咋样,听说您的产品已打进省城了。接下来陈书记拉开了大谈的架势。谈得激情了竟还在房内转来转去。由于晚上还要与一家用户联系,莘子尽量将话回得简洁明了。有几次她欲张口问书记有啥事,又觉不妥。便极力忍耐着等书记开口。书记却依然又是鼓励又是夸奖,又是希望地谈了一通又一通,无奈了莘子只得说:陈书记,我来坐的大货车,车还在门外等着,看你用车不?她的言下之意是说,若要用灰,立马就能送。书记听言却说:车还在等,你咋不早说,让车先走吧!等会事完了我另派车送你回去。无奈莘子只得出门差走了大车,返身回到书记房里。这一次书一边闭门一边直奔主题说:今天叫你来,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说着又将话收回去,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一双放光的眼贪婪地看着她。听此言,莘子则放松自己说:书记说笑了,我哪来的什么喜事呢!书记则嗬嗬笑着说:大喜,肯定是大喜,是你预料不到的大喜,你猜猜看!她听出了书记的话语中带出了挑逗之意,心中虽一沉,依然装出一幅笑脸看着书记,只看不说话。见她这般,书记又调侃般问:想知道吗?先得将我请一请,才能告诉您!这个陈书记当年和莘子的父亲在一块工作过,自从认识后莘子见他是不叫叔不开言,加上连年来又是现场会,又是去县上介绍经验,经书记介绍她销出的白灰,少说也上了百方。去年她申请要庄基,仅书记一句话,村上给她划的庄基比其他户宽了一间还多,她是将他当前辈和恩人待的,此时,听他之言,虽觉有点不舒服,还是热情地说:你说吧,叔,去县上还是去市上,叔愿去是看得起我,你点最高级的餐馆。书记则哈哈一笑说:叔没有那么高的口福,在咱镇上就行了。走吧,今天叔做东,祝贺您!走,去粮库餐馆,去了我再告诉你!粮库是国家在这个镇上新建的粮食储备库,直接归地区管。据说原是要建在市上,因了战备,迁到这个镇上,里边的职工和领导全从城里来。粮库建成后,大门在新开发的街面上,他们迎街便建了个二层小楼,一楼就餐,二楼歌舞厅住宿。莘子多次在那儿宴请过客户。
出书记房门,见镇机关其他同志的房门都关着,莘子问:还有谁呢!她意思是将其他领导都叫上,书记说:放假了,我值班,就咱们俩人。说着话书记走到她前边。莘子只得怀着忐忑的心跟在书记身后。出镇政府大门,向右约50米,进了饭店。菜是莘子点的,酒是书记给自己要的白酒,给莘子要的红酒。举杯之前,书记如开会般庄重地对娃说,县上从农村召收一批半脱产的干部来加强和充实农技和妇女工作,我推荐你,已批准了。你为半脱产的镇党委的妇联主任。真是一个无法预料的大喜事!当初其所以办白灰厂,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工作,也就没有了和海生抗衡的资格。她是憋着一股劲干的,她要让事实证明,看是我的能力强还是你海生的能力强。眼下,她自认自己成功了,曾一度,她朝思暮想地策划着,如何样在他面前再一次证明我的价值,再一次让他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可又一想,人家总归是干着国家的事,自己挣的钱再多,依然是个农民。心中又开始萌生了找个工作的念头,可总没有一个机会。前一段听说抛弃了她母女的父亲退休后让其养子顶替招了工,她一气之下还去质问父亲:难道这个亲生的女儿还不如假儿子。她去时少说也给父亲拿去上千元的礼品,她不是要父亲去享受而是要他看看他的女儿啥也不缺。她的质问让父亲有了悔意,但生米已做成了熟饭,父亲只得劝她回了家。她明白自己挣钱一辈子也花不完了,就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找个工作。以往公社招工,她也托人找过领导,但每每都没有结果,很显然,她要工作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挣钱,她除过为了名声外,是要击败海生并将他抓到自己身边来。
真是瞌睡遇上了枕头!莘子心中一阵惊喜,忙举起酒杯说:叔,谢谢您关照,喝!她俨然似个男子汉一般高高举杯。书记便应声站起,道一声,喝!一杯酒便一饮而尽。酒过三杯,俩人脸上都带了红。书记说:你今日别把我当书记,也别当叔,全当咱是好朋友,行不?此时莘子已喝得心热了,脸红了,头晕了,顺口就说:行,叔!全当咱是好朋友!书记听言,更来了劲儿,立马高高举杯说喝!又一杯一饮而尽,随即脱去外边的西服。动手先给自己斟一杯,放下白酒瓶便要抓红酒瓶,被莘子一手挡定说:我也来白的,我不喝白酒就对不住书记!书记说:好!好样的,象个巾帼英豪,喝。俩人咣地一碰,一杯酒又见了底。莘子平素只喝点饮料,少量也喝点啤酒、葡萄酒,白酒却从来未沾过唇,刚才喝首一杯,似乎觉得有了香味,一连喝下三杯、反倒心情爽快,周身燥热,头皮紧蹦,脸额绯红,似有千言万语要倾诉。情不自禁地向书记谈出了她的朋友海生当年是如何地爱她,她妈给她胸前做的小白兔是如何的好看,俩人如何的发誓要上大学。她还咬牙切齿地说:若不是那个文化大革命,他们早就大学毕业住进省城了,她说着又喝,喝着又说,说着又哭。书记虽也喝得多了,但却头脑清楚,不时地顺着她的情绪插几句她爱听的话,一时间说得个莘子只剩下拿起瓶子给下灌了。少说也喝了三个多小时,眼看太阳落山。莘子已醉得如一滩烂泥。书记叫服务员把她搀扶上楼,开了一个包间。服务小姐刚一离去,书记便倒锁了房门,先脱了莘子的衣服。当他给她解开扭扣,解开内衣扣和裤带时,烂醉如泥的莘子呓语般海生,海生哥地叫着,竟还亡命地来抱书记。书记先还愣愣地躲一躲,见她抱得急切,倏忽间似又明白了什么,便手儿颤颤地,气儿喘喘地边脱衣边说:乖乖,海生哥来咧!说着叫着,一身子扑上去,把个莘子激动得连声海哥海哥呀呀地叫着,如同一道铁箍一般抱住书记的腰。他们是怎么干的,干了几次,二人也许都说不清。
窗外一声长长的鸡鸣,将莘子惊醒,莘子头一动,似乎枕在一个软乎乎热乎乎的什么上边,睁眼一看,看见的是茸茸的胸毛,再看,书记如死猪一般睡在她的身旁,她如同触了电一般一把推开他,一身子跳到地上。她终于明白过来,一头扑过去骑在书记身上,又捶又骂又哭又嚎。书记被打醒了。双手推她到一边,边穿边说:你还以为你十七,十八咧。听此言,她似当头挨了一棍,无奈穿上衣服。咱是高兴,喝多了,你也回不去了,就住到这儿!书记说。让别人咋说呢!莘子悲哀地说。你放心,不会有啥事的,你若愿意咱们继续相好,若不愿意,我会保护你的,你放心,事该咋办仍咋办,我绝不是趁火打劫。更不会强迫您。书记说着在她肩上拍了一把。莘子坐在那儿不说话。放心吧,明天就来上班,你相信我,只要你真心爱那个海生,是他娃的福份,我会成全你的!书记说着笑了。莘子脸上的气显然有了消退。去还是不去!莘子整整想了一个晚上。
她和陈书记相识是人家抓典型主动找上门的,只凭陈书记那方脸盘、高鼻梁,开言眼角都带着善意的面容,莘子决心投靠这样的领导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也对她有了许多的好处。此时莘子一直在想你一个长辈怎么伪装得这么好,原来你待我好是有目的的,或者说是蓄谋已久的。想我莘子在社会上闯荡这么多年,什么样的男人没经过,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有一年,与一辆车同去彬州拉煤,深更半夜返回时,司机在大山深沟里将车一拐,拐到山背后一个岔路上直言要和她弄那事,还说只要她答应了,一车煤运费不要,再给她拉一车。听此言,莘子伸臂就是两个耳光,打后丢下一句:你狗日还算个人!打开车门跳下车便走,边走边说:煤也不要了,你给我滚!当时,天黑得连路和沟也分不清,她摸摸爬爬一鼓作气朝前走。司机显然是悔了,调头追上来,停车跳下来拽住她说:姐,我不对,我再不咧!她手一甩继续朝前走。就这样,她在前边走,司机在一边开,断断续续走了好几里路,司机只剩下叫一声婆了,仍将她叫不上车,只得驱车而去。那一夜她一直走到天亮,才坐上了长途班车。等赶回家,脚上已磨破的泡将袜子都沾了上去。此事后来让那个司机给传了出去,当然是赞美她之人品时说走了嘴,立马在周围传出了一片风声。她也成了当地女人贞操的榜样。县上有一个管车的单位的小头头,因给她派车多次照顾,出于感激,逢年过节她便带着一些土产去看人家。小伙子已过而立,仍未婚配,确实长得一表人才。加上人家对她的热情,似乎比得她心中的海生也退了色。一次,不知人家咋知她病了,拿着礼品来看她。当时她发高烧,躺身床上三天三夜水米没沾牙,母亲见她来了男朋友,有意避开。用母亲的话说,只盼我娃能尽快抓一个男人回来。见母亲出去,小伙子侧身坐她身边,伸手在她的额上摸试还烧不烧。当他抚上去的手久久地不愿离去时,似有一股热流倏然传遍了她的全身。让她的病弱的心一下子紧缩了,颤抖了。她的心气微微地喘着,她的双手儿颤颤地攥着,她的嘴唇儿吃力地一张一合,她迫切地期盼他的双唇能偎上来吻她一下。当时的他从她的激动和迫切的目光里,似乎看出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痛苦的生命的支点,他的腰身慢慢在弯,他的脸庞向下移,他的双唇似充了血一般已微微张开。眼见着两张嘴唇就要接触了,她却是双臂用力将他推开,将头偏向一边,禁不住的热泪夺眶而出。
这便是莘子的与人不同之处,她的超越常人的自制和把握自己的能力,使她终于保护了自己的贞操。这么多年,莘子就在与自己,与他人的博斗中挺了过来。眼下到了这一步,却糊哩糊涂栽倒在陈书记的面前,这其间的悲和恨咋就集中在了她一人的身上。她该咋办呢!莘子开始比较冷静地回忆上楼之后的情景,她觉着自己迷迷糊糊被人搀扶进了一个房子,她似明白又似糊涂地被放在床上,他只觉得天旋地转便转出一个海生来,她就呼喊着拥入他的怀抱。她忘命地迎接那幸福和舒坦地尖峰时刻。后来她就啥也不知了。尽管那声鸡鸣叫醒她时,看见睡在她身边的却是书记,而她惟愿这个人绝对不是书记而是海生,她还想即就是书记他也只是扮演了一个海生。这对书记而言又有何意义呢!如此自慰一番,她反倒觉出了书记的可怜。他虽是她尊敬的人,却永远不会成为她心目中的可爱的人。想到此,莘子开始觉出不可以将此事过于认得真。那么去还是不去;不去将预示永远和这个陈书记勾鞋弹烟锅,永远地勾去了他的人情;不去,将失去一个她将海生夺回来的最重要的砝码;去,也许会遭世人非议说:莘子用自己的身子换了个国家的饭碗;不去,等于不给陈书记这个面子(因为她去镇上上班之事最少镇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已知)这个高喉咙大嗓门的陈书记一旦发怒,说不定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去一个新的环境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在等待着她?书记还会不会和她纠缠不断?如此这般地反复对比,也许是美好前途的驱使,也许是和海生要终成百年之好的勇气,终于使她最后做出决定:去,即刻就去。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的非常重的一条是,她不信在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中,你陈书记会在这个镇上干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