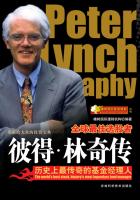贞元十七年冬天,韩愈又来到了京师,十八年(802)春天,始被朝廷任命为四门博士。奔波了多年,总算当上了朝廷命官,尽管这一任命姗姗来迟,且与韩愈的期望相差甚远,他还是接受了任命,毕竟这是朝廷命官,与当幕僚不可同日而语啊!这一年韩愈三十有五,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了。
四门学设博士6人,正七品上;助教6人,从八品上,还有直讲4人。这就是说,韩愈任四门博士,仅是一个正七品的官员。唐朝的官员共分九品,正七品是比较低的。唐朝的县令,京县令正五品上,畿县令正六品上,上县令从六品上,中县令正七品上,下县令从七品下,韩愈的级别仅与中等县的县令相当,以他的才学而论,确实是委屈他了。
贞元十九年(803),关中发生了旱灾,自正月至五月都未下雨,到了七月,关辅之地便出现了饥荒,有人提出罢吏部选、礼部贡举,以节省京师粮食。因为旱灾,便停止科举和吏部选拔,似乎有些荒唐。其时韩愈虽然没有上朝的资格,但还是给德宗上疏,表示反对。他在《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一文中说,臣窃以为十口之家添一两个人吃饭,不会多消耗很多粮食,如今京师人口不下百万,参加举选者不过五七千人,再加上他们的僮仆畜马,也不够京城人口的百分之一。况且今年虽因旱歉收,而去年则五谷丰登,商贾之家,必有储蓄,凡参加举选之人皆带有钱粮,以有易无,不会有多大弊端。如果暂停举选,带来的危害必然很大,因此应当慎重对待此事。可惜的是德宗并未采纳他的意见,贞元二十年(804)还是停了举选。韩愈人微言轻,区区一篇奏疏,没有引起天子的注意。
建议没有被采纳,只不过是一点小挫折,并不影响韩愈丹心辅国的悃诚。在任四门博士期间,他写的《师说》,成了千古传颂的范文。这篇短文是为跟他学习古文的青年李蟠而作,实际上是对那些轻视教师的人所作的批判。
《师说》一文层次分明,先以圣与愚相比,圣人尚且从师,何况愚人次以子与自身相比,子尚择师,何况自身最后以巫医、乐师、百工与士大夫相比,巫医等人尚且从师,何况士大夫清人林云铭说,本篇“行文错综变化,反复引证,似无段落可寻,一气读之,只觉意味无穷。”这深得韩文三昧之言。
尽管韩愈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但是官阶太低,俸禄不丰,致使贫困如影随形,始终未能摆脱,这使他苦恼不已。在人烟辐辏的京城,他看到了许多令人不解的现象:有些人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沦落风尘;有些人茸无能,却扶摇直上。有才者率多短命,无才者反而长寿。两相对照,真是判若云泥,不知老天为何如此不公愤懑之中他给好友崔群写了一封信,感慨地说:“自古以来,贤能的人少,不肖之徒多。自有记忆以来,每每见贤能的人多生不逢时,遇不到赏识自己的明主,而不肖之徒却往往飞黄腾达,拖青曳紫;贤能的人穷愁潦倒,谋生维艰,而不肖之徒却志满意得,骄横恣肆;贤能的人即使能弄个微小官职,便短命而死,而不肖之徒却驻颜有术,往往长寿,不知造物者为何竟有这样不公平的安排”
在谈到自己的情况时,韩愈说:“我自任四门博士以来,也算是有了官阶,但穷困反而更甚,我曾多次想归隐垂钓于伊水、颍水之畔,大概能够如愿。”当了朝廷命官,反而更穷困了,现实生活使韩愈又一次想到了归隐。垂钓于伊水、水之畔,不比当七品的四门博士逍遥自在得多吗每当心灰意冷之际,韩愈便想到了归隐,其实这不过是气愤之语。
多年四处奔波,韩愈还不到不惑之年,身体却明显垮了。他在信中对崔群说,近来尤感衰老疲惫,左牙床第二枚牙齿无故动摇脱落,眼睛看东西如雾中看花,平常便分不清人的颜色,两鬓已经半白,头发有五分之一已经发白,胡须也间或有一根、两根斑白了。一代文豪落魄到这种程度,真使人心酸!
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呢韩愈没有办法,只得故伎重演,给那些有权势的人上书,希望他们动恻隐之心,伸手拉他一把。贞元十八年七月,他先给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于上了一封书信,即《与于襄阳书》。但是于既没有因韩愈的吹捧而举荐他,也没有因韩愈哭穷而慷慨解囊,只是回信说:“足下之言是也。”尽管如此,韩愈仍感激涕零地表示:“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才,而能与卑鄙庸陋相应答如影响,是非忠乎君而乐乎善,以国家之务为己任者乎愈虽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谓之知己。”于只是回了一封不痛不痒的信,韩愈便把他当作知己,真让人不可思议!
给于的信既不得要领,韩愈又给任给事中的陈京写信。但是这封信的遭遇和上一次一样,一发出去便杳如黄鹤,没有回音了。
韩愈不甘心,又给京兆尹李实写了一封信,即《上李尚书书》。李实在任京兆尹前任过检校工部尚书,因此称之为尚书。对于这样一个人人皆曰可杀的人物,韩愈为了借重他,不惜违心地吹捧,并且颠倒黑白,将无作有,把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说成是体察民情、公正廉明的清官,这可能是韩愈一生中最荒诞的文字。
尽管如此,李实并不领情,不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甚至连片纸只字也没回复,这使韩愈伤感不已。心绪不佳,便觉得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在任四门博士期间,韩愈还写了《赠崔复州序》、《送许郢州序》、《送孟东野序》、《送陆歙州诗序》、《送齐下第序》、《送浮屠文畅师序》等作品,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在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作品,大概就是《圬者王承福传》了。
韩愈在任四门博士期间,政务不多,交游不少。仕途上的失意,曾使他一度有归隐的念头,但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并未付诸行动。读了那么多书,受了那么多苦,他怎能甘心与樵夫、钓徒为伍呢
到了贞元十九年秋,韩愈的四门博士已经当了两年,按照唐代规定,任期已满,必须从这一岗位上调出。韩愈没有后台,何去何从,不禁搔首踟蹰。就在他茫然无计之时,御史中丞李汶举荐他为监察御史,他才如释重负,感到无比轻松。
监察御史的官阶为正八品下,比四门博士还低,尽管如此,韩愈还是高兴的,因为他毕竟有了为天子效力的机会。虽然监察御史级别较低,权力却大,比坐冷板凳的四门博士强多了。有了这个官职,韩愈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他踌躇满志,准备干一番事业了。
不幸的是,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了侄子老成病逝的消息,这不啻是晴空霹雳,把他震得手足无措了。
老成之死,给韩愈精神上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身体也每况愈下了。他写道: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未能亲自料理老成的丧事,使韩愈抱恨终天。经过这一次打击,韩愈对一切似乎都已心灰意冷,再一次萌生了归隐之心。
处理完老成的后事,韩愈才去正式上任。这一年关中大旱,禾稼不收,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辗转沟壑,饿死者甚众。身为京兆尹、爵封嗣道王的李实,不去抚恤百姓,却大肆横征暴敛以给进奉。德宗每问及灾情,李实便上奏说,今年虽旱,但禾苗甚好,不影响收成。优伶成辅端看不惯李实这种恶劣行径,编成歌谣加以嘲讽,李实大为光火,上奏说成辅端诽谤朝政,结果被杖死。面对这种情况,韩愈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御史是言官,弹劾邪恶、为民请命自然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但是李实又是权势熏灼、手眼通天的人物,能不能扳倒他,是个未知数。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得罪了圣眷正隆的李实,那是要吃苦头的。如何定夺,韩愈不能不慎重考虑。这些顾虑在《苦寒》、《题炭谷湫祠堂》等诗篇中都隐隐约约有所流露。但韩愈也同样想起了几年前自己在《龊龊》一诗中的几句话:“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为什么不敢挺身而出,只考虑自己的荣辱得失呢如此畏葸不前,还算什么御史呢想到这里,他只觉得浑身热血沸腾,毫无顾忌地写出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在这篇奏疏里,韩愈首先说了关中的旱情:京畿诸县夏季亢旱,秋又早霜,所种田禾,十不存一,百姓被迫弃子逐妻以求口中之食,又要拆屋伐树以纳税赋,悲惨之状,殆非笔墨所能形容;其次颂扬天子圣明,皇恩浩荡,怜念百姓,同于赤子,犯法之人,还要赦免,何况这些无辜之人!京师乃国家根本,这里的百姓更应抚恤;最后为民请命,这才是他写这篇奏疏的关键所在: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韩愈在最后这一段反复斟酌,多次润色,既要反映百姓的疾苦,又要不引起当权者特别是李实的反感,直到他确认万无一失后,才把奏疏递了上去。这时已是朔风凛冽的冬季,虽然周天寒彻,但是韩愈并不觉得冷,他为自己办了一件应该办的事而感到惬意。
使韩愈始料不及的是,就在贞元十九年的年底,他突然被免去了监察御史的职务,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他在御史任上只干了几个月,还未来得及施展抱负,便被排挤出了朝廷,这使他困惑不已。
贞元十年的岁末,正是天气冱寒、滴水成冰之时,朝廷派人催促韩愈离开长安,到贬官的阳山去。说是催促,其实是逼迫。若干年之后,韩愈回忆那次被逼上路的情景,还不寒而栗。
韩愈不是一个人到贬所的,同行的还有张署。张署是河间(今属河北)人,长于文词,当时也任监察御史,遭人诬陷,与韩愈一起贬官,韩愈贬阳山,张署贬临武(今湖南临武东)。同是落难之人,此次结伴同行,路途上有个照应,自然比孑然一身好得多,两人从此成了知己。一路上雪虐风饕,山径泥泞,两人几次被颠簸于马下,韩愈涕泪交流,张署则号啕大哭。夜晚憩息于终南山下,两人同卧一席,因为是流人,照例有士卒押送,这些守隶防夫头足相顶着睡在一起,就在他俩身旁。当这些押送的士卒鼾声大作,梦入黑甜时,韩愈、张署却辗转床笫,不成梦寐,即使入睡片刻,又马上被噩梦惊醒。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愤懑、忧伤困扰着他们,简直是没有一刻安宁。
贞元二十年(804)初春,韩愈、张署来到了郴州(今属湖南)。
张署贬谪的临武属郴州管辖,到这里已无须再走,韩愈自湖南至岭南走郴州、临武、连州一路,须翻越骑田岭等高山,两人便在临武分袂,所谓“君止于县,我又南逾”是也。同是天涯沦落人,患难与共成相知。一路上彼此照顾,现在只剩下韩愈一人孤雁南飞,心里不免有些凄楚。
贞元二十年初春,韩愈经过千里跋涉,终于来到了贬谪所在地的阳山,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
韩愈身在阳山,其实心在朝廷,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也。他没有怨恨朝廷对他不公平,只想早日结束贬谪生活,重新回到朝廷。尽管他在阳山为官也兢兢业业,但仍然翘首企盼朝廷召他回朝。
韩愈在阳山一年多,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夏奉大赦北上郴州(今属湖南),在郴州刺史李伯康处待命。他在郴州三月,潜心着述,完成了《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等重要论着的写作。八月,韩愈得赦书移官江陵(今属湖北),任法曹参军。韩愈在江陵,与荆南节度使裴均过从甚密。均着有《荆潭唱和集》一卷,愈为作《荆潭唱和诗序》。在这篇诗序中,韩愈提出了“文穷而后工”的理论。这与他的“不平则鸣”说是紧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