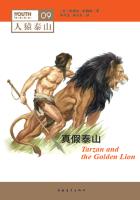--此文献给1994年站在冰排上的男孩
我和爸爸的父子关系有十年多了。在这10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多半不太融洽。爸爸是守在海与河之间的打鱼人,我是玩在河与海之间的淘孩子。我们总是想不到一起。
我们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叫营口的河海之滨发生的。这个小城濒临渤海,还有一条大河在这地方入海。这条河叫辽河,在中国地图上能找得着的,它在我家后面悄悄流过。我和爸爸的故事总与这片海这条河有关。再加上一条船,我们的故事就在河与海之间漂来荡去的没完没了。这期间有战争,也有和平,就像身边的海有汹涌咆哮也有风平浪静。我不承认这是什么高明的比喻,但确实是这么回事。那条船,是爸爸一直独占着的私有财产。鉴于我们的紧张关系它将来的继承权肯定不是我了。爸爸说过,宁可把它烂在水里也不会把它交给我。我可是一直惦记着把它弄到手,一个人驾着漂出河口到海上玩一天,可带劲儿呢。
大约一年前,我们的生活中多了黑云。当时黑云它蹲在河码头下流泪,一条腿还流着血,把下面的河水都染红了。黑云刚刚被主人抛弃。兔死狐悲,那天我想,爸爸哪一天被我气疯也会不要我的。但那是一件好事,我不会哭的。我获得自由了。
我决定收留这条黑狗。爸爸没言语,蹲在船头吸烟。船一随浪颠簸,把爸爸吐出的烟顿成了烟圈儿。看来还得跟他干一仗。想罢我脱下褂子摔在船上,叉着腰,怒视他。
怎么?不同意吗?我问。
我与爸爸的战争中,我属于屡败屡战、屡战屡败那种。但我从不甘心失败永远斗志昂扬。
爸爸还是没吱声,不过我发觉我们的船开始向码头靠近。两分钟后那条黑狗被我客气地接到我们的船上。望着爸爸的背影,我不相信已经取得了胜利。这可能是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吧,我悲观地想。
我边给黑狗擦伤口边给它取好了名字。
它叫黑云吧。怎么样?我问爸爸。没有请示的意思,他不是我的上级,这是对“战败国”的尊重。
爸爸咧嘴一笑,说,名字这东西就是个记号,叫啥不是一样。
我不甘示弱。我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不管你叫爸爸叫别的也一样呗,比如叫耳朵叫鼻子?
爸爸说,对。
这样,我收留了黑云。我暗自决定,在我计划中的那次漂流中也算上黑云一个。
黑云很快成了我们这地方孩子世界中的知名人士。有黑云撑腰,再也没有孩子敢欺负我了。在任何一条胡同里玩耍,只要有黑云在,我都能够大摇大摆目中无人。有一回我翻一本连环画,才知道这就叫“人仗狗势”。管它呢?自从有了黑云我威风多了,这才是主要的。
爸爸驾他的船贪黑起早地打鱼,有时要顺流漂到海中去,漂出很远。爸爸越漂越小最后连个黑点都看不着。有时还要逆河而上到河滩上捕河蟹。这要看什么季节了。在这方面爸爸是行家,与我没关系。
有一回爸爸出海捕鱼,我和黑云也去了。晌午,爸爸把船拖上沙滩。爸爸望着这片金黄的沙滩,说,这要是一片金子多好啊!
这要是一片金子多好啊--爸爸是越来越贪财了。
不只是爸爸,我们的小城整个发生了变化。以前小城是黑白的,现在变彩色的了,像电视机一样。一到晚上,灯红酒绿,熏燎着我们这个小城,小城的天空不再有腥咸的海风。大人们都惶惶的,丢弃了渔船爬上岸,脱掉湿淋淋的水衣,开海餐馆、炒股票、经营工厂。
孩子的世界也在变化。作为一个男孩子光有一个威风凛凛的黑云已经不够了,要有许多东西才行。花花公子皮鞋鳄鱼夹克,最好再有一双旱冰鞋。这东西在男孩子中最流行。这回轮到人家穿着旱冰鞋神气地从我身边滑来滑去了。胡同里少有的几个女孩也背叛了我和黑云,整天忽闪着漂亮裙子跟着“旱冰鞋”转。我朝她们背后淬了一口:朝三暮四!黑云也扯开嗓子汪汪吼了几声。那几个女孩哇地哭喊着像耗子一样没了踪影。我嘎嘎笑了个够。
渐渐地伙伴们疏远了我,特别是那几个有旱冰鞋的伙伴。我总是让黑云朝他们大咬大叫,他们怕黑云就远远地跑开。这更好,清净。以前那种前呼后拥的生活我还烦呢。这样我和黑云经常形单影只地出现在胡同里码头上。我经常大声笑着,好让那些神气的伙伴们知道没有旱冰鞋我照样过得快活。我开始教黑云跨围栏,匍匐前进,还教它叼飞盘玩。我要让黑云像个军犬。
爸爸说,这就对了,这有用。省得整天白吃饱。
我说,我不是为了有用。别把黑云当东西用。黑云不是东西。
爸爸说,对,黑云不是东西。
我又有很长时间不跟爸爸说话了。实际上是爸爸很长时间不跟我说话了。我认为这是一码事,不涉及谁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问题。爸爸经常蹲在船上发愣。他的网打不上太多的水货了。打上的水货又有一股废油味,不好吃。爸爸的日子不好混了,不过这跟我无关。我想把爸爸从我的故事中排挤出去,只留下黑云。黑云摇摇尾巴,表示同意。黑云就朝爸爸吼了两声。我满意地打了个口哨儿,叫上黑云,去码头上玩叼飞盘。
我们在码头上玩飞盘,有个叫锥儿的男孩在我身旁把旱冰鞋哧地来个急刹车,一甩头发说,这游戏我在电视上看过,你和黑云那两下子根本不上档次!
我火了,我说,谁又没请你当裁判!
黑云听罢,扔下飞盘,嗖地跃起来向那个叫锥儿的男孩扑去。他们都哇哇叫着,哧哧滑进了胡同。四个人一共摔了六个跟头。我兴奋地数着:一个、两个、三个……
我一抬头,看见爸爸。爸爸肩上挂着水淋淋的网,在阳光下闪着星星。脚下积了一摊水。就是说爸爸在这里站了半天了。我没注意。黑云也没注意。
那天晚上,爸爸从网上衣服上抖下许多沙子。望着那堆沙子,爸爸说,要是一些金子多好……这回我对爸爸的这个愿望有了兴趣。我说,要是有了金子就能……就能像电视里一样给黑云配上一身红褂子……
傻话,狗不是人,狗不用穿衣服。爸爸说。
去,黑云,把这件破衣服给我叼走。爸爸对黑云发出命令。
黑云歪着头瞅着爸爸,没动。我想,黑云真够朋友,除了我,谁的话也不听。
去!爸爸挥了挥拳头。
黑云竟妥协了,夹着尾巴奔到墙角,把爸爸那件破衣服叼了出去。
黑云这么没骨气。我很失望。
我没能把爸爸从我的故事中排挤出去,却要与爸爸的船分开了。天一冷,辽河水流成了冰,一直流到海里,到爸爸封船的时候了。河面上再也看不到一条船的影子。没有了船我开始注意河对岸,那边已经冒出许多高矮不齐的黑烟囱,在烟囱上方形成一团团黑云,久久不散。没有事我就带上黑云一齐蹲在河边数对岸的黑烟囱。每次我都数两遍。有一回是“十六”,有一回是“十七”,又有一回是“十六”。于是我断定是十六根。有时黑云蹲腻了就一跃,跃下河堤,到冰面上不时把嘴贴在冰上嗅嗅。我犹豫了一下,没跟下去。辽河的冰结得薄,人是从来不上去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冰会从这岸裂到那岸,裂成一条大缝。啾--像枪响,像甩鞭,裂成一块冰排整个往海上漂去,最后化成海水的一部分。大人们一提到冰裂脸色总是煞白。我不太怕,有一天能站在冰排上往海里漂一回才好呢,肯定比坐在船上强多了。可是我都没亲眼看见过裂冰。有几回裂冰都在夜里,一声脆响刺破黑夜。激动地想,裂冰了!躺在床上就再也睡不着。
爸爸封了船,也时常蹲在河边望着对岸。有趣儿,爸爸也在数烟囱了。本来爸爸也可以像一些闲起来的人,钻进灯红酒绿的地方转转。可爸爸没钱。
爸爸准备出城。
我问,去哪儿,要不要我和黑云陪着,你一个人,多没意思。
爸爸说,又不是去玩,老实呆着。然后走了。
我恨自己,骨头真贱,差点求他。
后来,爸爸回来了。爸爸说他去了河对岸那块地方,绕了很远才在一座桥上过了河。那块地方全是工厂。
爸爸说,我弄明白水货为啥有油味了,是工厂放出的黑水流进了辽河。
原来,爸爸是去生长黑烟囱的地方去了。晚上,爸爸从衣兜里掏出一截黄澄澄的棍,
让黑云叼。
是金子吗?我问。
是铜。也值钱。爸爸说。
爸爸为了能让黑云叼铜棍,为它准备了一条咸鱼,作为奖励。爸爸想要黑云玩玩,我没反对。黑云不会听他的。
果然黑云不叼。我不发话黑云不会叼的。爸爸掏出咸鱼。黑云看了看我,没动。
我说,叼吧,有你好处。黑云叼了铜棍,然后品尝咸鱼,并不停地冲着爸爸摇尾巴。
我说,爸,练习叼铜棍没啥好玩的,别玩了。
我说,别玩了,我不同意了。
爸爸说,这不是玩,有用。
我没管爸爸的态度,叫上黑云走开了。我不希望黑云跟爸爸打成一片。
我和黑云下一次大型的计划是能出河口到海上玩玩。当然不算爸爸,是单独行动。望着河面上的白冰,我觉得我们的理想还很遥远。爸爸的船还在岸边封着呢。
要是一条破冰船就好了,冰也封不住。
一天晚上,我做了个噩梦,醒了。
黑云。我喊道。喊了两声也不见黑云来。以往,只喊一声,就会听见黑云走过来,还能听见摇尾巴的刷刷声。黑云不见了,再找爸爸,爸爸也不见了。
爸爸带回一身冷气。我听见叮当的摔撞声和黑云大口喘着粗气的声音。
爸,不许你把黑云带走,黑云是我的。我跳下床,发现黑云的脚上粘满冰屑。我还看见黑云的嘴巴在滴血。
爸!黑云怎么啦?
我带黑云去冰上练习奔跑。爸爸搓着手,跺着脚,然后上床睡着了。我跳上去揪住他的耳朵喊道:我警告你--
黑云嘴上的伤第二天就好了。可我执意向爸爸要钱为黑云买药。
爸爸冷着脸说,它只是一条狗。爸爸没给我钱。我只好紧紧抱住黑云的脖子。
以后一连几天我没发现爸爸再带黑云出去,也许是我的警告起了作用。
有一天爸爸喜滋滋拉上我去了商场。爸爸神气地拍了拍腰包,今儿个挑双旱冰鞋,爸爸我有钱!
我没客气,挑了一双带劲儿的。一站在柜台前我才承认自己早就盼着这一天呢。爸爸付了钱说,爸爸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这玩意。
我穿上旱冰鞋在外面滑来滑去,黑云在我身边跳来跳去,大雪天都不嫌冷。那个叫锥儿的男孩小声嘟囔着,瞧瞧,出了个神经病!
那天晚上我把旱冰鞋放在枕旁,闭上眼睛却睡不着,总忍不住伸出手摸摸旱冰鞋上的小轮子。过了很长时间,我听见爸爸打了个哈欠,起床了,几下穿上棉衣,接着,叫了一声黑云。我一看天还没亮,就知道这里边有故事,装作没听见,偷偷跟出去。
爸爸的黑影蜷在河堤上。一道黑影向对岸射去。冰面上哒哒响着……
黑云--我知道,那是黑云。
别叫。爸爸一惊,转回身捂上我的嘴。
回去。爸爸说。
我不!你是在害黑云!黑云会遇到冰裂的!
不久,冰面上那道黑影又出现了,片刻就跃上河堤。叮当一声,是金属碰撞的声响。爸爸把那几件东西揣好,然后把一条咸鱼扔给黑云。黑云连看我一眼都没有,叼起咸鱼,又跃上冰面,转眼不见了。
我跺了跺脚,离开了这里。几条咸鱼就被收买了。我决定与黑云绝交。
当天夜里我就弄明白了,黑云从对岸叼回的是黄澄澄的铜棍,还有别的东西。都是那些竖起黑烟囱的工厂制造的,冒出几缕黑云再放出许多黑水,就制造出那些“产品”。
黑云,成了小偷。它幕后的老大便是爸爸。
我飞起一脚踢在黑云的腿上。黑云嗷嗷叫着,但没有跑开。我看见在黑云脸上有两道水迹,水迹正越拉越长。黑云哭了,嘶嘶呻吟。可我还是决定与黑云绝交。
首先,与爸爸绝交。
我不管你叫爸爸了!叫……
叫鼻子吧。爸爸拍了拍我。
我管你叫鼻涕!叫鼻涕!脏!
我操起那双旱冰鞋。
这鞋是偷来的,我得还给人家。我说。
他们放黑水呛走了鱼虾,他们欠咱们的。“鼻涕”指着对岸的烟囱。
我捂上耳朵。我也哭了。我与他正式绝交了。从此我叫他鼻涕了,再也不改回来了。
与黑云绝交也很简单。我与黑云面对面站着。我说,黑云,咱们结束了。黑云一直望着我。我不再看它。我不喜欢看它脸上那两道水迹。
我飞快跑到河堤上,小心地踏上冰面。冰面很结实,可见大人们骗得我们好苦。我们要是知道这冰面上能走人,小城里是不会流行旱冰鞋的。我放心地在河面上向对岸走着,离对岸越来越近,烟囱也越来越高,马上就到河心了。忽然我觉得脚下一震,接着嘎--啾--一条裂缝出现了。
冰裂了!我终于亲眼看见了。说不上是高兴是害怕,心嘣嘣乱跳。裂缝越来越宽,露出了灰汪汪一条水带。我脚下的冰排正向河口漂呢。这时我希望河堤上能有人,最好是那几个伙伴,让他们看看我正站在冰排上往海里漂呢。他们肯定羡慕得要死。这感觉比站在旱冰鞋上美多了。可河堤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却越漂越快,能感觉到对面河岸上的黑烟囱在向后移去,脚下的冰块却在变小。我是站在一个四面不着地的“冰岛”上向海中漂去啊!
河堤上有人了。冰裂开的响声惊动了他们。
坏了,一个小孩在上面呢。坏了!有人惊叫。
我一听见人们议论才有点害怕。我于是向他们挥动手臂,可是没有人肯下来。是啊,谁那么傻呢。我继续向前漂移。岸上的人们跟着我涌动。人群中突然窜出一条黑影。
黑云--我用尽力气喊着黑云的名字。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原谅了黑云,并且,看见黑云心里热热的。
黑云纵身跃下河堤,跳进冰水中向我游来。有些小冰块不时向它撞去,黑云几次消失在水面上,但黑云最终又浮出水面。黑云终于跃上了冰排,蹲在我身旁。
我说,黑云,咱们就要漂到海里去了,多好!我把那双旱冰鞋扔到水中,它不该属于我。然后我抱住黑云。
河水越来越蓝,一口口吞噬着我们脚下的“冰岛”。我和黑云的故事发展到这地步肯定是最辉煌最壮烈的了。有一刻我又看河堤上涌动的人群。那里面肯定没有“鼻涕”。要是他在里边我还会认真地叫他一回爸爸的。“鼻涕”这个词不怎么好听。
我看见了蔚蓝色的海湾。海面上的薄冰一夜之间就化成了海水。有两只雪白的海鸟一直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是大海派来的欢迎使者吧。我和黑云开始摇晃,我和黑云与大海之间的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时从涌动的人群中跃出一条影子,狠狠地吼道:儿子!
我张望了一下,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爸爸。
然后,我脚下的“冰岛”便丧失了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