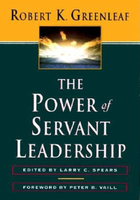黄队长,这么多年来,你步步高升,荣华富贵。外人看到了你表面的荣光,只有我知道你罪恶的灵魂。你坐在主席台上说的那些堂皇的大话,你自己何曾有一句相信。等着吧,我会一直纠缠着你,直到我的灵魂飘散。我会等着你,直到你受到应有的严惩。我要进入你的梦中,化为一条绞索,勒紧你的脖子。你害怕了吧。我知道,你的官做得越大,你的内心越不得安宁。不用去求神礼佛,你不敢对神说真话,也不敢对佛吐露真情。你还在家请道士,跳大神。那粘在壁上的黄纸,你以为真能镇住我心头的恨?我要进入你的梦境。看啦,你像狼一样尖叫,你从梦中惊醒,吓着了你身边的女人。
怎么啦?女人问。
做了个恶梦。你说。
你一身大汗淋淋。
我冷笑一声,在你的身上吹过一阵冷风。你打了个寒噤,对女人说你冷。
你知道这是我在纠缠着你。可是你不敢对你的女人言明。
作家,可怜的打工作家,你还在挑灯苦写到天明。你写吧,你怎么写,也无法让你的心安宁。
看看你写下了些什么吧,风花、雪月、温情。
你在回避什么?你依然是个懦夫。你假借李夜白的口为你开脱。你这个软弱的人,你的身体里没有男子的血性。面对暴力,你居然不敢向一个女子伸出双手,你居然不敢大喊一声:
不——
不——
不——
我知道,从那个台风之夜后,这一声呼喊,一直闷在你的胸腔,一直在折磨你的灵魂。
可怜啊,我的作家,那个赫鲁晓夫的鬼话,怎么能为你的软弱与无能找到借口?
你还是没敢真正面对你的灵魂。
你说,你不是张志新,你不是秋瑾,你只是一个,在文字里,把你的呐喊深埋的人。
这是什么鬼话?可怜的作家,你居然天真地以为,一次灾难,能改变我们的国民性?还是先改变你自己吧,让那些虚伪去见鬼,让你笔下的每一个字见你的本心。
啊,你流泪了!为什么?为了灾区的死者?
可是,你流过太多的泪,你的泪已流干。因为悲伤,因为感动。我知道,我知道了,你的心里扎下了无数钢针。
你看见了,你听到了,你想到了,那些丑恶的表演,那些被鲸吞的爱心,那些莫明其妙流出的帐篷,那些发国难财的人们,那些飘荡在灾区的人贩子……网络上到处流动着他们丑恶的嘴脸,他们的灵魂,将永不得安宁。
人们都在计较着那许多的小。人心小得像针尖。人心在针尖上舞蹈。
可怜的作家,可悲的人,你流泪了。你在打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你又看到了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
一个作家在你的QQ上留言,他说他只想做一个傻子,他什么都不想知道,他不想知道人世那太多的恶,他不想知道,这次地震还没有把人震醒。
不要怪他,麻木吧,麻木。
人性在灾难面前,有了短暂的复苏,又陷入了更深的深渊。
你们并没有被灾难惊醒。上天不过在给你们一次小小的演练,当末日的审判来临时,你们不至于如此的无能。相比这场灾难,我,一个小女子的冤魂,显得太轻,太轻。
作家,我亲爱的作家。我知道你的悲凉。我知道,你现在对国民性的改造,已失去信心。
你知道,贫富悬殊是人类灾祸的根源。
你知道,提高民族的精神境界,是一个写者的责任。
你在叫,你在喊,可是没有人听得见你的声音。
我的灵魂在夜色中飞行。
溪尾村,那是我永远的痛。
我俯瞰着身下的一切,那里的工业区,灯火通明。让我落下来,落下来。我的灵魂在夜幕下的工业区穿行。
终于到了下班的时候,许多工厂里都响起下班铃声。潮水一样,每一个厂门口,都涌出了灰色的人群。她们在谈论着今天的工钱,在指责某个领班的偏心。她们哪里知道,大批的工厂迁出了珠三角,珠三角在榨干一代人的青春后,不想为她们的后半生埋单。她们只知道,这时候,大排档里开始热气腾腾,一碗米粉,几串烧烤,一天的疲惫,在这一刻得以有了休整。电视里正在播放汶川的灾情。除非灾区有亲人,其他的人对此漠不关心。
幸福啊,现在的打工者。我当年打工时,这么晚还出来宵夜,绝对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现在的打工者,在深夜的大街行走不用再吊胆提心,神出鬼没的治安不再让她们失色惊魂。
我的灵魂在一个打工者对面坐下,她的脸上写着疲倦。
我熟悉她,她是打工作家王十月的二姐,作家在《寻亲记》中,曾写下他寻亲的过程。
现在,她还在做车衣工,从十八岁到三十八岁,流水线流走了她全部的青春,每天车出的衣服堆积成山,二十年车出的衣裳,可以连成万里长城。她在摊上吃了一碗两元钱的汤粉。吃完宵夜,她回到出租屋。我跟随着她,因为作家的缘故,我把她当成了亲人。她回到了出租屋,不见自己的男人。男人又在打牌,她清楚,寻找到牌场。
她对男人说,不要打了,回家去。
男人无动于衷。
她又说,不要打了,回家去。
男人还是摸牌打牌,对她的请求置若惘闻。
她这几天心情不好,米贵肉贵,房租又涨了一成。她上去推倒了男人的牌。这一下子,惹怒了男人。男人挥拳打向她的眼睛。这一拳,哪里还有夫妻情份。可怜的女人,此时唯有哭泣。她找不到倾诉的人。
我多想对她的男人说,珍惜眼前的幸福吧,想想那些在地震中瞬间破碎的家庭。可是她男人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只是一个离魂。
离开了她,我在那些亲嘴楼的楼道里飞行。一个酒鬼在楼道里大声喊叫。一间出租屋里,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正在吞食用身体换来的白粉。我知道,她,曾经是一个打工妹,也曾有着美好的梦。
我多想对他们说,珍惜自己的生命吧,想想那些在地震中瞬间消失的生命。可是他们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只是一个离魂。
我继续飞行。
我看到太多的冷。
我希望找到一些人间的温情。
我需要用温暖驱散围绕着我的寒冷。
我需要能量,让我的灵魂度过明天泥土里的凄清。
这么多年了,我的灵魂在渐渐消散。我曾经到过奈何桥,我见过地府的阎君。我放弃了再世为人的机会,我情愿做一个在阴阳两界间飘荡的离魂。阎君抚着长须,久久沉吟,小鬼们在一边狞笑:你的选择,将让你终有一天魂飞魄散,再也没机会投胎为人。
我说我不后悔,投胎之前的那一碗孟婆汤,让世人忘记了前生,让人不知道觉醒,让人不知道什么叫教训,依然是个糊涂人。
我的灵魂在小巷里掠过,一只狗发现了我,发出了汪汪的叫声。
我飘浮在一户人家的窗外。那对小夫妻,他们看上去感情很深。窗台上,晾着灰色工衣。曾经,灰色工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身份的背后写着两个字:打工。
我的灵魂继续飘荡,那小巷里,一家诊所,又挑起了我心头的痛。
十多年前,我就是在这样的小诊所里,失去了生命。那个所谓的医生,他告诉我说人工流产一点也不痛,他说宫外孕不是什么大病……我轻信了他的鬼话。
血崩,那么多的血……
那个所谓的医生吓得坐在地上。那张窄小的病床上,躺着的那个穿着灰色工衣的女人,鲜红的血染红了她的下身。好半天我才明白过来,那床上的人就是我,一个名叫北川的女子。同时,我也明白,自己成了一缕冤魂。
医生抛下我,逃之夭夭。我想去把他追上,让他还我生命。可是一阵风吹来,牛头和马面用索子锁住我,把我拉到了地府。阎王大笔一挥,生死簿上除了我的名,从此人间没有我这个人。
不——
不——
不——
我怎么叫也无用。
我的灵魂在高唱,每一个夜晚。可是你们却听不见我的声。
我拥有华丽的女高音,声音响彻云霄,在每一个黎明。
可是,你们都沉睡在梦中,怎么叫也叫不醒。
可我还是要大声歌唱,只有唱歌,才能排遣浸入到骨子里的冷。
啊~~~啊~~~啊~~~~~~~
可我还是要大声歌唱。
啊~~~啊~~~啊~~~~~~~
只有唱歌,才能排遣浸入到骨子里的冷。
第四乐章:男女声二重唱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这年的第二次台风,将在此日登陆。风雨欲来,小镇的天空已是黑云压城。中午已然若黄昏,路上少见有行人。冥冥中似有天意,十五年前那个台风之夜,李夜白跟着黄队长,在溪尾村犯下了此生难以赎回的罪。十五年后,当他重回溪尾村,欲赎回今生的恶时,又遇上台风来临。
走下大巴,李夜白感觉到了空气中弥漫的水汽。南方的记忆于李夜白来说,是潮湿的,如同他的心情。他站在镇中心的十字街边,脑子里渐次浮上了小镇十五年前的模样。
十五年前,李夜白尚是个青葱少年,从故乡来到南方。其时的小镇才刚刚开始开发,镇上的古老民居随处可见,沟港河岔密布,一条清澈的小溪绕镇东去。在李夜白的记忆里,溪尾村离镇中心尚远,地处偏僻,也没有几家工厂,零星散落在山坳里。坐巴士到得镇上,便没有了公车,若步行前往溪尾村,得半个小时。摩托佬们盘踞在十字路口,见有人下车,忽地一下就冲到你面前,靓仔靓女叫得亲热。路两边,很多绿得发蓝的细叶榕,根须从树上垂到地面,高大的大王椰间杂其间,或有数株木棉,把一树红花烧得如焰。经过一座小石桥,桥的年龄颇为古老。李夜白记得桥头有一座高大的石牌坊,上面刻着两个大字:棠溪。两边的石柱上,有一幅对联。对联的内容,李夜白已记不真切,只依稀记得有“一树紫棠”、“数顷梅花”的字样,让人对那时的溪尾、溪头二村,生出几许诗意的联想。过牌坊,两条路,一往左,一往右。往左去溪尾,往右去溪头。
如今,十五年过去了。李夜白再次来到这南方小镇。从公汽下来他还以为下错了地方。一问行人,说,是某某镇。千真万确,他是到了。他努力寻找记忆中小镇的样子,但举目皆是高楼。李夜白努力在记忆中搜寻溪尾村的方向,奈何实在分不清东西南北。叫了一辆摩的,问,去溪尾村多少钱。
溪尾村那么大,到溪尾哪里。
李夜白想了想,说,德基玩具厂。
德基玩具厂?在哪个工业区?
李夜白说,就是溪尾村工业区。
溪尾村有十几个工业区。
那……去溪尾村治安队。李夜白说。
十元。
李夜白坐上摩的。“日”的一声,摩托车拐进一条巷子,又拐进另一条巷子。不一会功夫,摩托佬说,往前走过这条巷子,治安队到了。
李夜白说,你送我到治安队门口。
丢,找死啊,现在禁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