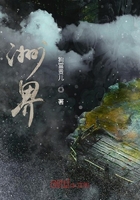实际上,人并非生来就是自由的。由于人掌握了那种使他们有可能控制自己命运的理智的工具,人才得到了自由。这些工具就是来自过去经验的知识和理智的方法。因此,追求自由的教育需要过去经验的知识。因为过去的经验曾经受到过反复的检验,所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就能产生获得自由的工具。
教师的伟大的和令人敬畏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操纵客观条件以帮助学生学习。教师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工作的;而且社会允许他行使这种权力。这就规定了教育的指导原则。于是,具有教育作用的经验就是有助于成长的经验,就是指导人们前进的经验,就是能够增强人们控制未来力量的经验。这样的力量就是自由。真正自由的基本条件就是要理智地运用这种力量。自由的人就是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及来自过去经验的知识来作出决定。所以教师在建立学习情境时,他首先需要关心的是,务必利用知识来解决问题,而所谓知识就是建立在过去经验基础之上的有实际用途的概括。
因此,有责任感的进步教育理论家显然不赞成打着教育的旗号进行任意的、没有指导的、没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强调,进行经常不断的、批判性的选择乃是教师的职责。事实上,杜威竭力要说明,坚定不移地强调批判的选择乃是进步教育最可宝贵的地方。因此,新的经验必须始终是与以前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学习必须是有组织的。各种经验必须有意义地互相联结在一起。必须把新的对象和事物看成与先前的经验有关系,有联系;而且新的对象和事物是从先前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
有人设想,只要给学生一些新的经验并注意使他们掌握较多的技能和能力去应付那些他们已经熟悉的事物,就足以实现在经验的基础上导致某种不同的东西的原则,这种设想是错误的。新的对象和事物必须通过理智与早期的经验关联起来,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要有意识地把事实与观念联系起来并取得进展。..在成长中把有关的事物联结起来,这就是他(教育者)要经常注意的事情。
如果“新教育”哲学家们的系统主张已在前面得到了适当的论述,可能要产生这样一些问题:它们是否事实上和进步教育决裂了?
为什么要重视教材?为什么要强调组织观念和掌握知识的重要性?
我们还要证明,尽管这种观点和儿童中心教育有差别,它仍然是同受文艺人文主义传统长期影响的传统教育相对立的一种教育理论。
“需要”的客观性这种观点认为课程应该以需要为根据;但是,对于“需要”这个概念的解释却与以前传统教育说法很不相同。首先,必须十分认真地考虑外部世界固有的限制和控制。思维活动是在一个其本身不是由思想所构成的环境中进行的。这不是一种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把经验看作与具有强烈限制作用的外部世界没有关系的东西。外界存在着杜威所说的“没有理性的实在物”,我们就生活在其中,并在它们之中成长起来。有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生活着的人不时被卷入一些不完善的、纷杂的、不稳定的情境之中。如果缺吃少喝,这个情境可能就不完善;当在车辆拥挤的时刻交通被堵塞,就会纷纷扰扰,这个情境可能就动荡不安。
他们认为,这些有问题的情境就构成了需要,需要就引起探究。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这里所谈的需要已不是狭隘的个人需要了。情境变成具有需要的性质了。虽然人是环境的一部分,但需要并不是以某种方式深埋于人的身体之中;需要存在于环境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有机体的内脏。
因此,问题是由情境产生的;人是这种情境的一部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每一种情境都有它的历史。此外,在一个变化的、能动的、进化的世界中,每一个这样的情境都有它的未来;它必定会变得和它在“此时此刻”的情况不同。这样,我们就要从动力方面,从发生方面来理解需要、具有需要性质的情境和有问题的情境;也就是说,需要乃是通过过去和现在走向未来的一个过程。
有一种观点认为,严格地说,需要说是教育的基础;探究发源于需要的情境。于是,任何探究过程都是在事物发展的承袭关系中开始的,而这种承袭关系的重要成分则是由过去的事物构成的。因此,我们就必须认知一些有关情境的事情;而且,由于别人也和这个情境有牵连,所以,就有可能进行合作---那就是说,人们可以进行共同的探究。探究的成果就是知识。让我们概括地重述一下:教育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需要存在于环境之中,它不是单纯地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人体之中;于是满足需要就意味着改造情境;改造情境是通过探究而获得成功的;探究又产生了有利于进一步探究的知识。
那么,我们是怎样探究的呢?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为了进行探究和获得知识,采用什么工作程序我们才能获得丰硕的成果呢?
可靠知识的获得如果事实材料和受干扰的情境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那么,这些事实材料就是无用的。但是,事实材料和产生这种材料的外部现实又不是完全一样的。事实材料是获得知识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它们是据以进行推理的原始材料。这个论点涉及的面显得比较专,但是它和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关系。我们一直认为,摆出事实材料是探究的基础。只有当我们获得这些事实材料时,儿童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如果我们不收集资料,我们就决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开始我们的教育工作。这就要求进行有条理的、精确的和认真的研究。只有当我们所使用的教材是建立在为满足儿童的需要而对事实材料进行了系统阐述的基础上时,儿童和青年人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换句话说,关心严密的、足够的基本知识和“满足青年人的需要”,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
在问题情境或不确定的情境中,这种把事实材料摆出来的过程便构成了意义。当一个受困难情境所纠缠的有机体,或者通过外部的行动,或者通过头脑里的想象,努力摸索以改造情景时,意义也就产生了。这种“摸索”是受那种已成为半成品的事实材料指导的。
在确定和收集事实材料之前,任何“摸索”都是盲目的、不理智的、不自由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在事实材料指导之下开始“摸索”,才能够产生意义和进行解释。
用来改造环境---摆脱交通堵塞,使吃、喝得到保证---的资料和意义就产生了知识。因此,需要是从一个总的情境产生的。需要不是狭隘地属于个人或私人的。一个受到干扰的或不完善的情境就表明需要有人去进行调查和计划,然后去检验这个计划能否改造情境。最后,所谓知识就在这种“需要---资料---意义”的背景中产生出来了。我们所谓的知识乃是一个经过检验的结论体系,而这些结论是从过去的经验里筛选出来的。知识就是建立在资料和意义的基础之上的,探究者在问题情境中运用这种知识从而对它进行了检验。那就是说,知识已经受了实验验证。认真的探究所产生的结论,在进一步的探究中是受到尊重的。既然所有的情境都受到过去影响,既然生活的本质乃是一种社会经验,那么,一个绝对没有经过探究的问题情境是不可理解的。因此,认真的探究必然会在学识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从过去的探究中所得出来的假定或原则是进一步探究的源泉。杜威教授认为,原则就是从先前的探究中产生的经过检验的工作方法,这种原则,从它的作用上来讲,是在进一步探究之先就已经有的。
如果情况确是如此,那么,当学生由于缺乏知识而不能从事某项探究时,教师的确是不愿编制一些把学生引导到这个探究领域中的教学单元。如果事先没有原则,那么,那些忽视理论与历史背景重要性的经验单元就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
虽然如此,在本文中我们并不是单纯地重新叙述一下古典的教育传统。按照这种观点,人类的经验乃是自然和进化过程的一部分。
思想被看成是一种增进人类健康和社会福利的工具,而它本身并非是“至善”的。理智生活的作用是洞察未来,并为未来的行动作出假设;对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进行思索,只有在为未来的行动作出假设时才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的理想是对于变化中的现在进行能动的改造,而不是完善地叙述和冥思绝对的实体。智慧的作用是解决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生活中实际面临的问题。
这就是说,应该建立一套学校课程来应付那种紧张、迫切、混乱的经验情境。制定课程需要有标准。如果适应生活意味着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生活而改造被破坏了的生活环境,那么,适应生活就不是一个不适当的或低劣的教育目标。我们应该考虑那些需要考虑的事情。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希望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构造未来。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对未来的期望,决定了学校课程的内容。在建设未来的事业中,我们手头上所有的最强有力的资源就是我们手头上所掌握的资料、意义和知识。
这些蕴藏的资源是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遗产,我们就是根据目前的需要和对未来的希望从这些资源中进行选择的。根本不存在某种过去流传下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材内容。知识不过是解决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提出对未来的希望的工具。
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是固定不变的。在把知识作为工具使用的过程中,理论是有所变动的,而且变得日益精密。来自过去的知识经常受到现在的改造。通过批评使知识精益求精,其结果最终就能把有批判根据的意义同梦呓和空想区别开来。这就是说,经验只有在根据它的背景来理解时,才富有意义。一个论点、一种思想或一个科学的概括,除非追溯到产生它的根源并弄清它过去之所以产生的目的、利害关系和意图,否则是无法理解的。此外,过去还提供了一定的可靠的概括或受过检验的观念。这些概括或观念是探究者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他必须掌握这些工具去认识和尊重这些真理。
这样的真理保证人们能够支配它们。然而,这些真理并不是绝对的,而且它们也不是永恒的。它们是有限的,而且它们总是要受到批评的。
有一点应该弄清楚:虽然实验主义者接受了进化论,否定了形而上学的绝对论,而且运用了实用主义的检验方法,但他们并没有否认某些受过检验的观念应该享有相对持久的地位。实验主义者不赞成探究者对所有的共相采取怀疑态度。肯定地讲,他们并不认为所有过去探究的结论都应该不断地遭到怀疑。相反,他们的观点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科学的概括,应该承认它们是人类探究的产物,而不是永恒的启示。同时他们认为,过去探究所得出的相对持久的结论必须经过不断的修正和修改。新的发现将不断地冲击着科学的概括。过去总是走向未来,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不会停留于现在;它将继续走向未来,在未来总会出现新生的事物。虽然新出现的情境决不是全新的,但其中可能有一些新鲜的因素。新的情境留有过去的痕迹,但在新的情境里,存在着以前没有探索出来的部分。应该尊敬和重视从过去探究中得到的原则,但是,即使是最受尊重的真理---我们之所以尊重真理,是因为它们是可靠的---也必须根据目前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仔细的检验。说它们是不变的,这只是相对而言。当最古老、最可靠的真理被当作解决当前问题的工具而使用的时候,也要对它们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改。
道德秩序的来源虽然科学包括教育工作的范围,但如果科学只涉及事实而不涉及价值,那么,靠什么来支持道德教育呢?靠情感吗?靠风俗习惯吗?
当教师向青年人传授科学的思想习惯时,他们肯定会提出一些有关价值的批评性问题。不管怎样,当我们教育他们要批评所有的东西,要检验、审查、试验所有的主张,暂时性地接受一切命题,而在出现了新的证据后要随时改变它们时,学生也会提出一些有关道德准则的问题。因此,为什么我们应该重视人生?为什么要说老实话?为什么要与人合作?或者,为什么要拥护宪法?在一个致力于把青年人教育成为敢于提出批评的、有理智的人的学校里,将会提出这类问题。
道德的约束力似乎只是以某种形式的自我利益为基础的。当然,自我利益可以扩展成包括“我的家庭”、“我的种族”、“我们一伙人”以及“我的国家”的利益;但是,科学的人文主义者是否可以把自我利益扩大到包括人类所有的利益,这恐怕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个人要为人类去过一种痛苦而艰难的生活?
为别人经受十年或二十年苦难,指望由于自己受苦而对将从其中得到利益的集体事业作出贡献,因而自己最终也能得到更大的欢乐,这种想法有人也许认为是可取的。然而,根据这个观点,似乎没有理由为了某种高于个人本身利益的事业而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
在漫长的教育史上,进步教育似乎表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道德热忱,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况。当支持进步教育的哲学把自我利益提到这么高的程度时,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曾经有过一种解释,认为参加这个运动的教师是一些妇女,他们热爱儿童但又没有自己的孩子,因此,儿童中心学校准则中反映出的那种对于儿童时期的天真想法迷住了她们。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个运动的道德热情来源于基督教;那就是说,当基督教的形而上学方面的内容被抛弃时,作为文化上的一种落后现象,基督教关于爱的基本道德继续保留下来了。人们引证了一些例子:博德和杜威都出身于基督教的卡尔文派,这种哲学的某些比较着名的解释者都是福音派新教培养出来的。
这些说法没有考虑到人们在各个时代表现出来的对人类自由事业的那种可以理解的献身精神。在自由传统中,进步教育充其量仅占有一席之地。它赞成理智上和道德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在人们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而形成他们自己的判断标准时产生的。这种运动中的道德热情产生于对人的伙伴的同情,对压迫人的暴力的愤慨,以及对他们的解救之道的清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