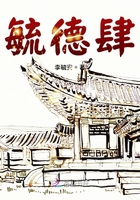50时过境迁,我和尹莉莉一直都把姥姥的传奇经历当作一个谜。姥姥临终之前对肖若聪的坎坷经历还有种负疚感。我想,这也许是她后来一直拒绝搬回古宅去住的一种情愫吧。那一年,我和莉莉在古宅的那间屋子里徘徊了许久,谁也找不出一句恰当的句子来评说它
都说古宅的风水硬,谁染指上了,不倒霉破财,也会碰到憋气窝火的事。李宜龙这一阵子的气就不太顺。日本人倒是不大找麻烦了,可后院又起了火。先是雨薇背着家人要去延安投奔共产党,让闵香莲赶到车站硬给拽了回来,结果雨薇躺在床上大病了一场,害得他到处寻医问药。偏偏这会儿,杨莹娇这边又生出事端来,这个外表温顺贤良的姨太太居然也敢在外边打野食和野汉子幽会。
起初,他还有点不大相信,让梁云贵再去探访一下。他转了一圈,跑回来说,这事千真万确,整个辽城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不过在瞒着老爷您一个人了。
李宜龙勃然大怒。把杨莹娇关在屋子里痛打一顿。莹娇起初还不愿承认,只是跪在地上哭哭涕涕,可终究禁不住再三逼问,只好以实相告。原来这个小骚货早就同那个姓牛的小子有染,而且还打过胎。他刚回来那会儿,她倒装得挺像,夜里没少向他献殷勤,还说些让她想死了之类的乖巧话。没想这个身子白白嫩嫩,模样酷似天仙的美人竟让他带上了绿帽子。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要是往上推十年,他一定会让那个姓牛的和肖若聪一样的下场,可眼下毕竟时过境迁了,他不能把姓牛的怎么样,也就只好冲姨太太发泄了。令他百思不解的是,那个牛铁山生得傻大憨粗,走起路像个蠢货,莹娇究竟看上他哪一点?他逼问莹娇,她不作答,只是呜呜哭。
“你真是个不值钱的贱货,找野男人也不选个模样好的,偏要找那个车轴汉,他给你插上,你就舒坦?”
香莲起初没介入这件事,只是心里暗暗骂莹娇没出息,怎么还敢偷偷与那小子来往。后来是柳眉看不下眼,跑过来说:“太太,你去给二奶奶说说情,她也怪可怜的。”
“活该,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光我说情又能顶什么用。”
“太太,您就劝劝吧,老爷的脾气您知道,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这话提醒了香莲。她不禁想起当年她和若聪的事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心中不由生出恻隐之心。她匆匆走进老爷房里,见他正揪着莹娇的头发逼问她同牛铁山发生过几次关系。莹娇哭得像泪人似的,见到香莲就犹如见到了救星,可怜兮兮地喊道:“太太,快来救我!”
香莲对宜龙说:“老爷,事情既然已发生了,我看就没必要叫那个真儿了,以后严加管教就是了。”
“不行,这回我非要狠狠收拾她一顿不可,这个骚女人坏了我李家的门风,我决咽不下这口气。”
香莲没好气地说:“这话可得两说着,你当初拍拍屁股就走了,把一个大家扔给两个女人。你一走就十年,莹娇她耐不住寂寞,做出点出格的事,也是情有可原的,你就不能暂且饶过她这一回?”
李宜龙放下的莹娇,气不打一处来地说:“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初你和姓肖的那小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我不知道!”
她顿时火了:“李宜龙,你不要消停两天,心里就难受。咱们还有笔帐没算呢,你不要以为我好胡弄!”
李宜龙话一出口,便有点后悔了。在肖若聪的事情上,他做得是有些过分,况且因为他,肖若聪才失去了做男人资格的。于是他又改口说:“我在教训莹娇,你来插什么嘴。”
闵香莲咬牙切齿地说:“好,这事我不管了,看你的这出戏怎样收场。”她说完将门使劲一摔便出去了。
当晚,莹娇在房梁上了吊,幸亏柳眉发现得早,她才捡下了一条命。李宜龙害怕这事传出去,便把家人和佣人召集到一起,再三吩咐不得走漏风声,然后又以养病的名义将莹娇转移到一个窄小的厢房里,每天让柳眉往里面送饭,并搜走了一切能够自杀的用具。
莹娇的事发后,好长一段时间,香莲都懒得和李宜龙说话。这不光因他的话刺伤了她的心,而且还有若聪的因素。他离开满铁事务所之后,一直没正当的职业,绫子又不肯放过他,三天两头找他的麻烦。他在沈阳呆不下去了,便跑回了辽城,住在了亲戚家中。
肖若聪本不想惊动香莲,可不知怎么的,偏偏露出了口风,传到李宜龙的耳朵里。一天吃晚饭时,他便把这个消息有意无意地透露给了妻子。香莲表面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却产生见他一面的欲念。她私下将柳眉叫到屋里,把心思说了。柳眉怕得不行,担心这事要让老爷知道了,没好果子吃。
香莲说:“你怕什么?有我呢。你只需把他领到我指定的一个地方就行了。”
柳眉无奈,只好照太太的意愿做了。香莲所做的这一切都没能瞒过李宜龙的眼睛。他见柳眉从香莲的屋里出来,慌慌张张的样子,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鬼。于是,他便打发人跟在她的身后。时间不长,下人跑回来报告说,柳眉和那个姓肖的一道去了一家旅馆。
李宜龙暗暗骂道:“这个小婊子也学会拉皮条了。”他于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到香莲的房间,见她正在梳妆镜前打扮。
“怎么,想出门呀?”他故作惊讶地问。
香莲正欲出门见宜龙突然闯进来,心里别提多别扭了,便没好气地说:“我在屋里闷得慌,想到外边转转。”
“柳眉呢?要不要让她陪你走一走哇。”他故意殷勤地说。
香莲听他话中有话,不免担心起柳眉来,偏偏这会儿,她急匆匆从外边赶回来,冒冒失失地嚷道:“太太,人我给您请了。”
香莲暗暗叫苦,便恼火地说:“你穷嚷嚷什么!”
柳眉撩开门帘,猛然发现老爷在屋里坐着,脸顿时吓得变了颜色,不禁往后退了一步。
“柳眉,你刚才说的什么?”李宜龙压抑着怒气,不动声色地问。
“我……”柳眉直勾勾地看着太太,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香莲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她冲柳眉使了个眼色,并骂道:“我让你给薇儿请个大夫,你一去就是半个时辰,那人呢?”
柳眉才如梦方醒,忙说:“太太,人家大夫说是坐诊,不上门的。”
他暗暗骂道:“这个柳眉也学会跟太太蒙我了。”但他又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
让香莲下不来台,便说:“薇儿整天呆在屋里还能没有病,让她多晒晒太阳就行了。”说完,他便若无其事地走出门去。
柳眉忙将肖若聪去旅馆的事悄声向太太说了。香莲犹豫片刻,觉得还是不能让李宜龙抓住把柄,就决定不去了。
“肖先生会等急的。”柳眉担忧地说。
“顾不得这么多了。”她说,“老家伙的鼻子比狗都灵,得小心点。”
就这样,肖若聪在旅馆傻等了半天也没见香莲的影子。他疑心香莲在有意耍弄他,一气之下便离开了辽城市。
此时,还有一位女子在寻找他。她就是若聪在日本京留学时,他的导师村田教授的女儿静子。静子与若聪一别十三年,几乎杳无音信。开头几年,静子给若聪不知写过多少封信,都没有回音。她不知偷偷落过多少次泪。无奈之中,她嫁给了中学时的一位同学。
他的家境不错,父亲是京都的银行家,人长得也很帅。谁知,她婚后才发现丈夫是个到处拈花惹草的纨绔子弟,结婚还不到一年,就另有了新欢。对静子动辄就拳脚相加。有时一连十几天都夜不归宿。
静子在生下一个女孩不久,便给丈夫抛弃了。没有办法,她带着女儿又搬回家里。父母见女儿落得这般境遇,也只能是唉声叹气,毫无办法。如今的女儿,长到了十岁,性情温和,酷似静子。她们母子与家人相依为命,生活不愁,只是静子在感情上一直无法割舍与若聪的那一段未了情,整日闷闷不乐,过早地生出许多白发。
村田教授理解女儿的心思,一日将她叫进书房,将一封写给满铁小野副总裁的信交给静子说:“如今是日中交战,人民受苦。日本战败是早早晚晚的事了。我看你趁日本人还控制着满州,去找肖若聪去吧,我听说他现在还孤身一人,再晚,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静子充满感激地接过父亲的信,登上了去大连的客轮。她来到中国的东北,见到已提前退休的小野先生,才得知若聪已离开了满铁沈事务所。她有点失望了,这偌大的东北,哪里去找他呢?她哀求小野说:“请您一定帮我找到这个人,否则,我就不能回去,拜托了!”
小野听了静子的一番哭诉,不禁为她的真情所感动。他说:“静子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你。”
小野动员了他所熟悉的朋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若聪的下落。但反馈的消息都很令人失望,肖若聪离开满铁之后,居无定所,四处流落,谁也不知他的准确去向。
静子两眼望穿,但却没有消息。她几乎绝望了。恰在这时,他又回到奉天,结果一下火车便给攥着他相片的日本宪兵抓住了。
若聪不明真相,大声抗议。宪兵却出人意外的和气,并将他径直送往日本人开的大和旅馆。当身穿和服的静子小姐出现在若聪面前时,他惊愕得目瞪口呆。他实在弄不明白这究竟怎么一回事。
“若聪!”静子不顾一切地扑过来,依偎在他的怀里,泪水止不住顺着她的双颊流下来。她已下定决心,这次死也不离开若聪了。
肖若聪这些年也一直牵挂着静子。他只是不愿静子知晓自己难以启齿的往事,也不愿给她带来心灵上的痛苦,所以他才选择了回国,并坚持不给静子回信。当静子泪眼站在他跟前时,若聪意识到自己先前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他情感的大堤已经出现了裂痕。在静子踮起脚尖狂吻若聪时,他也动了感情。他双手捧着她的面颊,叹息道:“世界这般大,你为什么偏偏千里迢迢跑来找我呢?”
“若聪,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吗?”静子哭着说,“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想起你,没有你,我会死的。”
若聪眼泪也籁籁地落下来。他声音颤抖地说:“静子,你是不知我的苦衷哇。”
“你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尽管说,我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若聪顿时痛哭起来,哭得是那般伤心。他声音颤抖地说:“我不能告诉你,你心里会承受不了的。”
“说吧,我挺得住。”她安慰道。
“我——我不是个男人。我是不能在那方面满足你的。”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说出了这句难以启齿的话。
“不,你是在骗我。”静子并不相信他的话。
于是,若聪便将三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讲给了静子。静子起初还能屏住呼吸听,听着,听着,她的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往事太难以令人置信了。先前的若聪在她心目中是那般完美,她何曾想到,他在来日本前还曾有过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静子猛然声嘶力竭地喊道。
她只觉天旋地转,仿佛天要塌下来一般。她朝前走了两步,两腿一软便摔在地板上,昏厥了过去。
“静子!静子!”若聪将她抱在怀里,失声地喊道。
也不知过了多久,静子才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若聪的脸,喃喃地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呀!”
若聪道出了这一切,心情反倒平静了许多。他后悔向静子隐瞒了这么多年,害得她千里迢迢跑到东北来。他太有愧于静子了。
“静子,是我对不起你,我也没有资格得到你。我已年过五旬,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让我们永远做一个好朋友吧,我会永远记住你的。”他动情地说。
“不,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你。”静子在经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做出了这样的诀择。
“那怎么行,这岂不太苦了你。”若聪执意不从,不愿让人怜悯。
“若聪,我想好了,两个人相爱,绝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关系。尽管你没有了性生活的能力,可我们依然可以相依相伴,有你这个人在我身边,我也就知足了。”
若聪给静子这情深意切的话语深深打动了。中日两国仍在打仗,但这也不能割断中日两国人民的情谊。他情不自禁地将静子又一次搂在怀里,用颤抖的手摩挲着她的秀发。他感到静子的气息打在他的脖子里,静子的头发撩动着他的面孔。他俩相互依偎着,屏住呼吸,相互倾听着对方心脏的跳动。
“静子,如果你真想和我在一起,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请求。”
“你说吧,我答应!”静子毫不犹豫地说。
“跟我留在中国吧。”
静子不禁一愣。她显然对若聪提的条件缺乏心理上的准备。在来中国前,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让她一定要把若聪带到日本。
“这很重要吗?”她试探着问。
“十分重要。”认真地说,“我不愿在一个屠杀中国人的政府眼皮底下生活。”
静子沉默了。她放开揽在若聪腰上的手,慢慢走回到椅子旁。
“你就那么痛恨我们日本?”她忧郁地问。
“不是日本,我痛恨的是日本的军阀政府。”他纠正道。
“如果有一天这个政府倒台了呢!”
“到那个时候,我可以重新考虑我的决定。”
“那好,我答应你!”静子说,“但我要把我的女儿接过来。”
“应当是我们的女儿,虽然我不是她的生身父亲。”
“对,我们的女儿。”
几天之后,静子回国将女儿接到了中国。没过多久,若聪和静子便在这个城市消失了。他们身边的人谁也说不清他俩究竟去了哪里。有人说,他们去了大兴安岭林区,也有人说,他们去了人烟稀少的科尔沁草原。
闵香莲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时过境迁,我和尹莉莉一直都把姥姥的传奇经历当作一个谜。姥姥临终之前对肖若聪的坎坷经历还有种负疚感。我想,这也许是她后来一直拒绝搬回古宅去住的一种情愫吧。
那年,我和莉莉在古宅的那间屋子里徘徊了许久,谁也找不出一句恰当的句子来评说它。
听母亲先前讲,这间屋子便是早年姥姥与肖若聪的幽会之处。也就是在这屋外的院子里肖若聪被官府的人五花大绑地推出去,不容分说便给阉割了。其实,他们在屋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尹莉莉推开古宅的一道门,惊愕地说:“诗剑,我怎么好像听到里边有人喊似的,怪瘆人的。”
我说:“你别这惊惊乍乍地好不好。”
她说:“还不是让你姥姥家的那点臭事给搅和的。一进古宅的大院,我就有种别样的感觉,只觉阴森森的。”
那年,恰好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十周年,双方相互庆祝之时,也传来一些不合谐的声音,围绕钓鱼岛主权和教科书问题,日本国内极少数人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招致中国人的强烈愤慨。
尹莉莉有强烈民族意识。她说:“你姥姥幸亏没嫁给姓肖的,否则,我都会为你感到羞耻。他逆来顺受,太缺乏一种民族精神了。”
我不以为然:“我不这样看,不管怎么说,肖若聪还是一个对中国有很深感情的人。尽管战后他和静子去了日本,还加入日本国籍,可他日后回大陆还不忘投资办企业,捐资慈善事业,毕竟还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她冷冷一笑,说:“也难怪,从人性的角度讲,人们往往会同情弱者的。”
“也不尽如此吧,”我说,“有些事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我姥姥当初对肖若聪一见钟情,应当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只可惜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为阻碍了他们的爱情。爱情就是这样的奇怪。他在心爱的女人面前,总欲把事情做得漂亮些,可往往事与愿违,这就只能怪老天没长眼了。”
“嗬,你什么时候信起天命来了,怪不得你处处与我作对,原来是想反其道而行之啊。”
她自做聪明地笑了起来。
“哎,别把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瞎联系,好不好?我有些不满地说。”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你就拿这个古宅来说吧,许多人都在里边住过,但各自的命运又不尽相同嘛。”
尹莉莉叹了口气:“诗剑,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古宅,真的像是一本书,就看你怎样去读了。”
“深刻!”我不禁慨叹说,“难怪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