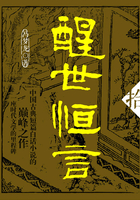闵香莲听到这久违的声音,差点没昏了过去。她万万没有料到他会找上门来。一别二十一年了,她只是从女儿雨霖的口中才知道他在沈阳城里做事。记得那天晚上,她失眠了。她恨那个负心的情郎,居然一走便没了音信,可她又无法忘掉他。这些年里,肖若聪的影子在她的心目中始终也抹不掉
雨霖随家人一道被迫迁出了大宅,重又搬进李宜龙先前的房子里,生计也成了大问题。宜龙商行和城里的几个分店都让日本人查封了。雇来的帐房和伙计见老板跑了,都作鸟兽状,一哄而散。他们临走时,免不了拿些值钱的东西做盘缠。香莲和莹娇也没办法,只好眼睁睁地看商行破了产。她们先前养尊处优惯了,如何遇到过这种狼狈的日子,真好像天塌下来一样。
好在香莲和莹娇还都带出来点私房钱,搬家后,又将这长年失修的房子拾掇一番,添置点物品,这家才像个样。但是,没有男人的家又是不能称之为家的。香莲、莹娇、雨霖、雨薇连同佣人柳眉五个女人处在乱世之中,总免不了要受到外人的欺侮。三天两头的,便有兵痞流氓找上门来,寻衅滋事,想占女人的便宜,吓得一家人整天关门闭户,除非不得以,连街都不敢上。
闵香莲自从上次受了刺激,心情一直不好,时常躲在房里独自垂泪。杨莹娇是个没有主见的女人,遇到这种场合,也只能唉声叹气。李雨霖没料到逃出了魔爪,又陷入虎穴,一天到晚也是提心吊胆的。她们就是这样度日如年地过日子。
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晚上,几个女人已上床躺下了,有一个黑影逾墙入院,悄悄走近香莲的窗下,轻轻地叩了几下窗户。香莲此时刚将灯吹灭,还未入睡,听到动静,心吓得怦怦直跳。她一把将被子蒙到头上,浑身打起哆嗦来。
她以为又是那个黄毛找她麻烦来了。前两天,他就借查寻李宜龙音信之名来到这儿,并对她动手动脚的。香莲忍无可忍,霍地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把剪刀,对准自己的心口说:“你要是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死给你看!”
黄操见状,只得罢手,临出门时说:“你这是何必呢。李宜龙把你丢下就走了,你年纪轻轻的,就能守得住活寡?真是想不开。”
香莲气得躺在床上哭了大半天。
外边的人又敲了两下,见里边的人不应声,便低声说:“香莲,别害怕,是我呀。”
闵香莲听到这久违的声音,差点没昏晕过去。她万万没有料到他会找上门来。一别二十一年了,她只是从女儿雨霖的口中才知道他在沈阳城里做事。记得那天晚上,她失眠了。她恨若聪这个负心的情郎,居然一走便没了音信,可她又无法忘掉他。这些年里,肖若聪的影子在她的心目中始终也抹不掉。她清楚,如果没有她,若聪也不至于混得那般惨。一想那会儿,他给人五花大绑地从她身边带走,她就感到无地自容的内疚。
她急忙披上衣服,从床上跳下来,撩开窗帘,借着月色,见到了那个男人焦躁地在院子里打转转。她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眼泪随即从眼眶中滚落出来。
二十一年前,在辽城郊外的那天傍晚,她就是在这个男人怀抱里,滚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而后,不管时间怎样流逝,她的心灵深处都清晰地留下了岁月的梦痕。她想去给他开门,又恐惊动临屋的莹娇和雨霖,只好将窗子打开一道缝,压低声音说:“若聪,你来这儿干什么?”
他惊喜地说:“我可找到你了。”
她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冷冷地说:“你走吧,我不愿见到你!”说完欲将窗户关上。若聪忙用手将窗扇顶住,急切地说:“让我进来吧,我有话对你说。”
“不行。”她嘴上虽这样说,可口气已软了许多。多年不见,若聪好像还没有变。不同的是剪去了当年拖在脑后的辫子,梳上了分头;脱去了长袍马褂,换上了西装革履,人显得更有风度,更精神了。
若聪看出了她的心思,又说:“你知道我为你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吗?”
他的这话戳到了香莲的痛处。她的鼻子一酸,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害怕让他看见,就急忙把脸背了过去。
若聪趁这功夫,推开窗户,跳进屋来,随手关上窗户,又将窗帘拉上了。他站在香莲的跟前,在黑暗中虽看不清她的脸庞,可也能体味到她此时此刻的心情。这些年,他丧失了一个做男人的权利,但他并没有丧失一个做男人的情感。自从那天在沈阳北陵见到雨霖后,他那颗僵死的心又开始复苏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已经长得这般大了,而且在许多地方还那么像他。于是,他便开始筹划这次与香莲的会面,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恰好这次,他受山田所长的指派,有一次到辽城出差的机会。他抽空回家一趟,方得知香莲一家的近况,悲叹之余,他愈发产生了同香莲和女儿见上一面的欲念。他一把拉住香莲的手说:“你们家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很替你们娘俩担心。李宜龙这样做,有中国人的骨气,就这点我自愧不如,我也佩服他。可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他毁了我的一生,我迟早是要报这个仇的!”
香莲猛地将手从他手上抽出来,厉声说:“我不许你这样做!李宜龙就是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也不该这样做。”
“你说什么?”他两眼通红,又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说:“你知道他是怎么坑我的吗?他可把我害苦了!”
香莲觉得莫名其妙,说:“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你何必还这样耿耿于怀呢?”
“耿耿于怀?”他忿忿地说,“我恨不得马上就杀了他!”
她警觉起来,问:“你深更半夜到我这儿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的?我请你不要落井下石。”
“香莲,你变了,”他失望地说,“当年你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若聪,我们都是过来的人,还有必要为过去的恩恩怨怨劳心伤神吗?再说,现在我们家的处境又是这个样,你就别再添乱了。”
“香莲,你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吗?我像是一条丧家狗一样,东奔西窜,一晃都二十年了,连个家都没脸回呀。”
“你这不是已经回来了吗?”她说,“我听雨霖说,你在沈阳给日本人做事,这次该不是帮日本人来找李宜龙的吧。”
若聪的心一惊,忙说:“站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不过,我还是有颗中国人良心的,上次的事,雨霖一定给你讲了,我给日本人做翻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好啦,”香莲这会儿对若聪猛然生出一种厌恶的感觉,“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就走吧,让人看见了,多不好。”
“香莲,你就这样心狠,连女儿都不让我看上一眼!”他一把拥住香莲的身子说。
香莲挣脱着说:“我的女儿不愿见到有一个给日本人干事的父亲。我求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给她。”
“不,我要让世人都知道,我是她的父亲。”
“你疯了!”香莲急了,忙用手去捂他的嘴。
这时,门突然开了,雨霖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她面对惶恐的两个人平静地说:“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倒很想认识一下我的这个生父。”
他俩都怔住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屋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雨霖这会儿,也认出了若聪就是她在沈阳两次见过面的那个男人。她恍然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原来是同这个男人联系在一起的。
她走到肖若聪的跟前说:“我倒想问上一句,你有什么资格做我的父亲?我又有什么理由做你的女儿呢?”
若聪听了这尖刻的话语,脸色羞得通红。他没想到他们父女会是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场合中相认的。他想解释一下,便说:“雨霖,我是对不住你,这么多年,我连一块糖也没给你买过,连一块花布也没给你扯过,可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呀。当年,是李宜龙拆散我和你娘的姻缘,又设计将我抓起来,我受的那份痛苦,你是想象不出的。……”讲到这儿,他的嗓子哽咽了。他让人像牲畜那样阉割的场景,又不寒而栗地闪现在眼前。
“别说了。”香莲此时也让往事触痛了心灵。她挥了挥手说,“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想带走我的女儿。”若聪说,“我要用我的后半生来补偿我对她的爱。”
“笑话,我为什么跟你走,让我也当汉奸吗?”雨霖尖刻地说。
“我不是汉奸。”他辩白说,“我给日本人干事,只不过是为了养活我自己。”
“天方夜谭,”雨霖嘴角浮出一丝冷笑,“老鼠偷粮食,也是为了养活自己,农民种粮食,也是为了养活自己,你是属于哪一类呢!”
“雨霖,不要这样说话。”香莲说。
她的言外之意是,他毕竟还是你的生身父亲。可雨霖却不以为然,尽管他曾在沈阳的旅馆帮过她,可她依然认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不该给日本人做事的。
肖若聪失望地离开了香莲的家。他先前的设想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闵香莲对他是那般冷淡,和二十年前判若两人。女儿不认他这个父亲不说,还讥讽了他一通,让他羞愧难言。他失魂落魄地走进一家酒馆,直喝得酩酊大醉,才跌跌撞撞走回自己的住处。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赶火车离开了辽城。
若聪走后,香莲的心情也颇为不平静。不管如何说,她同若聪毕竟有过那么一段耳鬓厮磨的恋情,要说一夜之间便忘得干干净净,那是不现实的事情。在她的印象中,肖若聪一向都是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人。当初,他不愿与她私奔,却又与她藕断丝连,才酿成日后的那场大祸。香莲至今也不知晓若聪给人阉割的事,但她知道若聪一定为此事吃尽了苦头。如今,他给日本人干事,也许真像他所说的,是迫不得已的,但即便如此,她也不能原谅他一个连自尊和人格都不讲的人是不值得她倾心去爱的。
“娘,难道我真的是他的女儿?”雨霖依旧有点不相信这件事。
香莲点了点头:“这事,我本不想告诉你,可你既然已听见了,我就不想再瞒你了。但你要记住,李宜龙依旧是你的父亲。他还是很疼爱你的。至于肖若聪,那就要你拿主意了。”
她说罢便将二十一年前发生的那场风波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女儿。雨霖还从来也没料到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世。她惊愕了。在记忆当中,她一直是个名门旺族的大家闺秀,从来也没有人在她跟前提及过肖若聪的名字,可一夜之间,她却突然变成了一个私生子。这个现实太令她难以承受了。
“娘,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她哭泣着说,“这些都不是真的,是吗?”
“不,这些都是真的”香莲也流着伤心的泪水说,“娘的命苦哇!”
之后的几天,雨霖的心情都很黯淡。她的脑海里总也摆脱不掉肖若聪的影子。她会情不自禁地把他与李宜龙加以比较。说起来,她对李宜龙的感情总有点疏远。从小她就很畏惧父亲的那一脸络腮胡子。虽说后来他剃去了胡须,可她依然留下那么一点怕的阴影,尤其在父母吵架的时候,她总是躲得远远的。
长大以后,雨霖又有些对父亲亲近了。她发现外表冷峻的父亲有的时候也很可怜。岁月的风霜使他过早地衰老了,两鬓斑白,额顶也开始变秃了。他积累了不小的家业,可一夜之间又一贫如洗。就在一个多月前,他托人传来口信,说他现在河南的南阳隐名埋姓开了一个杂货店,生意很清淡。他和梁云贵也仅仅能糊口而已。
香莲听了这话,幽怨地说:“这个死鬼,把我们孤儿寡母扔在这里就不管了。他算把我给害苦了!”
莹娇也愁眉不展地说:“小雨薇这些日子连大门口都不敢出,一出门就挨打。我们一家人都是女人,也一天到晚受人欺负,这日子可没法过了。”
“没法过了,你就走人。”香莲没好气地说。
莹娇怯生生地看了香莲一眼,退到一边去了。
雨霖见状,不高兴地说:“娘,天涯伦落人,您何必这样对待人家呢?”
“我怎么对待她了?”她没好气地说,“我还有苦没处诉呢。”
闵香莲自己也清楚,李宜龙走后,她的脾气变得越发古怪了,常常莫名其妙地发一通无名火。尤其若聪那晚走了后,她几乎天天都在发脾气,连柳眉也让她骂哭了几回。事后,她也挺后悔的,发誓再也不这样做了,可一遇上事,她又板不住自己了。
昨天,她收到肖若聪从奉天城给她汇来的一笔钱,还随寄了一封信,说是用来接济他的女儿的。香莲有心把钱退回去,可雨霖执意不肯,她不愿再伤那个人的心了。
雨霖清楚那天晚上她的话已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但那都是气头上的话,实际上,她对生父的第一印象并不算坏。
“大小姐,来客人了。”柳眉在门外喊道。
雨霖急忙往门外走。“会是什么样的客人呢?”她默默地想。
两个陌生的年轻人站在她面前,都二十岁上下的样子。
“您就是江太太?”其中一个人恭恭敬敬地问道。
“你们是谁?我们并不认识。”她警觉地说。
“是这样,”那人解释说,“我们是东北军七旅三团的,江迅副团长派我们接您出去。”
“你们认错了,我不是江太太。”她说完转身往屋里走去。
两个人急了,忙跟过来说:“江太太,您别误会,我们可不是坏人,我们有他的亲笔信,请您过目。”
亲爱的霖:
真没料到新婚之夜居然是我们忍痛离别的日子。“九·一八”的炮声葬送了我们的蜜月,
悲兮痛兮,撕心裂肺,难以言表。古人云:败军之将不言勇。我也无意表白我当时所做的一切。无奈上峰有令,不许抵抗,吾辈只能背上历史的骂名了。早知如此,莫不如就与你厮守在一起了。我真后悔。退守关内之后,我无一日不思念娇妻,幸亏有你一张照片,夹在我的证件里,每日与我相伴。孤寂的心,有谁知晓?幸亏日前,在北平偶遇小妹,方知你已返回辽城,心中不胜思念。今特让我的两位弟兄专程前来接你,万望不要推辞。切!切!
江迅字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六日
雨霖将信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眼睛不觉有些湿润了。新婚一别,不觉数月,她一直惦记着生死未卜的他。如今见到他的亲笔信,不禁喜出忘外。毕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先前对江迅杳无音信的幽怨,顿时烟消雾散了。
“他现在怎么样?”雨霖急切切地问。
“江太太,江副团长现正驻防北平南郊。他现在很好,只是盼着能早一天见到太太。”
雨霖脸一红,说:“谁想见他。”
“江太太,您要是不去,我们可就没法子交差了。您可知道,我们这可是冒杀头的危险来到日本人眼皮底下的。”
香莲也急忙说:“霖儿,听娘的话,快跟他们走吧。这里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莹娇也羡慕地说:“雨霖,你可真有福气。”
雨霖抑制着欣喜,收拾衣物去了。她真想能马上见到江迅。
这会儿,一阵唢呐吹奏的哀乐飘进屋里来。雨霖愣住了,忙打发柳眉去打听怎么回事。不久,柳眉跑回来说,是那个维持会长吴渔死了。
“他死了?”她惊讶地说:“他这个会长才当几天呀。”
“活该!”柳眉解气地说,“谁让他占了老爷家的大宅呢。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柳眉,可不能这样说,”香莲说,“我知道那个吴渔可是个懂事理的人。他本来也不愿干,是日本人硬逼他干的。可怜呢,快九十岁的人了,哪能经得起这番折腾。我看准是窝囊死的。”
“唉,日本人一来,谁也没好日子过了。”雨霖不禁叹了口气。
雨霖简单收拾一下行李,随那两个人从屋里走了出去。外边的天气很寒冷,她连忙将大衣领子立了起来。闵香莲、杨莹娇和柳眉三人难舍难分地将她送出大门外。雨霖走出好远,一回头见母亲她们还在远远地望着她。她两眼湿润了,使劲摆着手说:“娘,你们回去吧,日后,我会回来看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