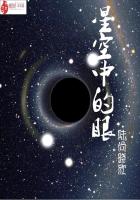四
我登上了进京的列车,天色渐渐暗下来,窗外的风景急速地向后退去,列车象匹骏马,在山谷间奔驰,大大的提声让人昏昏欲睡。我不知道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在哪里,进京是我打初稿时的想法,后来在我登上这列车的途中突然改变了,我成了无头苍蝇,只能用脚去支配身体。窗子关的严严实实,车厢上空漂浮着汗味,脚臭味以及鱼腥味。过道站满了人。一个民工样的人钻进了我的坐席下,两只脚留在外边,让人产生恐惧。我的脑中出现警察一人拽一支脚,顺着过道把他拖走的幻象。一位乡下的妇女怀抱着孩子在邻座哄,孩子被鬼抓了似的睁眼嚎,卷卷的黄毛已经被寒露成稀松的几缕。妇女把孩子送到我的眼前,恶狠狠地说,恶他,恶他。我一惊,看女人的眼神后才明白,是让我吓唬孩子。女人极有耐心地等着我,我感到双臂酸疼,只好大呵一声。孩子楞一下,仍旧哭。人在旅途,身不由己。孩子是无辜的,我成为善良的迫害者。我知道,人在这种闷热,混乱,嘈杂的环境中神经会受到严重伤害,如果间隙性神经病坐这样的车就会伏法。我说,你把他抱到门口吧,那里凉快些。随着车窗的黑暗,车厢安静下来,对座是一男一女,两个人贴在一起,边嗑瓜子,边窃窃私语,只能听出一些单词和破碎的瓜子皮。但我敢断定,他们决不是夫妻。挨我坐的是十四五岁的姑娘,双腿并拢,直直地伸出去,鞋跟顶着对座男人的鞋尖。女还合着眼睛,用两只嫩手掰瓜子,把瓜子批顺腿沟一溜。列车员走过来,说弄地下了,姑娘一声不吭,也不抬眼,脸上的肉都坠到腮下,让人产生去煽一巴掌的欲望。大腿根至讫间的瓜子批,象涨潮推上沙滩的泡沫,如果姑娘再长几岁,绝对能勾给人的流氓意识。这时列车员又走回来,厉声说,听着没有,别往地上嗑。那女的也说,小放别嗑到地上。姑娘眼不睁,决着嘴读让说谁整地上了。我看出,姑娘是抗议那男女的亲热。过了一会女的去另一车厢。姑娘睁开眼,把一把嗑开的瓜子递给了那男人。我知道自己是猜不出他们的关系了,便拿出上车前买的杂志看。我读着许辉的《秋天的远行》,我竟不敢,也不愿相信,我的想法与行为竟与许辉不谋而合。我决定不去北京,既然许辉在北京什么也没有找到(他说他没有目的,这是骗人的谎话)我还去干嘛。我在这时才恍然大悟,我想去北京的想法是可笑的,老吴怎么可能去北京呢。我准备先睡一觉,昨晚睡的太少,现在大脑有些混沌。
前一段我弄到了一笔钱。我有了钱才知道,当今的时代弄钱并不算难,而难的是花钱。我经常下企业采访,一些厂长经理谈到企业经营,就抱怨三角债,三角债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瓶颈。我决定从难处入手,我找到一位平时关系不错的厂长姜明,告诉他我要帮他请债。我许诺半年时间给他请回一百万元。厂长哈哈笑,说,你是记者,你怎么能去请债。我说你可以聘我为名誉职工。厂长最后说你试试吧,有一笔二百万元的款,压两年了,我亲自去了两趟都没请回,如果你能请回一些,我可以按厂内政策给你提成。我说一言为定。我们两紧紧握了手。
我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探索假,把存款和借的款五万元存入金卡,起身北上,这是一家中型汽车改装厂。我以异地采访记者的身份找到了厂长。厂长五十八岁,是这厂的元老,长了一付自然界的眉毛,脸方嘴阔,待人倒直率热情,我们谈的很投机,了解一点你的家庭生活,以便把稿子写的更丰满一些。老头呵呵笑,抹一把嘴叫的饭杂说,俺们欢迎,不吃啦?走。坐着厂长的袄地十分钟就到了。厂长夫人平易淳厚,把我热情让进屋,切茶倒水递烟,没一点官太太的傲慢矜持。我环顾客厅,屋子装修的很简单,电视机也不是名牌。墙上挂着字画,字写的很有功底,浑劲雅做,气韵生动,看落款,是厂长的墨宝。我说,哎哟,今天来对了,您是书法家呀,我正求师无门,您的字写的真好。厂长自得地抹了抹花白的短发,朗生笑说,活动活动筋骨,爱好而已,厂长谦虚,我说,您的书法深得颜书浑厚,气势磅礴的神髓,且有疏朗开阔,周围经验的华采,与舒同的字同源。厂长喜悦之色溢于言表:俺倒是喜欢颜鲁公的字,汉里碑拓也临了不少。你临过《礼器碑》吧?我问。你挺懂行,俺前年到山东开会,顺便到屈服孔庙看了《礼器碑》真迹,是汉隶中着名碑刻。其书法峻佾精妙,笔画艘竟刚健,结构端庄蜀绣,有青铜器铭文之意趣,被清书法家问芳纲遵为汉隶第一,习书人不能不习,俺特意买回一本《礼器碑》拓页。我们两从东京二王说到唐朝欧阳询,张旭,从大宋舒适,米嗑到清朝的王锋。厂长非常兴奋,以为遇到了知己,其实我对书法只知其皮毛,佻巧八十,光说不练。
我决定投其所好。我找到有一面之交的当地记者朋友,他的名,把我写老厂长的通讯发到日报上,便打倒回副,转车进系。我托北系的作家朋友花四万五千元购了幅张竟的条幅真迹,再次登门。厂长对我写的通讯很满意,拿出龙井茶款待。闲谈一会,我便拿出张竟的字画,展给老厂长说,这是姜明厂长让我崤给您的。这家汽车改装厂是姜明的配套厂,也是他最大的上帝。虽然欠款,姜明也要供他货,旧货款给一点,新货款又压下了,改装厂有钱也不愿还帐。厂长领我到书房,书房一张大举止漆写字台,上置文房四宝。墙角亭亭玉立的是巴西树,嫩绿若雨后的玉米叶,一面墙的书柜兼古董柜,满屋书香气,老厂长拿出放大镜,把画平展到写字台上,从上到下一个字一个字细瞧,镜子修到款印上,足足盯了半分钟,然后翻过来,细察托背。放下镜子,让我把墙上他自己的字摘下来,把张竟的字挂到墙上。老厂长则退至门口,背起手,眯起眼,神品赏,嘴里啧啧有声:珍品,珍品,上乘之作。这位清末明初的宫廷画家有一幅画《铁拐李图》,就藏于你的边城博物馆,我去边城时看过。这幅字不次于他的画。这么贵重的东西,你说俺怎么好收呢,光搁这放几天,俺临一幅再还他。说着,拉我的手回到客厅。我明显感到老厂长的手心全是汗,而且在抖。我知道厂长笑纳了,便借机说:姜厂长是我姐夫,他知道您喜欢书法,出差北京托人弄的,表示一点全厂职工的心意,感谢多年来您对他们厂的帮助。老厂长呵呵大笑,说,这小姜,还真没忘我这老头子,他们厂怎么样?我忙跟上:他的厂目前挺困难,主要资金困难,买原材料的钱都不是。现在各企业都挺困难,象您这样的企业真不多。那道是,老厂长自信地冲我点头说。又说,噢,小姜托你要账来了吧,这个小姜,怕俺该黄了他,哈哈哈哈。我说,哪里哪里,您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信誉证据高呢,你们是信誉三A企业嘛。我只是顺路,姜厂长说看您的情况。好吧,厂长宽厚的大手拍一下沙发的扶手说,先给他一半,你回去告诉小姜,要把质量稳定住,影响了俺的整车出厂,俺可找他算帐。厂长说完又爽朗笑起来。我也跟着笑,说:请您把汇到宁新化工厂,姜厂长要从这家化工厂进批原料。我把写着帐号,开户行的纸递给他,又说,老厂长,我想再麻烦您点事。老厂长盯了我一眼,问,什么事,说吧。我说想请您赐幅字。我知道他这样的书法家都喜欢送别人字,其实每个人都有表现欲。老厂长笑说:行,我就献丑了。说完进书房铺纸研墨,运气悬腕,书了寒儒风度四字。我这所谓寒儒便致谢告辞。几天后,100万元转到了我真正姐夫当厂长的那家化工工厂。他们这家镇办企业准备上一个新项目,正愁资金,我们谈妥,借期半年,利息25%。半年后,化工厂如期偿还了借款。我把姜厂长给我的2%要帐提成送一半给姜厂长。我知道挣钱不能自己花的道理。一夜之间,我成了一个小款爷。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壑难填。贪得无厌的人终将被欲海打翻,这是必然劫数。好在我是个小富即按的人。我和妻子几夜未睡好觉,真是又惊又喜。我们商量怎么样花,买房子,我们有房子;买汽车,太乍眼,再说买起养不起;买股票风险又大。没有钱时觉得缺很多东西,有了钱又发现什么东西也没法买,线少的不缺钱多的买不起。最后决定存入银行,国家的钱再还给国家。我自己把自己弄糊涂了,我的钱是挣的?骗的?偷的?抢的?就算是抢的,我抢谁的,所谓流通,就是象打篮球中的合理冲撞吧?但有一点是深切感受的,我们心里不再没有底,可以安心去生活了。
一切可以制造的安定背后,都可能潜伏着风暴式的危机。我在苦心掘金之后才发现,我已经站在了挖空矿石的陷阱边上。我决定救我自己。我说,我要去寻找老吴。妻子说,你上哪找他,谁知道他在哪里?我说,找不着也要找,我相信我们都不会丢失。妻子把脸埋到我的胸毛上,嘤嘤哭: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说你知道,我还在推自己下来,你应该帮我。写字台上的灰有大钱儿厚了,好几只苍蝇呛死在上边,我夜里常常听到老鼠在偷翻我的书看。你有时间帮我打扫打扫我回来后,好把那部长篇的下部写完,再说那个故事的结尾,我也该处理了。妻子死死地扎着我,边抽泣边应着。
朦胧中,我的脑袋象西瓜在桌面滚动。我抬起头,几个扛行李的汉子向车门拥去。窗外的灯光象妓女的眼睛,昏暗而多情。我站起身,随着前边的人,把脚扔进深不可测的站台。出站口验票的女人两眼惺忪,袖手抱肩,任零零落落的旅客消失于黑暗之中。一又窄又瘪的老头,胸前挂着牌子,向旅人亮售床铺,那卑琐的神情就象土改换斗的地主。有毛驴咴咴喷鼻,车上闭着面目不清的人影。我走过去,那人把一个软忽忽象下端肉的东西塞给我,我捏捏,又潮又粘,还是垫在臀下。哪蹽?那人用鞭杆指了下毛驴尖瘦的后跨,这是一个并不老的汉子,嗓音象包米面饼子,但不恶毒,看着蹽吧,我尽量语气粗些,给他一种亲近感。毛驴哒哒敲着马路,可能是某只蹄掌少了钉,哒哒中夹着趿拉趿拉的杂音,象城里的老人穿着拖鞋晨跑,我侧耳分辨,是左前蹄。赶车的汉子裹着棉大衣,嘴上的烟头明明灭灭,默不作声。偶尔哎一声,估计是告诉驴快些走。路两边坐着一栋挨一栋的大沿青瓦房,窗台离路面约米高,木门紧闭,无声无息。偶有一两幢二节楼,瓷砖贴面,定是新建的,这是一条主干道,道边有路灯,只亮灯薪,象输了钱的赌徒,红着眼,孤立无援,这是一个偏僻的小镇,我睃寻着店卑,但也看不清。毛驴车停下来,我转过脸,已到了镇子头,磨回吧,我说。汉子哦哦两声,毛驴有些莫名其妙,还是磨个半弧,又顺原路哒哒返回。到车站,我跳下车,问车老板:多少钱?两元吧。汉子耻着白牙,冲我笑了笑。我掏出一张票子,是拾元的,便说,甭找了,转身向候车室走去,候车室也是起脊青瓦房,房基下陷。屋字里灯光青白,蚊虫围着水银灯舞蹈。凳子上歪歪扭扭睡着几个人,墙根也有几个男人裹着棉袄在打瞌睡,象涂了银粉的瘪水桶,弃之心痛,爱莫能助,我的脚步声惊醒了斜靠椅背的老汉,老汉叮了我一眼,把挨着的年轻人往里谈恶了探,扬起胳膊说,过来歇歇腿儿。我知道是冲我说的,便冲老汉点头笑笑,走过去。我递给老汉一支烟,老汉晃晃头,从腰间抽出旱烟袋,装上烟,点了,刚吸一口,就哐哐咳,一扬下巴,一口痰射到对面的凳腿下,又抽口,将烟浓浓吐出。
去哪里,文化人?老汉想表明自己见多识广,能掐会算,张口称我文化人,我迟疑一下,说:本镇。公差?办事。我不想和他多唠,尤其是这个话题,我能告诉他是老吴把我引出来的,扳道又让许辉给弄到这个镇子?我说不清楚,他也不会明白。老汉不再追问,独立一口一口抽烟。我发现他的烟根本没咽下去,而是裹一口便吐出去,吐出去再裹。又坐了两袋烟功夫,老汉推年轻人说,透亮了走。老汉的吆喝声唤醒了凳子上、低上的人,便都拾缀包裹行李向外走。
屋子里只剩下孤伶伶的我。
我感到一股冷气从脚心一丝丝往身上爬,到膝盖,打个旋,又蛇一样往心窝钻,我越来越冷,身子紧缩,嘴唇颤抖,嗓子眼儿又痒又咸,是感冒了,我应该马上去医院弄些药。
五
我从阳光灿烂的云间坠入一个黑暗古老的洞穴中,眼前是透明的橙黄色,金星跳跃,继而进入一团灰色的浑浊,身体悠悠倒立,渐渐滑入又浓又黑的旋涡,嘈杂的声响从耳际退去,柔柔软软地沉寂到庞大的固体之中,四周是化石般光滑的静止,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带着潮湿的风急速掠过……
我睁开眼,窗外阳光灿烂依然,窗棂的影子斜射到雪白的墙壁上,象基督教堂顶的十字架。我的头顶挂着吊瓶。屋里除了一个床头柜和一把小方凳,其它什么也没有。这时,门轻轻开了,先是一张青春夺目的脸,然后是婀娜的白大褂。
醒了?你运气真好,这屋子刚粉刷过,你是第一个患者。
姑娘的嘴唇大而薄,红润鲜亮,让我想到果汁鲜满,甜中含酸的橘瓣,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用眼睛和嘴角笑笑:特意给我准备的?你们怎么知道我到这里来。
姑娘咯咯笑了,上下唇一抿,把笑意留给眼睛,告诉我,今天早上我晕倒在路上,是本镇两个青年人卸了一家门板,把我抬到了这里。这是我们的高级病房,院长吩咐了,让我护理好你这外地客人。姑娘说,你患了重感冒,额头能摊热煎饼,说者又咯咯笑了,牙齿象加工过的天然玉石,洁白透明,整齐均匀。
我被她的热情、直率而感动。
你叫什么名字?我突然想起一个人。
小真。名字重要吗?姑娘歪着白颈反问。总得称呼你些什么吧。
你可以叫哎,或者喂,我不在乎。
你姓小?百家姓里好象没见过。
你问我姓了吗?我这人记性不好,要不就考上大学了。
奥,是我的记性不好,我忘记着自己的姓,忘自己的名,要不弄个副外长啥的倒没啥困难。
你叫啥,看你能想起来不。
我叫老邸。我把眼撇上天棚,作思考状,我不姓老,我姓邸,我就叫老邸。要不你把身份证拿来,那上边有我的名字。就在那个背包里,夹层后边。我抬起半个身子,找我的包。
别找了,好不好,就叫老邸,来吧,喝点麦乳精。小真把枕头立起,让我靠紧床头。又端过一只精致的小碗,要喂我。我赶紧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行。嗨,你们城里的男人都这样呀,是真封建还是假封建。这是院长交代的任务,也是我的工作,谁让你是我们的客人呢。我纳闷的脸红,我确实是虚伪的,哪个男人会拒绝一个可爱的姑娘喂他水,除非是疯子傻子或同性恋者。我感到浑身发热,一股股热流往上涌,呈放射状,从心脏涌向双腿,涌向五官。我一口口喝着,象个婴儿。我想哭,我想起母亲和妻子。在我12岁的时候,我在园子里翻地,累了,就躺在墙根睡着了,等母亲把我抱到炕上,我已成了炭儿似的,母亲就这样含着泪喂我滚烫的姜汤,前年,我滑倒在楼梯上,因轻微脑振荡住进医院,妻子就这样深情地凝视我,一勺一勺喂我八宝粥。我现在才知道,童性是一直潜隐在每个人的精神中心,成熟和衰老的是肉体,是由社会塑成的表皮,所以天使的形象总是孩童,天使,是孩童和女性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