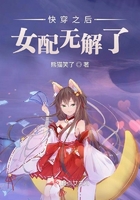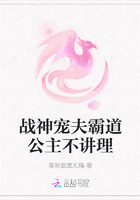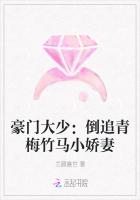咸丰与奕訢的矛盾增加了新的内容。奕訢同洋人频繁接触后,认为其与以往蛮狄大不相同,并非为争城夺地而来,可以遣使通好,借师助剿,视为共讨“发”、“捻”的“与国”。奕訢、桂良、文祥等人并于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还执意要去掉“通商”二字,欲统揽所有军国大事,明显有另立军机之嫌。所有这些,都是三人联名封奏,廷臣普遍回应,可见奕訢周围已形成了一股势力。肃顺等更密陈,巴夏礼被释放前曾劝奕訢自登大位;《北京条约》画押前,夷人提出让王公大臣跪迎奕訢以试探人心向背等。
可以看到,辛酉政变是清廷最高统治集团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这一历史的必然结果,以慈禧通过政变上台的历史偶然表现出来。
另有史家认为,辛酉政变中慈禧一方成功的决定性深层原因,是当时正统皇权思想或政治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赞襄政务八大臣虽奉有咸丰帝的煌煌遗诏,慈禧等人却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八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而京师文武大臣及握有兵权的胜保、僧格林沁等均倒向代表皇权的两宫皇太后一边。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充分显示出来。
失败的母亲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二十六日,同治十七岁,两宫皇太后撤帘归政。不到两年,十三年十一月初八,同治病危,两宫皇太后二次垂帘。
同治帝(1856年—1875年),姓爱新觉罗,名载淳,咸丰帝独子。在位十三年,年号同治,死后庙号穆宗。同治帝是清朝最后一位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皇帝。一位史家说,同治的时代被时人誉为“中兴”,而中兴的辉煌事业却与同治无缘。同治一生都隐匿在其母慈禧的裙幅背后,属于他的只有一段可悲可叹无可奈何的风流故事。
同治六岁登基,两宫皇太后垂帘。除了读书、成长,锦衣玉食,同治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权欲熏心、志大才高的生母慈禧全副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国家大事上,完全忽略了同治的存在。也许她以为她给了儿子生命;她为了儿子皇位的稳固,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发动了辛酉政变;她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为儿子铺路……但她远远离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不仅仅在于她不再有时间和精力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关心和看顾儿子,更在于她将儿子物化成了作为大清国家标志和符号的一个皇帝,以相应的标准衡量和对待他,特别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施恩者的姿态对待他,难得笑脸相迎,总是板着面孔、恨铁不成钢、无穷无尽地说教、苛求和训斥。
同治理所当然地投向了温柔慈爱的慈安,对她孝顺孺慕,如同亲生母亲。对慈禧则敬畏有加,暗暗滋生了越来越强的逆反心理。
同治与慈禧第一次公开对着干,是擒杀安德海。安德海原籍为历史上的太监之乡——直隶南皮,早年自宫入内当了太监。他机灵乖巧,擅长溜须拍马,没几年便得到慈禧的喜欢,成为慈禧心腹。辛酉政变时,他行苦肉计,回京传递两宫密信,成为铲除肃顺一党的“功臣”、慈禧跟前红得发紫的人物。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后,安德海仗势骄狂跋扈,“渐干国柄”。他屡进谗言,使慈禧夺了奕訢议政王之权;又笼络朝野,招降纳贿,使文武百官奔走于其门下,势焰骎骎,有如明朝权宦魏忠贤。同治最讨厌安德海那种小人得志的下贱嘴脸。安德海狐假虎威,竟成心当着慈禧,用教训的口吻劝导他好好读书,还派人监督他,将他的一言一行全都报告给慈禧。同治曾因事斥责安德海,安德海转身便到慈禧那里告状,使慈禧责罚他,让他益加痛恨。同治年龄渐长,情窦初开,喜欢上慈安宫里的一个宫女,那是青春期男孩的一种炽烈、清纯的情感。安德海为讨好主子,将此事添油加醋密告慈禧,说皇上为了那个宫女,三天两头往那边跑,所以来这边的次数越来越少,读书也不上心了。还说,此风不可长,皇上长大了,什么都由着自己性子来,将来可怎么得了云云。慈禧听了火冒三丈,立即移驾慈安宫中,拉下脸儿说了一番大道理,将那个宫女指婚发出了宫。同治又气又痛,对安德海恨之入骨,经常在宫中用刀砍小泥人的头,边砍边咬牙切齿地说:“杀小安子!”同治八年(1868年),同治已十四岁,两宫皇太后颁旨为他筹办大婚。安德海向慈禧讨了到南边采办大婚物品、监制龙衣的差使。这事非同小可。清朝入主中原后,鉴于历朝宦官干政的流弊,在宫中立下铁牌,严禁内监过问政治、交接外朝,不准出京,如有违反,一律处死。安德海仗着慈禧的喜爱,仗着自己替主子做过大事,根本没把清朝的祖制家法放在眼里。他大张旗鼓、耀武扬威,带着诸多随从、远近亲戚、买来的老婆、保镖、女乐、僧人,载了十几大车的箱笼物什,浩浩荡荡出了京城。在通州上船,共计大平安船两艘、小船五六艘,大船船头挂一面“日形三足乌”大旗,取“三足乌为西王母取食”之典,一路招摇,进入山东。不料,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以没有勘合、假传圣旨、擅自出京并搜出十数箱珍宝及外官请托密函为由,一举拿下。同治早就等着这一天。他兴奋不已,觉得此次杀安德海有十分把握,母后慈安、六叔恭王、军机大臣肯定都会支持。丁宝桢的折子到时,慈禧恰巧受了点凉没到养心殿,这折子便被同治一把抓到手里。他命人请六叔恭王带军机处、内务府的人一齐来,又去找慈安来听折子。随即,同治将此事知会慈禧,道:小安子胆大包天!我见额娘休息未起,赶紧传了六叔、军机处和内务府的人来商量怎么办,然后赶来请旨……慈禧一听脸色大变,刚要发作,同治又急道:额娘息怒,犯不着为这混账东西生这么大气!这混账东西不说为额娘争光,反倒给额娘脸上抹黑!不收拾他,倒像咱们没有祖宗家法似的,额娘千万别气坏了身子。慈安也道:妹妹别着急,不是有顺治爷留下的规矩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小安子自找,让咱们白疼了他!慈禧被堵得哑口无言。当时朝野一片喊杀之声,近支宗室亲王大臣也纷纷上折力争,坚决要求惩办安德海,维护祖宗家法的尊严。内务府主张严办,不开先例;军机处拟“就地正法”;慈安则道:这安德海犯法,辜负了我们姐俩儿对他的信任,听说他还在船上挂了什么旗子,好象是皇太后叫他四处去打秋风,成何体统!妹妹,我看是容不得他活命了,这也是他自找的,不是你我不给他面子,你说呢?
于是,安德海人头落地。慈禧咬碎银牙往肚里咽,并追加一道谕旨,命将此案一干人犯——跟随安德海的亲信、太监、保镖、帮手一律就地处决;安德海花钱买来的妻妾等人全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又发一道明发上谕,将本案有关文件全都编入宫中则例,着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事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如有不安分出外滋事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连该管太监一并惩办。上谕通令各省督抚,“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拿,奏明惩治,毋稍宽纵。”
同治与慈禧第二次公开对着干,是选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两宫皇太后主持为同治挑选后妃。经过反复筛选,只剩下了四位,刚好是一后一妃二嫔之数,关键是位次如何排。本来说好,主意由皇上自己拿,但十七岁的同治还是要听两位皇太后的意见,而两位皇太后的意见却不一致。慈禧中意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富察氏出身满洲正黄旗,端庄秀丽,更重要的是性格柔顺,小同治三岁。慈禧喜欢老实听话、低眉顺眼的儿媳,可减少婆媳间的矛盾和摩擦,在迎合自己心意、顺从自己指使的前提下,和和美美地过日子。慈安则中意清朝唯一的蒙古状元崇琦的长女阿鲁特氏。阿鲁特氏虽然相貌不很出众,还长同治两岁,但雍容端庄,气质高贵,娴熟诗书,德才兼备。俗话说,“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同治即将亲政,但他毕竟只有十七岁,需要一个稳重、有主见的贤内助统率六宫,如果比皇上还要年少柔弱,这一双孩子如何挑得起重担呢?还有一层,这阿鲁特氏是被赐死的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端华身后无子断了香火,况其获罪因肃顺而起,慈安总有怜悯、不忍之情。同治本人原没有什么定见。但他知道若要选色,皇帝定制六等妃嫔,将来还有的是机会,皇后则不同。亲政在即,届时自己一个人掌管天下,若娶个比自己还没主意的小媳妇,岂不还要为后宫多操一重心?他听说阿鲁特氏是个才女,长相二等,德性一等,隐隐有了一定的倾向。慈禧、慈安的做法也不同。习惯于事事做主、特别是为儿子做主的慈禧,自认自己是生母,给儿子挑媳妇是天经地义之事,自信自己完全是为儿子好、尽心尽意为儿子考虑,儿子没有理由不听自己的,她没有想过儿子的想法和感受,也没有想过要了解儿子的想法和感受。慈安则把儿子的想法放在了首位。她专门绕到同治的住所,问儿子的心意,和自己一样最好,不一样也别事到临头难为他。不料儿子的思路竟与自己不谋而合,欣慰之余,她感到儿子确实长大了。
正式选定后妃之前,慈禧当着慈安的面,以不容争辩的教训口吻叮嘱同治:立后是大事,皇帝须好生考虑。这四位姑娘,凤秀的女儿是满八旗世家,当年乾隆爷孝贤后就是富察家的女儿。论家世、论人品都是没得挑的。崇琦的女儿相貌平常,大你二岁,且是蒙古八旗。自康熙爷到现在二百来年,皇后都出在满洲世家,这个例儿可不可以破,你可想好了。同治逆反之极,几乎立刻就作出了对着干的决定。慈安瞧了出来,知道大事不好。她了解慈禧,谁要负了慈禧,这辈子再甭想过好日子。慈禧必定会迁怒同治所选之皇后,后宫将永无宁日。
正式选定后妃的程序,是设一铺明黄色桌围的御案,案上放一柄如意、一对大红彩缎荷包、两对镶黄边绣鸳鸯的荷包,作为皇家的定亲信物,由皇帝亲手将其分别交到中意的候选者手中。其中如意代表皇后,大红彩缎荷包代表妃,镶黄边绣鸳鸯荷包代表嫔。候选者接过定亲信物就算定了终身,只等着大婚的日子迎进紫禁城了。两宫皇太后与同治就座后,四位名媛被引导进来,请完安后侍立一排。慈禧拿起如意,郑重地递给同治,又一次加重语气叮嘱道:皇帝,你可想好了,瞧中了谁,便把如意给她吧。同治答应一声,双手接过如意,转身径直走向阿鲁特氏,毫不犹豫地将如意给了她。慈安赶紧拿起大红彩缎荷包递给同治,一面向他示意凤秀之女。同治会意地接过荷包递了过去。又分别将另外两对荷包交给了余下的两位姑娘。选妃结束。阿鲁特氏成了大清第十代皇后。
一位历史学家曾生动而准确地描绘了慈禧当时的感受,征引如下:
慈禧突然觉得,天地之间有个什么东西塌了下来。不偏不倚,一下砸在她的心上。一股热血从心底里冲了出来,像奔突的烈焰刹那间便填满肺腑胸间,然后往上一下子涌到了脑门。左额头的青筋不由得猛烈跳了起来。她突然看不清眼前所有的东西了,皇上、名媛、命妇、太监们全成了一片血晕,血晕之中的儿子突然变成六岁时的模样,咧着嘴笑着,伸着手向自己走来,走到一半,突然调头向慈安走去了……转眼又变成刚刚生下的婴孩,张着嘴,不知是哭还是笑……有好几天,慈禧心里都是凄凄凉凉的。人都说儿子是自己的亲,可是自己要强了一辈子,偏偏是自己的儿子不给自己争气,连平民百姓娶媳妇嫁女都是凭父母一句话呢,何况自己是掌管天下的皇太后。居然管得了天管得了地,却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这多让人伤心。更让人伤心的是,儿子竟听慈安的话。平日听她的也罢了,毕竟是她把他从小抱大,脾气又比自己好,也就不计较了,可到这关键时刻还是听她的。传出去叫自己多没面子,不跟没有儿子一样了吗?十月怀胎,那辛苦谁能理解,生孩子时受的苦痛谁能体会!这往后,大事小事都听她的,那自己还有什么意思。不成了摆设!眼看着立后完了就是亲政,他们两人要是拧成了一股绳,凡事不听自己的,再把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局面抛到一边另搞一套,岂不寒心!到时候自己靠边站了,连话也说不上了。那不得活活气死!
在慈禧的内心深处,还藏着一种不为人知的阴暗心理,这是一种强烈的嫉妒之心,一种女人才有的嫉妒。对她来说,十七年来儿子一直是属于她一个人的。不管慈安在同治心里占有多重的分量,只有她才是皇上的生身之母。无论是谁,无论走到哪儿,这一点都无法改变。所以慈禧在心理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她可以居高临下地看慈安,看儿子,因为她知道她永远是最后的赢家。可这回却不同了,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已经娶了媳妇,他的心属于另外一个女人了,母亲被无情地排挤到次要的位置上。这种变化对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来说,实在是一种无奈,一种尴尬,更是一种挑战。于是她本能地站到了儿媳妇的对立面。她嫉妒这位状元女儿的才华,嫉妒她的出身,嫉妒她可以入大清门、行御道。这是唯有册立中宫的皇后才有的特权,而这一切对慈禧来说都是永远不可能有的……也许换一个婆婆娶了这样一个体面的儿媳会高兴得发疯,可慈禧一点都不高兴,她不允许这世上有比她更尊贵的女人。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中,同治大婚。五天之后,两宫皇太后颁布懿旨,命钦天监于翌年正月择吉期,举行皇帝亲政大典。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两宫撤帘,同治亲政。
同治亲政的一年多中,他似乎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修园,一是冶游。修园,本出于孝心,想为两宫皇太后营建一方颐养天年的乐土,一方面安慰归政后落寞无依的可怜母亲,一方面稍稍转移母亲的恋权之心。冶游,则出于逆反之心。同治对后妃本无所偏心,慈禧却延续选妃时的矛盾,固执地偏向位于第二的慧妃,几次三番、无端地讽劝皇帝广沛甘霖,“眷顾”慧妃,同治索性发狠不召任何一位妃嫔侍寝,独宿乾清宫。然同治毕竟年少、不耐寂寞,加之修园为贪官所骗,朝上亲王重臣哭谏,朝下两宫太后数落,他自卑到了极点、心烦到了极点,于是破罐破摔,听从佞臣宵小的教唆带引,微服冶游,放荡于琉璃厂、八大胡同、茶园酒肆、青楼妓院,狎邪淫乐……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同治病了。前因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群臣激烈反对,修圆明园改为修三海(北海、中海、南海)。这一天,同治亲行巡视三海工程还宫后,自觉不适,本以为劳累所致,稍息即愈,不料竟发起烧来,太医院用药无效,一连三日不退。第四日,同治耳后颈项四肢出现了大批丘疹。侍候于旁的太医院首领庄守和、李德立惶惧战栗地在脉案中写下了沉重的两个字——“痘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