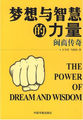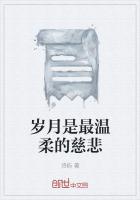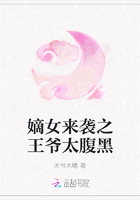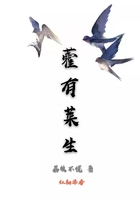唱工一层,旧戏的“护法使者”,最要拿来自豪。唱工应废不应废,别是一个问题,纵使唱工不废,“京调”中所唱的词句,也是绝对要不得。歌唱一种东西,虽不能全合语言的神味,然而总以不大离乎语言者近是。且是,曲折多,变化多,词句参差,声调抑扬,才便于唱。若用木强的调调儿,总是不宜。“京调”不能救治的毛病,就在调头不好——不是七字句,就是两三加一四的十字句。任凭他是绝妙的言语,一经填在这个死板里,当然麻木不仁、索然无味起来;这个点金成铁的缘故,全是因为调头不是——不合言语的自然,所以活泼泼的妙文,登时变成死言语,不合歌曲的自然,所以必须添上许多“助声”、“转声”。我们说话,不是要七字十字,唱曲何必定要七字十字。从四言五言乐府,变成七言乐府,是文学的进化,因为七言较比五言近于语言了;从七言乐府,变成词,是文学的进化,因为词更近于语言了;从稍嫌整齐的词,变成通体参差的曲,是文学的进化,因为曲尤近于语言了;可是整齐的“京调”,代不整齐的“昆弋”而起,是戏曲的退化,因为去语言之真愈远了。现在把一部《乐府诗集》和一部《元曲选》比较一看,觉得《元曲选》里的词调好得多,使我们起这种感觉,固然不止一个原因,然而主要原因,总因为乐府整齐,所以笨拙,元曲参差,所以灵活。再把一部《元曲选》和十几本戏考比较一看,又要觉得生存的“京调”,尚且不如死了五百年的元曲,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敢断言道,“京调”根本要不得,那些“转声”、“助声”,正见其“黔驴技穷”,和八代乐府没奈何时,加上些“妃”、“豨”是一样的把戏。“京调”的来源,全是俗声:下等的歌谣,原来整齐句多,长短句少——这是因为没有运用长短句的本领——“京调”所取裁,就是这下等人歌唱的款式。七字句本是中国不分上下今古最通行的,十字句是三字句四字句集合而成,三字句四字句更是下等歌谣的句调。总而言之,“京调”的调,是不成调,是退化调。就此点而论,“京调”的上等戏,又和那些下等戏在一条水平线上了。照这看来,中国现在的戏界,不特没有进化到纯粹的戏剧,并把真正歌曲的境界,也退化出去了。
同学汪缉斋对我说,中国社会的心理,是极端的“为我主义”;我要加上几个字道,是极端的“物质的为我主义”。这种主义的表现,最易从戏曲里观察出来。总而言之,中国戏剧里的观念,是和现代生活根本矛盾的,所以受中国戏剧感化的中国社会,也是和现代生活根本矛盾的。
二改革旧戏所以必要
照上文所说,中国戏剧,既然这样下等,应当改革的道理,可就不多说了。但是关于旧戏的技术文学各方面,还有批评未到的地方,现在再论一番,作为改革旧戏所以必要的根据。
就技术而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举其最显著的缺点:第一是违背美学上的均比律(Law of proportion),譬如一架黄包车,安上十多支电灯,最使人起一种不美不快的感觉,这是因为十几支电灯的强度,和个区区的黄包车,不能均比。中国戏剧,却专以这种违背均比律的手段为高妙;《鸿鸾禧》上的金玉奴,也要满头珠翠,监狱里的囚犯,也要满身绸帛。不能彼此照顾,互相陪衬,处处给人个矛盾的,不能配合的现象,哪能不起反感。第二是刺激性过强。凡是声色一类,刺激甚易的,用来总要有节制;因为人类官能容易疲乏,一经疲乏,便要渐渐麻木不仁,失了本来的功用了。更进一层,人类的情绪,不可促动太高:若是使人心境顿起变化,有不容呼吸的形势,就大大违背“美术调节心情”的宗旨。旧戏里头,声音是再要激烈没有的,衣饰是再要花梢没有的;曲终歌罢,总少觉“余音绕梁”的余韵,只有了头昏眼花的痛苦。眼帘耳鼓都刺激疲乏不堪了,请问算美不算美?至于刺激心境,尤其利害,总将生死关头,形容得刻不容发,让人悬心吊胆,好半天不舒服。这种做法,总和美学原理,根本不相容。第三是形式太嫌固定。中国文学和中国美术,无不含有“形式主义”(Formalism),在于戏剧,尤其显著。据我们看来,“形式主义”是个坏根性,用到哪里哪里糟。因为无论什么事件,一经成了固定形式,便不自然了,便成了矫揉造作的了,何况戏剧一种东西,原写人生动作的自然,不是固定形式能够限制的。然而中国戏里,“板”有一定,“角色”有一定,“千部一腔,千篇一面”。不是拿角色来合人类的动作,是拿人类的动作来合角色;这不是演动作,只是演角色。犹之失勒博士(Dr.F.C.S.Schiller)批评“形式逻辑”道,“‘形式逻辑’不是论真伪,是论假定的真伪。”(此处似觉拟于不伦,然失勒之批评“形式逻辑”,乃直将一切“形式主义”之乖谬而论辩之其意于此甚近,但文中不便详引耳。)西洋有一家学者道,“齐一即是丑”(Uniformity means ugliness);谈美学的,时常引用这句话。就这个论点,衡量中国戏剧,没价值的地方,可就不难晓得了。第四是意态动作的粗鄙。唱戏人的举动,固然聪明的人,也能处处用心,若就大多数而论,可就粗率非常,美术的技艺,是谈不到的。看他周围的神气,尤其恶浊鄙陋,全无刻意求精、情态超逸的气概;这总是人心理的暴露,平素没有美术上训练的缘故。第五是音乐轻躁,胡琴一种东西,在音乐上,竟毫无价值可言:“躁音浮响,乱人心脾”,全没庄严润流的态度。虽然转折很多,很肖物音,然而太不蕴藉,也就不能动人美感了。旧戏的音乐,胡琴是头脑,然而胡琴竟是如此不堪,所以专就音乐一道评判旧戏,也是要改良的。上来所说五样,原不能尽,但是总可据以断定美术的戏剧,戏剧的美术,在中国现在,尚且是没有产生。
再就文学而论,现在的旧戏,颇难当得起文学两字。我先论词句。凡做戏文,总要本色,说出来的话,不能变成了做戏人的话,也不能变成唱戏人的话,须要恰是戏中人的话,恰合他的身份心理,才能算好,才能称得起“当行”。所以戏文一道,是要客观,不是要主观,是要实写的,不是给文人卖弄笔墨的。“昆曲”的词句,尚且在文学范围之内。然而卖弄笔墨的地方,真太利害了,把元“杂剧”、明“南曲”自然的本色,全忘干净了,所以渐渐不受欢迎了。“京调”却又太不卖弄笔墨了,翻开十几本戏考竟没一句好文章,全是信口溜下去,绝不见刻意形容、选择词句的工夫。这是因声造文,不是因文造声,是强文就声,不是合声于文。一言以蔽之,京调的文章,只是浑沌,无论甚人,都是那样调头儿。若必须分析起来,也不过一种角色,一种说话法,同在一个角色里头,却不因时因地,变化言词。这样的“不知乌之雌雄”,还有什么文学的技艺可说?我再论结构。中国文章不讲结构,原不止一端,不过戏文的结构,尤其不讲究。总是“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全没有曲折含蓄的意味。无数戏剧,只像是一个模刻下来的——有一个到处应用的公式。若是叙到心境的地方,绝不肯用寓情于事,推彼知此的方法,总以一唱完之大吉,这样办法,固然省事,然而兴味总要索然了。我再论体裁,旧戏的人物,不是失之太多,就要失之太少。太多时七错八乱,头绪全分不清楚了,太少时一人独唱,更不能布置情节,文学的妙用,组织的工夫,全无用武之地了。譬如“昆曲”里的《思凡》,文词意思,我都很恭维他,但是这样不成戏剧的歌曲,只可归到广义的诗里,算一类,没法用戏剧的法子去批评他。戏里这样一人独唱的,固是绝无仅有,然而举此例彼,那些不讲究的体裁,正是多着呢。照这看来,中国的戏剧文学,总算有点惭愧。
论到运用文笔的思想,更该长叹。中国的戏文,不仅到了现在,毫无价值,就当地的“奥古斯都期”,也没有什么高尚的寄托。好文章是有的,(如元“北曲”、明“南曲”之自然文学。)好意思是没有的,文章的外面是有的,文章里头的哲学是没有的,所以仅可当得玩弄之具,不配第一流文学。就以《桃花扇》而论,题目那么大,材料那么多,时势那么重要,大可以加入哲学的见解了;然而不过写了些芳草斜阳的情景,凄凉惨淡的感慨,就是史可法临死的时候,也没什么人生的觉悟。非特结构太松,思想里也缺少高尚的观念。就是美术上文学上做得到家,没有这个主旨,也算不得什么。大前年我读莎士比亚的《Merchant of Venice》,觉得“To baitfish withal……”一段,说人生而平等,何等透彻,这是“卢梭以前的《民约论》”。在我们元曲选上,和现在的“昆弋”、“京调”里,总找不出。我很盼望以后作新戏的人,在文学的技术而外,有个哲学的见解,来做头脑,那种美术派(Aesthetical School)的极端主张,是不中用的。
再把改良戏剧当做社会问题讨论一番。旧社会的穷凶极恶,更是无可讳言,旧戏是旧社会的照相,也不消说,当今之时,总要有创造新社会的戏剧,不当保持旧社会创造的戏剧。旧社会的状况,只是群众,不算社会,并且没有生活可言。这话说来很长,不是这篇文章里,能够全说的。约举其词,中国社会的里面,只是散沙一盘,没有精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差不多等于无机体。中国人却喜欢这样群众的生活,不喜欢社会的生活——这不就简直可说是没有生活吗?就勉强说他算有生活,也只好说是无意识的生活,你问他人生真义是怎样,他是不知道;你问他为什么叫做我,他是不知道。他是阮嗣宗所说大人先生袴裆里的虱子,自己莫名其妙的:他不懂得人怎样讲;他觉得戕贼人性以为仁义,犹之乎戕贼杞柳以为桮棬;他不觉得人情有个自然,有个自由的意志;他在樊笼里,却很能过活得,并且忘了是在樊笼里了——这是中国人最可怜的情形;将来中国的运命,和中国人的幸福,全在乎推翻这个,另造个新的。使得中国人有贯彻的觉悟,总要借重戏剧的力量。所以旧戏不能不推翻,新戏不能不创造。换一句话说来,旧社会的教育机关不能不推翻,新社会的急先锋不能不创造。
上面说的,都是新剧所以必要的根据。我还要声明一句,对于有知觉的人,这都算废话。
三新剧能为现在社会所容受否
戏剧应当改良的理论,纵然十分充足,若是社会全无容受的地方,也不过空论罢了。所以我们要考察现在社会的情形,能容新剧发生否。说到中国戏剧界,真令人悲观得很。一般“戏迷”正在那里讲究唱工、做工、胡琴的手段、打板的神通,新剧的精神,做梦还没梦到呢。记得一家报纸上说,“布景本不必要,你看老谭唱时,从没有布景,不过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搬来搬去,就显出地位不同来。西洋人唱做不到家,所以才要布景。”这种孩子话,竟能代表许多人,想在这样社会里造出新剧来,如何不难。但是细细考察起来,新剧的发生,尚不是完全无望。专就北京一部而论——其实到处都是这样——听戏的人,大概分为两种。第一种人是自以为很得戏的三味——其实是中毒最深的——听到旧戏要改良的话,便如同大逆不道一样,所以梅兰芳唱了几出新做的旧式戏,还有人不以为然,说:“固有的戏,尽够唱的,要来另作,一定是旧的唱不好了,才来遮丑。”你想和这种人还有什么理论,然而娴熟旧戏的人,差不多总是这样思想。第二种人在戏剧一道,原不曾讲究,不过为声色的冲动力所驱使,跑到戏园里“顾而乐之”,这种人在戏界里虽没势力,在社会上却占大多数,普通听戏的人,差不多总是这样。现在北京有一种“过渡戏”出现,却是为这一般人而作。所谓“过渡戏”者,北京通称新戏,但是虽然和旧戏不同,到底不能算到了新戏的地步,那些摆场做法,从旧的很多,唱腔没有去了。(有一个作戏评的人,造了这个名词,我且从他。)社会上欢迎这种戏的程度,竟比旧戏深得多;奎德社里一般没价值的人,却仗这个来赚钱,我有一天在三庆园听梅兰芳的《一缕麻》,几乎挤坏了,出来见大栅栏一带,人山人海,交通断绝了,便高兴得了不得。觉得社会上欢迎“过渡戏”确是戏剧改良的动机;在现在新戏没有发展的时候,这样“过渡戏”,也算慰情聊胜无了。既然社会上欢迎“过渡戏”比旧戏更很,就可凭这一线生机,去改良戏剧了。
说到新思想一层,社会上也不是全不能容受。我在旧戏里想找出个和新思想印合的来,竟找不出,只有“昆曲”里的《思凡》还算好的;看起来竟是一篇宗教革命的文章,把尼姑无意识的生活,尽量形容出来。这篇《思凡》本是《孽海记》的一出。就《孽海记》全体而论,也没甚道理可说,我这番见解,总算断章取义罢了。一个女孩儿,因为父母信佛,便送到庵里去,自己于佛书并未学过,佛家的宗旨,既然不知道,出家的道理,更是不消说,却囚在那里,如同入了隧宫一般,念那些全不懂得半梵半汉的佛经。什么思凡不思凡,犹可置而不论,只这无意识的生活,是最不能容忍的:跑下山去,也不过别寻一个有意识的生活罢了。(“只因俺父好念经”一段,下至“怎知俺感叹多”,把这个意思,形容尽致。)所以就这篇曲子的思想而论,总算极激烈的。但是一人独唱,全没情节,听戏的人,不能懂得这个意思,却无从照着社会上欢迎这篇戏的程度,来判断新思想的容受。我后来又找出“过渡戏”《一缕麻》是有道理的,这篇戏竟有“问题戏”的意味:细分起来,有几层意思可说:
(一)婚姻不由自主,而由父母主之,其是非怎样?
(二)父母主婚姻,不为儿女打算,却为自己打算,其是非怎样?
(三)订婚以后,只因为体面习惯的关系,无论如何情形,不能解约,明知火坑,终要投入,其是非怎样?
(四)忽而有名无实的丈夫,因极离奇的情节死掉了,他的妻以后的生活,应当怎样自处?在现在社会习惯之内,处处觉得压迫的力量,总要弄到死而后已。
(五)父、母、庶母、女儿间的关系,中表兄妹的关系——就是中国人家庭的状况——可以借此表见。
总而言之,这戏的主旨,是对于现在的婚姻制度,极抱不平了。在作原文的包天笑未必同我这见解一样,在演成戏剧的人和唱这戏的人,未必有极透彻的觉悟,然而就凭这不甚精透的组织,竟然很动人感情了。我第一次同同学去看,我的同学,当然受很大的刺激,后来又和亲戚家几位老太太去看,回来我问他们道:“觉得怎样?”他们说:“这样订婚,真是没道理。”咳!这没道理一句话,我想听人心里,总有这样觉悟,这点觉悟,就是社会上能容纳新思想的铁证。虽然中国人的思想,多半是麻木性的——不肯轻易因为没道理,就来打破这没道理——若使有人把这没道理说得透彻了,用法子刺激利害了,也就不由地要打破这没道理了。凭这一点不曾梏亡尽的“夜气”,“扩而充之”,不怕不能容受新思想。所以说到改良戏剧的骨子,还不算是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