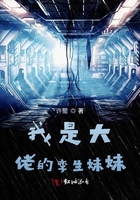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隋亡陈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取西洋历史以为喻,汉世犹之罗马帝国,隋唐犹之察里曼。后之罗马帝国名号相衍,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今桑原氏泯其代谢之迹,强合一致名曰“汉族极盛时代”,是为巨谬,其弊二也。凡此二弊,不容不矫。本篇所定之分期法,即自矫正现世普行桑原氏之分期法始。
以愚推测所及者言之,欲重分中国历史之期世,不可不注意下列四事:
(一)宜知中国所谓汉族于陈隋之间大起变化唐虞三代以至秦汉,君天下者皆号黄帝子孙,虽周起岐洴,秦起邠渭,与胡虏为邻,其地其人固不离于中国。故唐虞以降,下迄魏晋,二千余年间,政治频革,风俗迥异,而有一线相承,历世不变者,则种族未改是也。其间北秋南蛮,入居边境,同化于汉族者,无代无有。然但有向化而无混合,但有变夷而无变夏,于汉族之所以为汉族者,无增损也。至于晋之一统,汉族势力,已成外强中干之势。永嘉建兴之乱,中原旧壤,沦于朔胡,旧族黎民,仅有孑遗,故西晋之亡,非关一姓之盛衰,实中原之亡也。重言之,周秦魏所传之中国,至于建兴而亡也,所幸者,江东有孙氏。而后缔造经营,别立国家,虽风俗民情,稍与中原异质,要皆“中国之旧衣冠礼乐之所就,永嘉之后,江东贵焉”,为其纂承统绪,使中国民族与文化,不随中原以俱沦也。江东之于中原,虽非大宗,要为入桃之别子;讫于陈亡,而中国尽失矣。王通作《元经》书陈亡而具晋宋齐梁陈五国,著其义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民也。”(《元经》卷九)故长城公丧其国家,不仅陈氏之亡,亦是江东衣冠道尽(改用陈叔宝语)。江东衣冠道尽,是中国之亡,周秦汉魏所传之中国,至于建兴而丧其世守之域,至于祯明而亡其枝出之邦。祯明之在中国,当升降转移之枢纽,尤重于建兴,谈史者所不可忽也。
继陈者隋,隋外国也。继隋者唐,唐亦外国也。何以言之?君主者,往昔国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虏,其不纯为汉族甚明。唐之先公曾姓大野,其原姓李氏而赐姓大野欤?抑原姓大野而冒认李姓欤?后人读史,不能无疑也。此犹可曰一姓之事,无关中国也。则请举其大者言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后南朝,正魏周而伪齐陈,直认索虏为父,不复知南朝之为中国,此犹可曰史家之词,无关事实也。则请举其更大者言之,隋唐将相,鲜卑姓至多,自负出于中国甲族之上,而皇室与当世之人,待之亦崇高于华人。此犹可曰贵族有然,非可一概论也。则请举其民俗言之,琵琶卑语胡食胡服(见《颜氏家训》、《中华古今注》等书),流行士庶间,见于载记可考者甚繁,于此可知隋唐所谓中年,上承拓拔宇文之遗,与周汉魏晋不为一贯,不仅其皇室异也,风俗政教固大殊矣。为史学者不于陈亡之日分期判世,而强合汉唐以一之,岂知汉唐两代民族颇殊,精神顿异,汉与周秦甚近,而与唐世甚远,唐与宋世甚近,而与南朝甚远,此非以年代言也,以历朝所以立国所以成俗之精神察之,然后知其不可强合。今吾断言曰,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不蒙前代者也。
(二)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自隋迄宋,为“第二中国”,既如上所述矣,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自隋至于唐季,(五代之名甚不可通,中原与十国地丑德齐,未便尊此抑彼,其时犹是唐之叔世,与其称为五季,不如称为唐季,可包南北一切列国,说详拙著札记。)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虽年世愈后,胡气愈少,要之胡气未能尽灭。读唐世史家所载,说部所传,当知愚言之不妄也。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说明之曰“第二中国”,上与周汉魏晋江右之中国对待,分别可也。此“第二中国”者,至于靖康而丧其中原,犹晋之永嘉;至于祥兴而丧其江表,犹陈之祯明;祥兴之亡,第二中国随之俱亡,自此以后,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祥兴于中国历史之位置,尤重于祯明,诚汉族升降一大关键也。
(三)宜据中国种族之变迁升降为分期之标准如上所云,“第一中国”、“第二中国”者,皆依汉族之变化升降以立论者也。陈亡隋代,为汉族变化之枢纽,宋亡元代为汉族升降之枢纽,今为历史分期,宜取一事以为标准,而为此标准者,似以汉族之变化升降为最便。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诚以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种族有其种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今取汉族之变化升降,以为分期之标准,既合名学“分本必一之说”,又似得中国历史上变化之扼要,较之桑原氏忽以汉族盛衰为言,忽以欧人东渐为说者,颇觉简当也。
(四)宜别作“枝分”(Subdivsion)勿使与初分相混。如上所言,既以汉族之变化与升降,为上世、中世、近世分期之标准,而每世之中为年甚长,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别作“枝分”,使之纲目毕张。兹以政治变迁为上世枝分之分本,风俗改易为中世枝分之分本,种族代替为近世枝分之分本,合初分与枝分图为下表而说明之:
甲、上世
(一)上世第一期周平王元年以前。(二)上世第二期起周平王元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三)上世第三期起秦始皇二十六至晋建兴五年。
乙、中世
(四)上世第四期起晋建兴五年至陈祯明三年。(五)中世第一期起陈祯明三年即隋开皇九年至后周显德六年。(六)中世第二期起宋建兴元年即显德六年之次年至祥兴二年。
丙、近世
(七)近世第一期起宋祥兴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至至正二十四年。(八)近世第二期起元至正二十四年即韩氏龙凤十年至明永历十五年。(九)近世第三期起明永历十五年即清顺治十八年至宣统三年。
丁、现世至民国建元以来。
说明上世、中世、近世之所由分,与中世第一、第二两期之所由分,俱详前。
周平王东迁以前,世所谓唐虞三代,此时期中虽政治不无变化,而其详不可得闻,既无编年之史,(竹书纪年不足信。)又多传疑之说,(夏殷无论,即如两周之文王受命周公居东厉王失国诸事,异说纷歧,所难折衷。)惟有比而同之,以为“传疑时代”,盖平王以降,始有信史可言也。
东周数百年间,政治风俗,上与西周有别,下与秦汉异趣,其时学术思想昌明,尤为先后所未有,故自为一期。
上古第三期,括秦汉魏西晋四朝,为其政治成一系也。
上古第四期,括东晋宋齐梁陈五朝,为其政治成一系,风俗成一贯也。
近世第一期,括蒙古一代,第二期,括明朝始终,第三期,括满清一代,近世独以朝代为分者,以朝代之转移,即民族势力之转移故也。
分世别期,最难于断年,前期与后期交接之间,必有若干年岁为过渡转移时代,合于前世既觉未安,合于后期更觉不可,今为画一之故,凡过渡时代均归前期,如上世中世之交,有数朝为过渡转移期,全以归于上世,必于陈亡之后,始著中世。又如上古第一期与第二期之交,周赧入秦,与始皇一统间,数十年为过渡期,今以附于第一期,必俟六国次第以亡,然后著第二期。一切分期,除近世第一期外,俱仿此。近世第一期所以独为例外者,以元人入中国与往例不同,未入中国时,固在朔漠号称大汗,既摈出之后,又复其可汗之名,此于中国纯为侵入,故第一第二期间,以吴始建国为断,不以顺帝北去为断。
分中国历史为如是三世,固觉有奇异之感焉,则三世者,各自为一系,与上不蒙而上世中世又有相似之平行趋向是也。北魏北周第二期之缔造时与上不相蒙者也,辽金第三期之缔造时与上不相蒙者也,中世之隋唐,犹上世之秦汉,同为武功极盛之世。隋之一统与秦之一统,差有相似之点。中世之北宋,犹上世之魏晋,同为内政安人、外功不张之世。中世之南宋,犹上世之江左,同为不竞之世。南宋之亡,尤类陈亡,此上世中世平行之趋向,不待详言者也。中世与近世趋向绝殊,固由承宇文者为隋代,完颜者为元辽,与魏晋与周已不可强同,元隋更大异其性,此后之历史遂毫无相似者矣。简言之,上世一系之中,所有朝代,但有相传而无相灭;中世一系之中,亦但有相传,而无相灭;近世一系之中,但有相灭,而无相传,是非以帝族言也。以其立国之道察之,如是云尔。
余为此分期法,读者宜有所疑,以谓“梁陈不竞半虏之隋唐代承统绪,本汉族甚不名誉之事,如今日通行之分期法合汉唐而一之,此丑可掩,今分而为二,非所以扬历史之光荣也。”余将答此说曰,学问之道,全在求是,是之所在,不容讳言其丑。今但求是而已,非所论于感情。余深察汉唐两代实不能比而同之,纵便违心徇情,比而同之,读史者自可发觉,欺人无益也。陈隋间之往事,曷尝不堪发愤,要不可与研究史学之真相混合言之。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有几位北大同学鼓励我在本日特刊中写一篇蔡先生的小传。我以为能给蔡先生写传,无论为长久或为一时,都是我辈最荣幸的事。不过,我不知我有无此一能力。且目下毫无资料,无从着笔,而特刊又急待付印,所以我今天只能写此一短文。至于编辑传记的资料,是我的志愿,而不是今天便能贡献给读者的。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特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严词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一)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DD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D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但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二)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名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
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三)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作大将。”蔡先生说时,声色俱厉,我的酒意也便醒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贵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