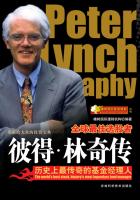本志同人皆今日学生,或两年前曾为学生者,对于今日一般同学,当然怀极厚之同情,挟无量之希望。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鹰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径途,尽力研求,喻之于众。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其他更有专文论次。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同人浅陋,惟有本此希望奋勉而已。此本志第四责任也。
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近之径途,小节出入,所不能免者。若读者以“自相矛盾”见责,则同人不特不讳言之,且将引为荣幸。又本志以批评为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若读者以“不能持平”腾诮,则同人更所乐闻。
既以批评为精神,自不免有时与人立异,读者或易误会,兹声明其旨。立异之目的若仅在于立异而止,则此立异为无谓。如不以立异为心,而在感化他人,但能本“哀矜勿喜”之情,虽言词快意为之,要亦无伤德义。同人等所以不讳讥评者,诚缘有所感动,不能自己于言。见人迷离,理宜促其自觉之心,以启其向上之路;非敢立异以为高。故凡能以学问为心者莫不推诚相与;苟不至于不可救药,决不为不能容受之诮让。然而世有学问流于左道,而伪言伪旨足以惑人者,斯惟直发其覆,以免他人重堕迷障。同人等皆是不经阅历之学生,气盛性直,但知“称心为好”,既不愿顾此虑彼,尤恨世人多多顾虑者。读者想能体会兹意,鉴其狂简也。
本志虽曰发挥吾校真精神,然读者若竟以同人言论代表大学学生的思潮,又为过当。大学学生二千人,同人则不逾二十,略含私人集合之性质;所有言论由作者自负之,由社员共同负之。苟有急进之词,自是社中主张,断不可误以大学通身当之。
发刊伊始,诸待匡正,如承读者赐以指教,最所欢迎。将特辟通信一栏,专供社外人批评质询焉。
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
近年坊间刊行之中国文学史,于分期一端,绝少致意。竟有不分时代,囫囵言之者;间为分期之事,亦不能断画称情。览其据以分期之意旨,恒觉支离:此亦一憾事也。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规定分中国文学史之教授为三段:一曰上古,自黄帝至建安;二曰中古,自建安至唐;三曰近古,自唐至清朝。似此分法,大体可行;然于古今文学转变之枢机,尚有未惬余意者。就余所知,似分四期为宜。今列举如左:
一、上古。自商末叶至战国末叶。
二、中古。自秦始皇统一至“初唐”之末。
三、近古。自“盛唐”之始至明中叶。
四、近代。自明弘嘉而后至今。
谈文学史者,恒谓中国文学始于黄帝:此语骤观之似亦可通,细按之则殊未允。黄帝时书皆不传,今但有伪内经而已。虽残缺歌谣,有一二流传至今,正不能执此一二残阙歌谣,以为当时有文学之证。何者?此一二残缺歌谣,不足当文学之名也。其后有所谓《虞书》者,今所传《尧典》(伪孔《舜典》在内)是也。此篇文辞,大类后人碑铭墓志,决非荒古之文。寻其梗概,与《大戴礼记》中宰予问、五帝德无殊。开始即曰“稽古”,作于后代可知。意者同为孟子所谓传,汉世所谓儒家所传之书传;其后真《尧典》亡佚,遂取《尧典》之传以代之(说详拙著《尚书十论》)。《尧典》既不可据,则当时文学,不可得言。《虞书》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语;《尚书大传》载云卿之歌。舜时文学,似已可谓成立矣。然《虞书》仅有诗之名,诗之实未尝传于后代,卿云诸歌,又未可确信为真。故不能以虞代为中国文学所托始,“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郑康成《诗谱序》语)。其他散文,《禹贡》、《甘誓》颇可信。然《禹贡》仅言地理,《甘誓》不过诏令,不足当文学之名。至于商朝,虽郑康成以为“不风不雅”,而颂实存。古文家以《商颂》为商代之旧,由今文家言之,则西周之末正考父作。今以《商颂》文词断其先后,似古文家义为长。(余固从今文非古文者,独此说不可一概论。)纵以颂非商旧,而风中实有殷遗。《周南·汝坟》之二章云,“鲂鱼頳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此为殷末之作,决然无疑。(汝坟为殷畿内水。)又《关雎》篇云,“在河之洲。”章太炎先生云,“南国无河!岐去河亦三四百里。今诗人举河洲,是为被及殷域,不越其望。且师挚殷之神瞽:殷无风,不采诗,而挚犹治《关雎》之乱,明其事涉殷。”此《关雎》为殷诗之确证。今第一期托始于商者,以《商颂》存于后世,商末诗歌犹可见其一面,至于前此而往,自黄帝至于夏年,以理推之,不可谓无文学,然其文学既不传于后世,断不可取半信半疑之短歌以证其文学,惟有置之。编文学史而托始黄唐虞夏,泰甚之举也。
西周文学大盛矣:韵文则有“诗”,无韵文则有“史”有“礼”。从文学之真义,“礼”不能尸文学之名;然舍“礼”而仅论雅颂豳风二南,其文学固可观也。东周可谓中国文学最自由发达之时代。约而论之,可分六派。一曰“诗人”之文学邶以下之风,(除豳)与所谓“变雅”者是。二曰“史家”之文学,《国语》(《左传》在内)《战国策》、《吴越春秋》、《越绝书》是。(此数种未必尽真。)三曰“子家”之文学,孔子之《易系》,子思之《中庸》,《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之类是。四曰“赋”之文学,荀卿之“赋”是。(荀“赋”之体,必当时有之,作者谅不仅荀子一人,特传后者,惟荀子耳。)五曰“楚辞”之文学,屈平宋玉景差所为者是。六曰歌谣之文学,散见之歌谣是。凡此诸派,各不相同,然有普遍之精神,则自由发展,有创造之能力,不遵一格是也。故以文情而论,同在一时,而异其旨趣;以形式而论,师弟之间而变其名称。(屈辞宋赋体各不同。)今试执此时所出产之文学互比较之,有二家相同者乎?无有也。是真可谓中国文学最自由之时代矣。降至汉朝,此风顿熄。夫知东周之政治思想,不与秦汉侔,则知东周文学不可与秦汉合也。
自秦至于“初唐”为中国骈俪文学历层演化之期。此时期间,文学之推移、恒遵此一定趋向,不入他轨。若前期之自由发展,不守一线者,概乎未之闻焉。秦代文学特出者,李斯一人耳。此人之推翻东周文学,犹其推翻东周政治与思想也。李斯之文今存者,当以诸刻石与《谏逐客书》为代表。刻石之文,一变前人风气;诚如李申耆所云,“亦焚诗书之故智。”其赫赫之情,与其四字成章之体,后世骈文之初祖,“庙堂制作”之所由防也。《谏逐客书》一文,多铺张,善偶语,直类东汉之文矣。西汉司马相如扬雄之赋,用古典,好堆砌;故虽非骈文,而为后世骈文树之风声。(汉赋乃楚辞之变,文体差近,故分文学时代者,每合楚汉为言。其实楚辞汉赋,貌同心异,论其质素,绝不侔也。)至于东汉魏晋之世,竟渐成对偶铺排之体。宋齐而降,规律益严。至于陈周之徐庚,“初唐”之王杨,骈体大成矣。此将千年间,直可谓风气一贯。自李斯始,俪体逐渐发达,经若干阶级,直至文成骈,诗成律,然后止焉。此时期中,岂少不遵此轨者。若汉之贾谊,犹存楚风,枚乘五言,不同词赋,王充好以白话人文,陶忛不用时人之体。然皆自成风气,为其独至。或托体非当时士大夫所用之裁,(如枚乘五言之体,在当时不过里巷用之,士人不为,东汉以后,士人始渐作五言耳。)或文词不见重于当代,(如王充。)或仅持前代将沫之风,(如贾谊之赋。)或远违时人所崇,(如陶忛是。当时时尚之五言诗乃颜谢一派,而非陶也。)皆不能风被一世。其风被一世者,皆促骈文之进化者也。平情论之,中国语言为单音,发生骈文律诗之体,所不能免也。然以骈文之发达,竟使真文学不能出现,此俳优偈咒之伪文学,乃充满世间,诚可惜耳。此时期中,惟有五言诗杂体诗为真有价值之文学。然五言至于潘陆中病已深;齐梁以后,成为律体,更不足道焉。
骈文演进,造于极端,于是有革命之反响。此革命者,未尝明言革命,皆托词曰复古。虽然,复古其始也。自创其继也;复古托词也;自创事实也。贵古贱今,中国人之通性。不曰复古,无以信当世之人。然其所复之古,乃其一己之古,而非古人之古。此种革命之动机,酝酿于隋唐之际,成功于“盛唐”之时。隋炀唐太,皆有变古之才。至于“盛唐”,诗之新体大盛;至于“中唐”,文之新体大盛;六朝风气渐歇矣。以文体言,唐代新体有数种:七言诗,(六朝人固有七言,如鲍照之伦,然不过用于歌曲,偶一为之,未能成正体。)词,新体小说等是。世谓开元元和之世,诗多创格,不为虚语。以文情论,六朝华贵之习渐堙,唐代文学,渐有平民气味,即是以观,不谓唐文学对于六朝为新文学不可也。宋元文学又多新制。要之,此时期中,可谓数种新文学发展期。其与第二期绝不同者,彼就骈文之演进,一线而行;此则不拘一格,各创新体,亦稍能自由者也。又此期之新文学,可分二类。甲为不通俗的新文学;若杜子美白香山之诗,韩退之柳子厚之文,以至宋人之散文七言诗等是。此种文体,含复古之性质。乙为通俗之新文学。如白话小说词曲剧等是。此种文体,唐代露其端,宋元成其风气。以文学正义而论,此最可宝贵者也。乃二种新文学演化之结果,甲种据骈文专制之地位,囊括一世,乙种竟不齿于文学之列。寻其所由,盖缘为乙种新文学者,不能自固其义,每借骈文律诗之恶习以自重;因而其体不专,其旨不能深造,其价值不能昭著。且中国之暗乱政治,惟有骈文可以与之合拍;固不容真有价值之通俗文学,尽量发达也。
词曲之风,明初犹盛,故明之前叶,宜归于第三期。然自弘治嘉靖而后,所谓“前后七子”者出,倡复古之论。于是文复古,诗亦复古,词亦复古。戏曲无古可复,则捐弃不道;道之者则变自然之体,刻意卖弄笔墨;是直不啻戏剧之自杀。其后则有经学之复古,今文学之复古。自明中叶至于今兹,皆在复古期中。经学今文学之复古,有益于学问界者甚大。盖前者可使学人思想近于科学(汉学家),后者可为未来之新思想作之前驱(今文学派)。独文学之复古,流弊无穷。故中国人之“李奈桑斯”,利诚有之,害亦不少也。条举其弊,则文学之美恶,无自定之标准,但依古人以为断;于是是非之问题,变为古不古之问题。既与古人求其合,必与今人成其分离。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In human Literature)。质言之,此时期中最著之文学家,下之仅是隶胥,上之亦不过书蠹。虽卓异之才,如毛奇龄恽敬龚自珍者亦徒为风气所囿,不能至真文学之境界,不得不出于怪诞。固亦有不随时流,自铸伟辞,若曹雪芹、吴敏轩者;然不过独善其文,未能革此复古之风气也。
中国文学史既分为如是四期;今再为每期定一专名,以形容之。
第一期,上古。“文学自由发展期。”
第二期,中古。“骈俪文体演进期。”
第三期,近古。“新文学代兴期。”
第四期,近代。“文学复古期。”
今中国之新文学已露萌芽,将来作文学史者如何断代,未可逆料,要视主持新文学者魄力如何耳。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凡研治“依据时间以为变迁”之学科,无不分期别世以御纷繁。地质史有“世纪”、“期”、“代”之判,人类进化史有“石世”、“铜世”、“铁世”、“电世”之殊。若此类者,皆执一事以为标准,为之判别年代。一则察其递变之迹,然后得其概括;一则振其纲领之具,然后便于学者。通常所谓历史者,不限一端,而以政治变迁、社会递嬗为主体试为之解,则人类精神之动作,现于时间、出于记载为历史;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为历史之学。历史学之所有事原非一端,要以分期为之基本。置分期于不言,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无术以得其简约,疏其世代,不得谓为历史学也。世有以历史分期为无当者,谓时日转移无迹可求,必于其间斫为数段,纯是造作。不知变迁之迹,期年记之则不足,奕世计之则有余,取其大齐以判其世,即其间转移历史之大事,以为变迁之界,于情甚合,于学甚便也。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之中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返观中国论时会之转移,但以朝代为言,不知朝代与世期,虽不可谓全无关涉,终不可以一物视之。今文春秋有“见闻”、“传闻”之辨,其历史分期之始乎春秋,时代过短,判别年限又从删述者本身遭际而言,非史书究义,后之为史学者,仅知朝代之辨,不解时期之殊,一姓之变迁,诚不足据为分期之准也,日本桑原骘藏著《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寻桑原氏所谓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似此分期,较之往日之不知分期但论朝代者,得失之差,诚不可量。然一经中国著史学教科书者尽量取用,遂不可通。桑原氏书虽以中华为主体,而远东诸民族自日本外,无不系之,既不限于一国,则分期之谊,宜统合殊族以为断,不容专就一国历史之升降,分别年世,强执他族以就之。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中国学者强执远东历史之分期以为中国历史之分期,此其失固由桑原,又不尽在桑原也。且如桑原所分尤有不可通者二端,一则分期标准之不一,二则误认历来所谓汉族者为古今一贯。请于二事分别言之。凡为一国历史之分期者,宜执一事以为标准,此一事者一经据为标准之后,便不许复据他事别作标准,易词言之,据以分割一国历史时期之标准,必为单一,不得取标准于一事以上。如以种族之变迁分上世与中古,即应据种族之变迁分中世与近世,不得更据他事若政治改革、风俗易化者以分之。若既据种族以为大别,不得不别据政治以为细界,取政治以为分本者,但可于“支分”中行之(Subdivision),不容与以种族为分别者平行齐列。今桑原氏之分期法,始以汉族升降为别,后又以东西交通为判,所据以为分本者,不能上下一贯,其弊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