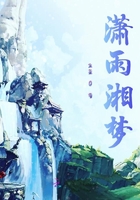西门残雪行走在夜色中。
夏日的势头已过,晚风携起了微漠的凉意。建康城在经历了一个人心惶惶的夏季之后,终于迎来了秋天。
夏天的逝去并未携走乱世的尘埃,夜后依然戴着鎏银面具出没于王侯将相府邸,绝杀笺漫天飘散,收到它的人,就只有被夜后强势夺魂的命运。十五天如同与鬼神定下的生死契约,没有人能逃过“绝杀十五”的死咒。
今天下午韩铮收到了来自总堂的信笺,信中说长老给西门残雪的时间已剩不多,尽管她为了阻止夜后而负伤至今没有痊愈,但时间并不容许脚步的放缓,夜后的行为已经愈发地令人发指,若不继续采取行动,怕是来不及了。跟月行舟的利益相比,所有的怜悯与慈悲皆是虚妄,于是在这股无形压力的催促下,入夜之后韩铮与西门残雪在建康分头行动,欲再次从各个暗茬处获取关于夜后行踪的线索。
西门残雪右肩与左腿的伤经过近两个月的休养已有了明显的好转,在街头巷尾奔走已不成问题,但短期还是不宜动武。
这是一场宿命与执念的赌局,她欣然而赴。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西门残雪今夜一身淡雅之装,藕色心字罗衣两重,一件流云纹绘的薄氅加身,乌黑的青丝绾成了慵懒精致的发髻。她极度厌恶这身打扮,但是为了掩盖眼中的戾气,用韩铮的话说,她“务必要自我委屈一下了”。
在市井中走马观花地行了一程,西门残雪站定在装潢体面的酒坊前,她抬起头,看着酒坊门口的灯笼在徐徐的晚风中轻摇,洒下一地的斑斓。
栖月阁。
西门残雪定了定神,缓步踏入。
落座在栖月阁二层靠楼梯口的桌边,西门残雪环顾四周,酒客形形色色,或举杯论道,或低头独酌。紫陌红尘,众生百态,一杯微甘的醇酒荡不尽世事的悲苦,霓虹百翦之下,是不忍问津的暗黑漩涡。
“请问客官想来点什么?”那名唤作小南的店小二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
“一壶云熹冻酒。”西门残雪淡淡地说。
“客官要不试试青醴?”小南殷勤地向这位面色冰寒的女酒客推荐栖月阁的招牌,“青醴是栖月阁的一绝,来栖月阁若不尝尝青醴,将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不了,上次来的时候已有品尝。”西门残雪轻轻摆了摆手,嘴角带着游丝般的笑意,“这次前来,新酒换旧酿,尝点别的。”
“好嘞,客官稍等啊!”小南应着,转身跑开了。
新酒换旧酿。西门残雪相信小南能懂。
继而她上身向后仰下,靠在椅背上,懒懒地抬起眼打量楼梯口来来往往的酒客。来建康之后,她很少一个人在街坊闲游,平日里不是跟白氏兄妹呆在一起、随众人一同出去走走,就是与韩铮碰头、揣摩上面的计划。静下来的时候,西门残雪会想,若不是背负着这般沉重的命格,自己或许只是一个在月行舟总堂混迹的普通成员,历练、试手、磨剑、杀人,闲下来便可以独自在武陵的酒坊消磨时光,断不会像今夜这样,佯装出一副悠闲散漫的模样,心中却在步步为营地盘算如何与月行舟的眼线用旁人不易察觉的暗语交换情报。
过了很久,小南才端着一个放着酒壶的托盘过来。
“客官久等了。”小南满脸堆笑,小心翼翼地将云熹冻酒放在木桌上。
“晚来也就罢了,可还忘了拿酒杯。”西门残雪挑挑眉,微微仰起脸,带着一丝无奈的笑容打量着他,“你这小二是怎么当的?”
“唉,坏了!客官息怒,怪小的疏忽,马上给客官拿去!”小南猛省,一拍脑袋,将托盘放在木桌上,转身跑开了。
西门残雪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然后坐直了身体,一只手细细摩挲着细腻精致的酒壶,另一只手探到托盘边,一根手指轻抬托盘,一根手指以极快的速度往托盘下面一勾,一封压在托盘下面的信函顺势滑进罗衣宽大的袖口,整串动作做得行云流水,不留丝毫破绽。
未几,小南拿着一只酒盏折了回来,恭恭敬敬地放在木桌上:“客官慢用。小的坏了客官的兴致,客官见谅。”
“无妨。”西门残雪再度摆了摆手,“来栖月阁喝酒,本就没有时间的概念,我不急的。”
小南听了,乐呵呵地附和着笑道:“哪里,这世道多乱啊,怎能不急?”
“世道荒乱,小心着走便是,何必惶惶不可终日?”西门残雪淡淡地说。
“不慌也不行了啊,连乘舟的人都要随时提防着漩涡。”
乘舟的人。西门残雪会意,抬头看着小南乌亮的眼睛,这个长期在栖月阁跑堂的少年穿一身陈旧的布袍,肩上搭着抹布,若不是话语里透着点点暗示,西门残雪差点都以为他已经淡忘了自己最初的信念。“天下已混乱至此,夜魂游弋,长歌当哭,何苦用抓不住的时间禁锢自己?”
“客官你就不明白了哇,连十里秦淮那样的脂粉地儿都漂浮着血腥味。”小南想了想,继续说,“据说如果要让那股腥味儿散尽,得不争不杀至少两个月。”
“哦?”西门残雪眉峰一挑,“这位小哥懂的挺多的嘛。”
“嗐,都是来这里喝酒的那些公子哥儿说的,小的听到,就捡着了呗。”小南憨憨地笑着,抓了抓脑袋。
“好罢。”西门残雪低声笑了,斟上一杯云熹冻酒,“你去忙罢。”
“好嘞,客官有事就叫我啊!”小南哈了哈腰,转身跑开了。
西门残雪端起杯盏,不紧不慢地品着云熹冻酒,接下来她需要做的,仅仅是优哉游哉地将这壶佳酿饮完。
云熹冻酒的名气虽不及青醴,却也在众酒客中颇有口碑。不同于青醴的甘冽沁脾,云熹冻酒的口感醇浓厚重,下肚之后又会回泛起丝缕凉意,有如被冰镇了一般,遂被名为“冻酒”。
夜魂。秦淮。两个月。
西门残雪慢慢地喝着酒,心中反复揣摩着这几个词,总堂传来的一纸信函还在轻罗衣衫的袖口中,待她饮完这壶云熹冻酒回去与韩铮会和之时再拆开。
她曾经确实是无酒不欢之人,武陵的酒肆常有她低头独酌的身影,亭台楼阁上也不时能听到她乘着酒兴翩然而奏的飞扬笛音。
但终究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自己在建康步步谨慎地生存,在夹缝中万分小心地抠取着关于那个妖魔的一点点情报。西门残雪觉得自己到底还是会累的,像今夜这样悠然地坐在建康最好的酒坊喝酒已是一种奢望,奈何袖口里的一封信函却让一切都变得沉重起来。
西门残雪心中苦笑,脸上却装出轻松惬意的模样。她右手秉着酒盏,食指轻轻敲击着杯身,她徐徐转动头部,再度打量起四周形形色色的酒客。
蓦地,西门残雪敲击杯盏的手指不动了,整个人稍稍绷了起来,定定地看向远处临窗的一桌。
叶归澜背对着她坐在窗边,背脊微微有些佝偻,正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纵使只是一个背影,却是道不尽的寂寞孤单。
十里秦淮。
韩铮披一身夜色,打开了分堂的门扉,淡淡的霉味扑面而来。韩铮面不改色,在这里住了数日,他早已习惯了鼻尖的这缕异味。
屋里一片漆黑,西门残雪还未归来。韩铮沉吟片刻,在黑暗中轻车熟路地找到火镰,点亮了木桌上一支快燃尽的蜡烛。昏暗的烛光照亮了狭小的厅堂,韩铮坐在了木桌边,从怀里掏出一纸信函,在烛光下缓缓展开。摇曳的烛光辉映在他枯槁的脸庞上,伴着他鹰隼般透着缕缕锐气的眼睛,阴恻而寒冷。
阅着信函的内容,韩铮的面色逐渐凝重起来,继而他长久地吐了一口气,将信笺放到火烛上,火舌舔了上来,信笺慢慢化为了灰烬。
木门咿呀一声叫人推开,西门残雪缓步踏入。韩铮静了片刻,抬起了头:“姗姗而归啊。”
“那壶云熹冻酒喝得慢了,误了些时辰。”西门残雪掩上门扉,将薄氅取下,随手扔在了一旁的桌案上。
“难得的兴致,多享受片刻也无妨。”韩铮释怀地笑了笑。
“这兴致,消受不起。”西门残雪冷哂一声,走到韩铮对面坐下,隔着跳动的烛火,与他默默相对。
气氛沉闷良久,韩铮打破了沉默:“上面怎么说?”
“信我还没看,怕是计划有了改动。”西门残雪声音淡漠,然后她一扬衣袖,信函从轻罗衣衫的袖口中飞出,斜斜地落在韩铮跟前。
韩铮从木桌上捡起信函,慢慢打开。
西门残雪不语地看着他,眼中的戾气在烛火温暖光芒的映射下,却是愈发的阴寒渗人。
阅罢,韩铮看向西门残雪:“上面说,给你的时间,再宽限两个月。”
“果然。”西门残雪轻哼一声道,“我在栖月阁听着‘云歌’的话,差不多都猜到了。”
“是么?”韩铮扯了扯嘴角,笑容干涩,“信中还说,长老分析夜后的势头,估计她短时间内不会收手,再加上你为组织负伤不轻……”
“可以不提这事了么?”西门残雪冷冷地打断了韩铮的话,颇为不耐。
“好罢,这只是上面的意思。”韩铮怔了片刻,无奈地笑了笑,继续说,“然后鉴于这些因素,上面再宽限你两个月。”
“知道了。”西门残雪凉凉地道。
“你不看一下么?”韩铮朝她扬了扬信笺。
“不了,烧了罢。”西门残雪摆了摆手,她微微侧脸,瞥见了木桌上的灰烬,眼神动了动,“你那边呢?”
“上面给我的指示,不过就是协助你,尽早拔除夜后这根芒刺,仅此而已。”韩铮轻描淡写地说着,将信笺放到了火烛上,烛火爆起了明亮的光芒,火舌****之后,点点灰烬散落下来,覆盖了之前的那一层。
西门残雪看着灰黑的烬末飘撒下来,突然想起了另一桩事:“在栖月阁的时候,偶然遇见了叶家公子。”
“叶家公子?”韩铮愣了片刻,“他没觉察到什么罢?”
“没有的罢。”西门残雪漫不经心地拈着灰烬,“他能觉察到什么?”
“你们不是认识么?”
“认识又如何?他座位跟我离得远,又是背对着我,能觉察么?”西门残雪面带讥嘲。她本想说白府的人与自己更加熟识,不也对自己来建康的真实目的一无所知么?但她想了又想,还是没有将话说出口。
“罢了,没有照面便无妨,我多心了。”韩铮自嘲地笑道。
西门残雪没有言语,眼中深重的戾气映着跳动的烛光,满是萧寒。
初秋的深夜,她与韩铮相对而坐,烛火发出哔哔剥剥的声响,摇曳出满地的冷清。
天气清明,轻风微凉。
莫府。
莫霭坐在老榕树粗壮的树干上,晃着双腿嚼着锦糖酥,歪着脑袋看不远处叶归澜与江岩沐着初秋轻拂的微风过招试手。叶归澜在今天一大早莫霭还没想好去哪里消遣的时候提着血馥来到莫府,说很久没有与江岩过招了,想练练手。江岩欣然答应,遂与年轻人在府院的空地上拉开了阵势。
叶归澜手持血馥,起手落刀之间尽显沉稳之态。他知道自己这与理想的层次仍有一段距离,但比起几个月前的生涩,自己的刀术已在杀父之仇的驱使下有了令人称奇的进步。
江岩长剑在手,步步谨慎地接着年轻人娴熟的招法,这个少年白皙的脸上渐渐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他还记得初识叶归澜的时候,莫霭总是打着“我就是叶大侠的朋友”的旗号,隔三差五地往叶府跑,叶归澜生性淡漠孤单,不愿出门游玩,于是自己常常拿着佩剑陪他练刀。那时候正值建康的雨季,在纷飞的烟雨中,这个年轻人运着乌青色的长刀,神情落寞而幽深,任凭烟雨湿了衣衫,却一直固执地练着。而今几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今日再度试手,江岩明显感觉到叶归澜今日演武虽未出狠招,自己却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了。
叶归澜上前一步,翻腕扬手又是一记斜斩!江岩侧移横挡,凌厉的妖刀斜劈在剑锷上。少年只觉得虎口一疼,刹那间剑已脱手,随着叶归澜的收势打着旋儿飞出老远。
佩剑落地,发出铮鸣的声响,一切又重归于平静。叶归澜将血馥收在身后,静默地看着赤手空拳的少年。
江岩静立半晌,缓缓笑道:“叶公子刀法突飞猛进,江岩甘拜下风。”
“江兄弟承让。”叶归澜淡淡地说。
“叶公子的刀法使得游刃有余,却是招招留情,刀路亦不在主线上。”江岩看着叶归澜萧索的眼睛,料及主上与叶归澜熟识的关系,将方才试手的感悟尽数道了出来,“叶公子是有什么顾虑么?”
叶归澜的眼神动了动,微微讶异于少年的敏锐:“我……”
“两个男人,哪来这么多废话?!”
叶归澜和江岩同时一愣,一同转头看向那个被他们遗忘很久的女孩子。
莫霭在树上百无聊赖地坐了好久,好不容易看到二人的试手告一段落,却又开始说一些在她看来无关痛痒的话,不由地烦躁起来。
“那……我退下了。”江岩尴尬地笑了笑,拭去了鼻尖上的汗珠,向一边走了一小程,将地上的佩剑捡起来推进剑鞘,转身离开了。
莫霭从树干上跳了下来,走到叶归澜跟前,抬起下颌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红褐色的眸子神色复杂。
“胜了石头,又逞能了是不?”莫霭偏着脑袋看着他。
叶归澜慢慢地收了血馥,默默地与女孩子红褐色的眼瞳相视,没有说话。
莫霭又看了他一阵,上前一步,掏出一张方绢,替叶归澜拭干了他额头上的一层薄汗。温软的暖香直扑年轻人的鼻息,他不知道这缕淡淡的味道究竟是女孩子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还是方绢的熏香,一时间只觉得暖香沁脾,竟不觉有些脸红。
莫霭收了方绢,又抬起头看着他,那双红褐色的眸子跳动着琥珀一样的光彩,映出年轻人神色戚戚的一张脸。
两人又是一阵沉默。
良久,莫霭率先开口,打破了僵局:“叶大侠你今天练刀确实心不在焉的呢。”
“有么?”叶归澜心中一怔,不想莫霭也觉察出了他的异常。
“我一外行,不懂什么使招留不留情、什么刀路在不在主线上,但我就看你与石头过招时的神色,就觉得你有心事。”莫霭偏着头,一本正经地道,“叶大侠你今天来……不单单是想找石头过几招罢?”
“小霭你也发现了啊……”叶归澜缓缓地低语,心中思量自己是不是在这个女孩子的面前根本没有遮掩的余地,“我今天来找小霭,确实有事想跟小霭说……”
莫霭愣了愣,定定地注视着年轻人,似乎很想看穿他眼中淡薄的哀愁:“什么事?”
叶归澜沉思良久:“我……要成亲了。”
时间霎时凝固。
沉默。
叶归澜看见那双红褐色的眸子渐渐地冷了。他第一次看到莫霭用这种眼神看他,这个昔日里总是悠闲散漫、满口都是“叶大侠”的跳脱女孩,如今却用一种陌生得让他不寒而栗的眼神直视着他。
良久,莫霭缓缓开口:“和谁?”
“和……白姑娘。”叶归澜的声音低缓而迟疑。
“白姑娘……”莫霭想了又想,“可是阿聆?”
“是。”
“为什么是她?”
叶归澜沉思半晌,缓缓地回答:“这是父亲生前的意愿,我……不忍违背。”
“你喜欢她么?”
“我……”叶归澜噎住了,那一刻,他从女孩子的眼瞳中读出了不解。看着那双忧伤的红褐色眸子,叶归澜几乎可以确信莫霭对自己是有着那份悸动的情愫的,但事态已经发展至此,那隐匿的情思到底只能为所谓的责任与诺言献祭。
“你真的喜欢她么?”莫霭提高了音调,又问了一遍。她仰着脸,倔强地望着年轻人。她大概是没有想到,这个原本生性闭塞、对人情世故分外淡漠的年轻人在自己的陪伴下走过了近半载的时光,已渐渐习惯了与她一同将足迹洒遍郊野的山岗、一道并肩走过建康喧闹的街头巷尾、一起躺在织语斋屋顶看灿烂的星空,可到最后,他竟然选择迎娶另一个人!
“不是,小霭,你听我说。”叶归澜的心已经乱了,他本就不善于表达,现在面对失落又难过的女孩子,更是不知如何是好,“我……已经无从选择了。”
“无从选择?”莫霭硬生生地重复道,眼神却是愈发的冷漠失望,“这个‘无从选择’,究竟要从何说起呢?”
是啊,这个“无从选择”,究竟要从何说起呢?
叶归澜纵然有满腔的苦水,却无处倾倒,毕竟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在这个关头却成为了这腔苦水的源头。何去何从,何始何终,叶归澜自己都不曾知晓:“叶、白两家联姻是双方早已有了的打算,可……”
“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莫霭看着她,不依不挠地问。
“小霭你听我说,这桩事本是有的,可是家父遇刺了,就一直搁置,双方都一度以为这件事无疾而终了,但……”
“但现在你开始害怕错过这桩天赐良缘么?”莫霭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古怪又酸涩的笑容。
“不,不是的。”叶归澜慌忙摇头,“白大将军以为此事已经落空,就作出了将白姑娘献予国主的决定。无论是映尘还是其他友人,都不愿看到白姑娘陷入深宫的囹圄……”
莫霭再次愣住了。听着年轻人的解释,她眼瞳中的震颤在一丝丝扩大,她就这么睁大眼睛看着他,琥珀般的眸子里尽是不可名状的心酸与凄凉:“所以……你要以父辈的名义……救她?”
“不能算救罢……”叶归澜微低着头与她对视,说出方才那番话已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言语,他好似已经词穷了,“就算是做个……顺水人情。”
“顺水人情,好一个顺水人情。”莫霭失声苦笑。她的眼圈有些红了,但她就一直逼视着年轻人神色略略仓皇的眼睛,却不曾掉下一滴眼泪。
“小霭,对不起。”叶归澜很想避开莫霭的视线,但那双写满失望与一丝愤怒的眼睛始终牵绊着他,千言万语终究只能汇成一句“对不起”。
“你何必……跟我道歉?”
何必道歉?
叶归澜又是沉默。
“你并没有负我啊。”莫霭轻轻摇头,继续说道。她本想跟往昔对着罗衾罗裳或者江岩发牢骚时一样一股脑倒出一大堆话语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可她还是忍住了,因为她忽然想起,以自己现在的处境,似乎并没有为难年轻人的任何资格。
又是僵局。
“你走。”莫霭转过身去,不再看他,“大喜之日应该不远了罢,白家的人……可不希望看到你一脸苦相。”
“小霭……”
“你走你走!”
叶归澜无言以对。
“你走啊!”莫霭再一次用尽所有的力量吼道。
叶归澜看到女孩子的背脊开始颤抖,他不知道莫霭是不是哭了,如果还是从前,他会走上去,轻轻地拍着莫霭的肩背以示安慰。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面对莫霭的无助只有用掌心微末的温暖来表达关怀,但现在,自己连这样的动作都做不了。
他已经是一个和别的女人有婚约的人。
小霭,对不起。
叶归澜的内心千千万万遍地重复着这句话,终是没有再度说出口。
正如莫霭所说,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负了她什么。没有互诉衷肠,没有海誓山盟,他跟这个女孩子不过是在这个动荡的尘世彼此陪伴着,即便彼此有着些许的倾心又如何,在乱世中,爱情本来就是一种奢侈,脆弱而易碎,身在这个荒乱的世间,根本就不能奢望所谓的永远。
岁月已经撒下天罗地网,无法逃脱的,有我的遗憾,与你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