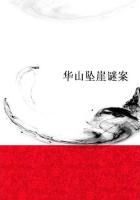星期六的早晨,庞月娟破例起得很早。何文庸原想在沙发上多睡一会儿,但庞月娟在他身边走来走去,还不时地哼唱着什么歌,搞得他躺着很不自在。后来他实在躺不住了,只好揉揉眼坐起来,无可奈何地说:“今天可是星期六啊,你这样早起来干什么?”
庞月娟冲他笑着说:“今天咱去西丽湖吧?”
何文庸一时没反应过来:“两丽湖?”
庞月娟说:“是啊,到‘相思湾’度假村去玩一天,怎么样?”
何文庸想了一下才想起来,于是说:“那个余老板的孩子已经毕业了,他们生意人都很实际,现在再去,他还能像过去那样招待咱吗?”
庞月娟笑着说:“就因为他们实际,我才敢去,别忘了,我可是局里的办公室副主任,专门安排各种会议的,他要是把我打点好了,以后能有亏吃吗?”
何文庸笑了,摇摇头说:“看来真是哪一行都有哪一行的腐败啊。”
庞月娟说:“这跟腐败可是两回事,我并没多给那个余老板什么,局里安排会,反正到哪里都是住,如果去了西丽湖可能还会更便宜些,这小是很正常吗?”
何文庸一边起身穿着衣服说:“对,典型的腐败分子狡辩!”
庞月娟热了两袋牛奶,又烤了两份“三明冶”,跟何文庸一起吃了就从家里出来。小区里晨光很明媚,深秋的阳光将植物叶子映得金黄。何文庸和庞月娟来到小区停车场,只见那辆乳白色的“本田”牌轿车上落满一层灰尘。
何文庸随庞月娟坐到车上来问:“你最近,怎么不常开这辆车?”
庞月娟说:“局里人的素质,也并不比下面学校高多少,都是‘气人有、笑人无’,你整天上下班弄辆车开着,还不招人忌恨呀,那就要离倒霉不远了。”
庞月娟说着,忽然冲何文庸一笑:“你来开车吧。”
何文庸摸了摸衣兜,驾驶证倒是带在身上,于是笑笑说:“好吧,我开。”
庞月娟坐到旁边的座位上,把头朝靠背一仰说:“今天,我也享受享受吧!”
汽车很快驶出市区。何文庸一边开着车,感觉心情很好。所有的事总算都已过去了,除去乔丽,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又都渐渐恢复了正常。乔丽始终没有来过电话。何文庸也从没跟她联系过。何文庸觉得这件事已没什么好说的了,待后面找个时间,将手续办了也就是了。只是今后的住处是个问题,他意识到,这样不明不白地住在庞月娟这里总不是办法,而且时间长了,也容易又被人抓住口实、这次出来,他也想跟庞月娟谈谈这件事。
原来庞月娟事先已给余老板打过电话。余老板照例又迎到“相思湾”门口,然后满脸堆笑地一路陪着走进来。这一次余老板非常知趣,推说自己有事,只让一位做领班的小姐陪着,而且并不总跟在身边,随时有什么要求只要跟她说一声,由她给安排就行了,并先声明一切免单。庞月娟笑着说:“余老板这样客气,今天晚上我们就更得回去了!”
余老板说:“何校长上一次帮了我那样大的忙,我小孩现在已经考上了区重点高中,眼看今后上大学肯定不成问题了,我正愁没机会报答一下呢!”
何文庸笑着摆手道:“那是孩子自己努力,学校和老师都不过是外因。”
中午饭是在湖心的“听浪台”吃的。晚秋的风只是有些凉,还不太冷,中午的阳光很充足,就越发显得暖暖的。四周很静,除去风声和水声,没有一点动静庞月娟特意要了一小坛绍兴产的“花雕”酒,点的也都是江浙风格的卤制小菜。
何文庸忽然对庞月娟说;“我想,从你那里搬出去住了。”
庞月娟眼里闪了闪,笑着问:“怎么,我哪里得罪你了么?”
何文庸连忙说:“不不,不是这个意思。”
庞月娟说:“那好端端的,怎么忽然想起搬出去?”
何文庸说:“我……在你那里住长了,总不是办法,再说,再说……”
庞月娟点点头说:“明白了。”
何文庸说:“这段时间,我……真得感谢你。”
庞月娟笑了,说:“你要说感谢的话,我可就要收房费了。”
何文庸端起酒杯说:“不说了,干杯吧。”
庞月娟问:“可是以后,你住哪儿呢?”
何文庸说:“我父母那里是不能回去,这种事,暂时还不想让老人知道,再说,我估计乔丽离婚以后也不一定想要孩子,所以那边,就不想惊动,我已经找到一处出租的闲房,是个一室一厅,租金也还合适,每月只要五百元,先凑合吧,等办了手续再做长远打算。”
从西丽湖回来仍是何文庸开车。庞月娟喝了一些酒,说是有些头晕。路上两人都没怎么说话,只是开着车上的音响,默默地听音乐。何文庸几次想挑起话头,跟庞月娟聊几句,后来见庞月娟没兴致说话,也就作罢了。
晚上回到庞月娟家,何文庸有些累,随便冲了个澡坐到沙发上就不想动了,一边看着电视,觉得有些犯困。庞月娟去卫生间里洗澡。何文庸听着哗哗的水声渐渐远去,只觉倦意阵阵袭上来。忽然,他闻到一股幽香的水气,接着就感到自己的脸和脖颈被人轻轻抚摸着。
他睁开眼,就见庞月娟正穿着浴衣坐在自己身边。
庞月娟轻声问:“累了吧?”
何文庸顿觉一振,浑身倦意立刻全无。
庞月娟又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今晚……不想感受一下我的床吗?”
何文庸的手自然而然地伸进庞月娟的睡衣。他站起来,随着庞月娟朝卧室走去。
庞月娟的卧室里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四面墙贴着水红色的壁纸,光线很暗。何文庸感到床很软,和庞月娟躺到上面就像是一条船上下颠簸着,有些控制不住两人的身体。庞月娟的呻吟声很轻微,但听起来非常舒情,他将手放到她的乳房上,轻轻抚摸着。
自从那一次他和她躺在一起之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又想起庞月娟的乳房。这时,他在心里想,他终于将它牢牢地把握在手里了。
外面突然有人敲门。先是很急促,接着就变成哐哐的踢砸声。
何文庸在庞月娟的身上,一下僵住了。
庞月娟侧过头问;“谁呀--?”
她的声音还没落地,房门已经被打开了。一个彪形大汉闯进来,冲进卧室来到床前。他边晃动着手里的一串钥匙,狞笑着说:“你以为我没钥匙是吗?实话告诉你,我早就料到你会有这一手,所以上次我哥回来时,我就找他把钥匙要过来了!”
庞月娟倒显得很镇定,她拉过被子将自己和何文庸盖严,然后冲他说:“你先出去一下,让我们穿上衣服,好吗?”
大汉歪起嘴一笑说:“你们还懂羞耻吗?”
何文庸说:“请你先出去。”
大汉立刻走上前来,一拳打在何文庸的脸上。何文庸的鼻孔和嘴角顿时流出血来。他跟着又伸手抓住何文庸的胳膊,轻轻一提,就将他拎出被子,然后随手甩就又把他扔到客厅里。何文庸一边连滚带爬随手抓过庞月娟的睡衣裹到身上。这时大汉已经跟过来,没等何文庸站稳就又是一拳打过来。何文庸晃了晃,勉强站住了。接着大汉就又是一拳,又一拳。大汉打何文庸出手很重,但又很专业,显得技法非常娴熟而且讲究,他每一拳都重重地落在何文庸的脸上或身上,却又不让他摔倒,这就以便于继续击打他。何文庸只觉得头被打得昏昏沉沉,身体摇摇晃晃,眼前已经天旋地转金星飞溅。
庞月娟这时已经穿起衣服,站在卧室门口突然喊了一声:“你够了没有?”
大汉这才停住手,回头看看庞月娟说:“你还有理了是吗?你对得起我大哥吗?”
然后,他朝门外一挥手,立刻就又冲进几个手持木棒的年轻人。这些人看也不看庞月娟跟何文庸,只是横起棍子见东西就砸,屋里顿时响起一片稀里哗啦的破碎声。
大汉临走时对庞月娟说:“明天咱们教育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