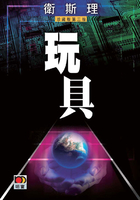其实按南海南夜总会的规矩,小姐们的小费是要签单的,最后客人算账时再统一交到银台上。但何文庸事先告诉罗心良,他要当着客人的面把小费递到小姐们手里。他就要这样的效果。他想向胡子主任强调,今天是花园中学花钱请他吃喝玩乐的。这时陶大林和徐静宜也已进来坐到桌旁。酒桌上有了朱艳和徐静宜两个女性,刚才的狎昵气氛就收敛了一些。
何文庸斟了一杯酒,端起来说:“我没酒量,再敬主任一杯。”
胡子主任端起杯喝了,哈哈一笑说:“你何校长够意思,办事敞亮,有场面,不像是个耍笔杆的文化人,好,那咱就说个痛快的吧!”
何文庸微微一笑:“你说。”
胡子主任说:“现在我手上确实有一笔‘下岗职工再就业技能培训费’,实话说,数目还不小,可我得把这笔钱花在刀刃上,这个刀刃你明白吗?”
何文庸看着胡子主任。
胡子主任又说:“晤……这么说吧,我手下还有这么多人,他们也得吃饭,包括我,我也是人,我也得吃饭,我们厂的这个服务中心就是我们的饭碗,这话你明白了吗?”
何文庸早已明白了。他刚要张嘴,陶大林却突然说:“对不起,我还是不太明白。”
胡子主任回头看看那几个都已醉得不省人事的手下说:“好吧,那咱就明人不说暗话,如果咱们合作成了,那几家企业我敢保证,肯定也都跟着走,可问题是怎么算?”
陶大林眨着眼问:“什么怎么算?”
胡子主任看看他:“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回扣,当然是回扣!”
何文庸低头考虑了一下,然后抬起头说:“百分之二十,可以吗?”
胡子主任哈哈笑起来:“百分之二十?我一万块钱给你再回来就变两千啦?”
何文庸问:“那你说,多少?”
胡子主任先伸出四根手指,然后又翘起拇指和无名指:“四六!我四,你六!”
何文庸一下张大了嘴。他没想到,这个胡子主任竟然这样黑。
胡子主任又说:“其实这事是明摆着的,四六你不干,总会有人干,你干了还有个六,要不干可是一分都没有,反正钱在我手上,我当然要选择最合适的合作伙伴。”
何文庸看看朱艳,朱艳也看看何文庸。
就在这时,胡振中突然举起酒杯对胡子主任说:“来,干了这杯!”
胡子主任哈哈大笑起来:“哎,这就对啦!古人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说着就举起酒杯跟胡振中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何文庸的心里腾地冒起一股火来。他想不要说自己,就连朱艳还都没有表态,他胡振中怎么就答应了?是谁给他的这个权力?但想了想,却又无话可说,刚才胡振中并没说任何与这件事相关的话,他只是跟胡子主任喝了一杯酒。至于胡子主任以为校方同意,那只是他的事。
何文庸又想想,也只有这一条路。于是,也就只好默认了。
朱艳连忙也端起一杯洒说:“我不会喝酒,不过还是一干杯吧,这件事就算说定了?”
胡子主任说:“说定了!”
朱艳问:“还用有个什么协议吗?”
胡子主任一笑说:“这种事,恐怕不好落到纸上吧?君子协议就是了。”
这时,陶大林忽然说:“没关系,咱们有见证人,以后谁都不会反悔的。”
胡子主任一愣:“见证人,谁是见证人?”
陶大林笑着一指身边的徐静宜:“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晚报记者徐静宜小姐。”
胡子主任放下酒杯,慢慢站起来。他看看何文庸,又看看朱艳,然后沉着脸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怎么回事?开玩笑呢是吧?”
何文庸也愣住了。他没想到陶大林会来这一手。
胡子主任冷笑一声:“看来你们花园中学没有诚意啊!”
陶大林笑着伸出手,做着朝下压的手势说:“请坐,您请坐,我们要是没诚意,能费这么大劲请你们吃饭吗?我刚才说这位徐静宜小姐是我们花园中学的老师,并没错,说她是晚报记者,也没错,她正要调到我们学校来,只不过还没办手续。”
徐静宜也冲胡子主任笑笑说:“就算我不是花园中学的人,这里毕竟也是我母校,我当然希望你们合作成功,请放心,只要你们双方不食言,我不会在报纸上披露半个宇的。”
胡子主任这才举起杯,跟何文庸和朱艳几个人碰了一下。
从南海南夜总会里出来时,何文庸窝了一肚子火。
他看看前后没人了,就沉着脸问胡振中:“刚才是谁让你表态的?”
朱艳办成了事,心里正高兴,就说:“算了算了,胡老师当时并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想跟胡子主任碰一杯,话赶话正好赶到那里了。”
胡振中低着头,默默地朝前走着。
何文庸忽然发现,他走路已经有些打晃,到了嘴边的话才又咽回去。
陶大林送徐静宜上了出租车,从后面赶上来说:“今天这事,办得真漂亮!”
何文庸回头瞪他一眼说:“还有你!弄个记者来也不事先说一声,还搞什么见证人,多此一举,已经谈成的事差一点又崩了!”
陶大林一吐舌头。
朱艳说:“陶老师也是好意,我看刚才这事办得挺好,这一来对那个胡子主任也有点威慑,万一他以后变了主意,咱让记者写篇文章就够他受的!”
何文庸这才哼了一声,又问走在前面的胡振中:“你饿不饿?”
胡振中说:“……有点儿。”
朱艳说:“我也是,今晚根本就没吃饱。”
何文庸一拍陶大林说:“走吧,咱们吃馄饨去!”
吃完馄饨已是晚上十点多钟。胡振中先回学校去了。陶大林说要到同学开的一家洗浴中心去蒸一蒸,拦了辆出租车也走了。何文庸看看朱艳,说要送她回去。朱艳并没反对,两人就沿着路边慢慢朝前走去。初春的月光很清冷,薄薄地洒在地上。寒风里已经些许有了暖意。朱艳的心情显然很好,一边走着轻轻哼起歌来。何文庸此时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愉快,是做成一件事后的那种愉快,这感觉从大学毕业以来还从没体验过。
他看看身边的朱艳说:“没想到,这件事真让咱们给办成了!”
朱艳说:“是啊,只要钢厂这边一答应,纺织厂和耐火器材厂那几家企业肯定也没问题,这样不光债务问题解决了,学校的经济状况很快也能改善!”
何文庸由衷地说:“难怪98中李校长不愿放你。”
朱艳立刻笑着说:“哎,这里可没我什么功劳啊,事情是你策划的,酒是体和胡老师一起喝的,记者是陶老师找来的,我干什么了?”
何文庸看着她一笑,忽然说:“这回咱又要在全区爆出新闻了,我越想这个培训中心越有前途,既解决了咱们学校的经济困难,又开发出闲置资源,还帮企业做了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技能培训,一举多得,要我看,这种再就业技能培训应该是个朝阳产业!”
朱艳说:“这回局里的那个庞副主任又该表扬你啦!”
何文庸听出朱艳的话音里有些酸,没接她的话茬儿。
朱艳又说:“我看那个庞副主任,对你挺好啊?”
何文庸故意轻松地一笑说:“是啊,局里领导都对我不错。”
朱艳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我是说……”她忽然不说下去。
何文庸有些后悔送朱艳回家了,至少在刚才应该拦辆出租车。
朱艳又说:“问你个问题,可以吗?”
何文庸突然有了种不安的感觉。他想说,最好不要问,但话到嘴边却嗯了一声。
朱艳说:“这个问题,已经在我心里搁好多年了。”
何文庸已经猜到朱艳要问什么了。
果然,朱艳说:“当年在那个舞会上,你为什么拒绝我?”
何文庸在心里想了一下,觉得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有些事可以挑开说了。
于是,他说:“我当时……不敢碰你的手。”
朱艳就伸过手来,拉住了何文庸的手,她问:“现在,敢了吗?”
何文庸的心里突然感到有些吃惊。他发现自己和朱艳这样拉着手,竟没有丝毫感觉。朱艳的手很粗硬,握在手里觉得满是筋骨,这使他想起她在西藏这些年的经历。这真是个强硬的女人啊,当年带着自己的青春跟爱人一起去闯西藏,现在孤身一人回来,竟还能有如此的工作热情,真不容易!他这样想着,手就像松开的绳索,渐渐没了力度。
朱艳立刻敏感地察觉到了,自己将手轻轻抽回来。
她说:“是啊,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伴……也挺好。”
何文庸说:“嗯,以后就这样……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