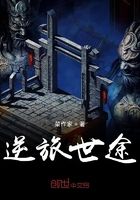姜雪子念着阿弥陀佛,庆幸肖依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没闯进局里去。要不的话,局里的人们一准会笑掉大牙,也会一改对肖依的看法的。甚至,姜雪子都能想象得出,要是肖铁活着的话,一个巴掌烙上去,让肖依哭着喊着去满地找牙。
“嫂子,就你们成天穿着老虎皮,狐假虎威才正点,是吧?”肖依很不屑地“切”了一声,“抓紧乐,活着就是要抓紧行乐。我算想明白了。”
姜雪子恨得牙痒痒的,却也对她的话无从下口。虽说肖依是一副蛮横劲,但在言谈举止间也有一种对姜雪子的依恋和尊重,一口一个嫂子地喊。无事不登三宝殿,肖依肯定是有谋而来,也不清楚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嘴上抹了蜜,有什么好事呀?”
肖依伸手,择掉了姜雪子肩头上的一根断发,喜滋滋地说:“嫂子,马上该过年了,我想送你一件礼物,就怕你不接受。”
“咦?我该不会成了中举的范进吧?”
“想想你也真不容易,嫂子。其实,这件礼物本来就是你的,我先借用了一段。现在该是完璧归赵的时候了。”肖依说得很真诚。但姜雪子如堕十里迷雾当中,一时也想不明白肖依犯了什么痴?她瞪大了眼睛,揪揪肖依的耳垂,像在看她发没发高烧。肖依抿着嘴角,坦然地说:
“嫂子,你在外面租房子,这么久了,负担也挺重的。我想了想,我要把那套老房子还给你。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和我哥肖铁的仪式办没办,但你们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了。房子是我哥的,也就是你的,我要还给你。”
姜雪子愕然,“瞎说什么呀?哪根筋不对了你?”
“我可没心血来潮哦,嫂子,”肖依拨拉掉姜雪子的手,对她的不领情带了些气咻咻的反感,“我想了很久,才下定这个决心。你要再不接受,我可立马反悔了!一星期后,我就搬出去,你退了那套租借房,我把钥匙给你。屋里的家具、电器和厨房的东西都留给你,我一样也不带走。”
“那你住哪儿?去喝西北风呀?”
肖依露出了狡黯的笑,预谋良久地贴近了姜雪子的脖颈,贴耳说:“不过哪,你得帮我一个忙,天大的忙。要是成了,房子就是你的了。我绝不食言。”
“什么忙?得用一套房子做佣金?”
“我要结婚了!”
“谁?”
“臧毅!”
霎时,姜雪子觉得有一个成语是为自己度身定做的:五雷轰顶。手里的袋子滑脱了手,掷在脚下,她像扶住了空气里一根无形的柱子样,按住了太阳穴。天杀的!肖依一准是昏头了,嫁给谁不好,偏偏嫁给“臧毅”这个名字。真是不疼的手指头往磨眼里钻,找不痛快受?肖依瞧出姜雪子有点灵魂出窍似的,忙问:
“嫂子,嫂子你怎么了?”
姜雪子懈怠地摆了摆手,表示没多大的麻烦。她定了定神,稳住了自己。
要是没猜错的话,肖依一定是上次在咖啡屋里,与自己一块时认识下的臧毅。如此说来,自己乃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介绍人了,一辈子将洗不净身上的污浊,也没法对九泉之下的肖铁有个交代了。
姜雪子仍清晰地记得,当初肖依甩给臧毅的那记响亮的耳光一她看见臧毅在洗手间门口鬼鬼祟祟,时不时地伸进头来,打探里头的动静。起初,她以为他是盯梢自己来着,最起码也是一个淫贼,心理变态的偷窥狂。就算咖啡屋里只有一个男女共用的洗手间,他也不能那样贼头贼脑吧?
她和臧毅争执的过程中,肖依打马而来,不问青红皂白地扇了一记猛烈的耳光,将臧毅弄得眼花缭乱,不明所以。却原来,正是吃的那一记脆生生的耳光,将他俩焊在了一起?进而到了谈婚论嫁的鬼地步。这阴差阳错的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呀?姜雪子百思不得其解。
按着肖依的性格,她不是那种雷厉风行、一杆子插到底的主儿。就算因错而生了情愫,他俩迅速黏糊在了一起,但也不大可能进展到如此地步的。
姜雪子犹记得初冬的那一夜,肖依请自己去火锅城里涮毛肚鳝鱼,她隔着包厢的落地玻璃,目睹了肖依与臧毅的亲昵举动。姜雪子原以为不过是逢场作戏,有一搭没一搭的露水情缘,现在想来,自己却是大错特错了。像蒙在鼓里的人,地球人都知道了,自己却还装嫩傻笑,浑然不觉呐。
“你说的是臧毅?”姜雪子艰难地问。
“哦!吃我耳光的那个家伙。”
姜雪子盯着她眼中一团真诚的物质,看稀罕似的,明白她早巳陷进了臧毅的泥淖中了。但她仍肝疼似的说:“你了解他吗?你了解他的全部背景吗?做这样的傻事?”
“怎么了?”
“没什么!可我忍不住要对你讲明白,我不能不负这个责任。”姜雪子拽着肖依,偎在了商店侧廊后的卷闸门下,避开湍急的人流,寻了个相对安静的场所。“臧毅有一个哥哥,叫臧刚,是个杀人犯,持枪抢劫银行的凶手。正是我给他画的通缉令上的肖像,才迅速捕获了臧刚。臧刚巳经被执行了死刑,我当时就在现场哪。”
“我早知道啦,臧毅早给我交代了。”肖依蛮不在乎道。
姜雪子一瞧她的大咧咧劲儿,恨不能也扇她一个耳光,将她扇醒过来。姜雪子急了,也不明白该如何说服,先是咬了咬捏紧的拳头,忽地将胳膊搭在了肖依肩上,“你是我妹妹,虽说你哥肖铁那样了,不在这个世上了,可你永远都是我妹妹,我不能对你袖手不管。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况且,这是一辈子的终身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的。相信我,我说的话,你哥的在天之灵也会点头同意的,我要为你负责。”
“我就是冲这个来的!”
“怎么?”
肖依不再轻佻了,态度诚恳地说,“反正,你是我嫂子,我哥哥他自私地死掉了,这个世界就我俩相依为命了。你就是我的家长。我和臧毅要订婚了,我想,让你代表我这一方,和臧毅的父母亲见面,把日子定下来。”
“我?”
“你是我嫂子嘛!”
真像吞了一只铁蒺藜似的,骨鲠在嗓眼里,咽也不是,吞亦艰难。姜雪子的胳膊像一座断桥,搭在肖依肩膀上,冰冷麻木,连对方的一丝体温也感触不到。事先一点预兆也没有,肖依就将一枚炸弹般的信息塞过来,让自己连个防备的机会也准备不了。但姜雪子横下了心,好歹,也要将利害关系讲明白,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走上一条不归路。姜雪子稳了稳情绪,挤出来一团和气,循循善诱地说:
“肖依,听说过蛇鼠一窝吗?他哥臧刚,放着好端端的银行副行长的位子不坐,为争一把手的位子,雇凶杀人,持枪抢劫了银行的营业所。执行死刑的那天,就是臧毅亲自去火葬场收的尸,我也在现场,我能感觉出他身上的不对劲来。”
“你不能一概而论!他哥那样坏,可他是个男人,有骨头!”
姜雪子捏紧了拳头,杵在肖依的锁骨处:“你才认识他多久?不就是上次在咖啡屋里冲突时,你才见第一面的吗?怎么能说有感情基础呢?这可不是玩过家家,是找一个能一辈子共度的人。得好好想想,不能被甜言蜜语给糊弄住,要自己拿主意才是。相信嫂子,凭着一个女人的直觉,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哦!”
“他爸爸妈妈对我可好了。再说,他真不是他哥那样的人,他有主见,有骨头,有男子汉的那种魄力和勇气……”肖依像背课文样,专拣一些动听的赞美词,堆砌在臧毅的身上。姜雪子听着她孩子气的话,脸都烧烫了起来。
“嫂子,我也老大不小了。我哥死了,你也有一堆的麻烦事。我不想让你替我操心。我巳经度过了前一段乱七八糟的日子,调整了过来,我想趁着他人还不错,嫁掉算了。我不想再玩了,特累!”
“你有多老?大言不惭的!怎么能这样自轻自贱地,把自己打发掉呢?”
肖依读出了姜雪子的违拗和反对,单刀直人地说:“说白了,是你不了解他,你也不知道他有多优秀。你嫌弃的是他有一个杀人犯的哥哥。你是个警察,怕给你丢人现眼,给你抹黑,对不对?”
“是!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姜雪子倔强道。
“切!”肖依抬脚,踢了一下地上的袋子,凶巴巴地说,“别居高临下看人了。照你的逻辑,我哥贪了命案现场的一笔钱,自感对不住身上的老虎皮,把你和我都羞辱了一番,然后跳河自杀了。我们就该一辈子背着这个骂名吗?难道一辈子都要抬不起头来做人,为他的愚蠢和自私付出代价吗?嫂子,你一直没走出我哥留下的阴影’就是你的这种心理在作祟。你把自己也圈进了这个混账逻辑里了。”
“你!你怎么能这样指责你哥?”姜雪子讶异道,目瞪口呆着。
见肖依掉头就走的样子,姜雪子连忙扳住了她,血管贲张地又追问了几句。肖依显然吃了一脸的灰,在姜雪子身上找不见温度和呼应,气急败坏了一般:“本来就是这么回事!简单得跟‘一’一样。不能因为你是肖铁的未婚妻,你就护短,你就袒护一个死掉的人。那样做,对你一个活着的人,究竟有什么好处?”
“他是你亲生哥哥,也是我的丈夫。”姜雪子头一次这样称呼肖铁。
“他巳经死了,可我们都活着。”肖依仿佛一块冷却下来的铁,嘴里蹦跳出来的字,颗颗都像子弹。“臧毅说过了,生活没变,生活还在继续。我们活着的人,不能那般期期艾艾胆战心惊,总替死掉的人检讨吧?”
“臧毅说过的?他的话就那么值钱?”
姜雪子无话可说了,抬脚跨过了地上的袋子,径直站在了午后的街上。她觉得自己像一条窒息后的鲸鱼,终于喘出了一口闷气,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她贪婪地呼吸着,仰面望天,一箱箱的云朵,越发像灰鼠的皮毛,压过来,横陈在天上。无疑,一场大雪巳成燎原之势。她的内心也凝结住了,冰块一样挂着。
临转身的一刹,姜雪子听见肖依的牙缝里滚出了一个恶毒的词。肖依说:
“老处女!”
先是鹅毛大雪做了开场白,接着掉下来的是雪渣子,含了更多的水分子,颜色也冻得剔透晶莹。雪渣子打在颊面上生疼,落在地上迅速凝结住。
一年里最冷的月份到了。
一下雪,队上的同事们就有理由不回家了。出了局里的食堂后,三三两两地凑在一块,不是打双扣,就是玩锄大地。对牌戏,姜雪子一向不很精通。就算缺人搭桥,姜雪子勉强登场,也很少有人愿意与她打对家。久而久之,便无人再吆喝她玩几把了。这样也好,省得把时间花在那种无聊的打发上。她这样想。
洗了饭盒,姜雪子趴在桌子上,打开了电脑。
她不会跟人聊天,自然也没有号。因了职业的缘故,姜雪子的软件里存有上百幅不同男女的面部特征图,她喜欢将他们迥异的面部轮廓化整为零,然后整合一新,制造出更新的模样来。作为技侦部门的摹拟画像专家,这是她的一种极私密的快乐,不足为外人道也。这天中午,姜雪子调出来的是央视的主持人李咏的头像。
偶尔看看电视,姜雪子总喜欢将频道固定在李咏的节目上。一来他的节目益智,天南海北的什么内容都有,凌乱得像一锅大杂烩,包楸也抖得好,往往能出奇制胜;二来,这一档节目就是一个“闹”字,杂花生树,风生水起,斑驳得令人眼花缭乱。姜雪子在家时,一般都会卧在沙发上,抱着一只枕头,跟啦啦队们鼓噪着大喊。
后来就起了变化。姜雪子随手一点,视屏上出现了肖铁的一幅指纹,绷紧了整个画面,网兜状一般,历历在目。将近一年了吧,连姜雪子几乎都忘了,文档里竟然还存储着这么一个文件。她倒吸了一口凉气,怔怔地逼视着那一枚指纹。
刑警支队按照自己的技术力量,给每一位同志都做了尽可能多的个人档案,以备不测。大到"^人、血型、对某些药物的过敏分析、身高、家庭状况、疾病史和身体特征,小到指纹、牙齿、虹膜和毛发的备案等等,一应俱全。按照老胡的说法:弟兄们都是提着脑袋和几家人的性命作战的,万一有个不测,也好找到几个零件,给家属一个交代。
话虽狠了些,叫人揪心难堪,但不无道理。
肖铁出事后,技侦上的大姐奉老胡的指令,将他的资料都删除了。老胡担心她们在同一个办公室,稍不留意,会让姜雪子睹物伤情的。但老大姐心眼极好,抱着雁过留声、云过留影的想法,偷偷地将肖铁的某些资料存在了姜雪子的电脑里,让她做个纪念。其中,就包括了肖铁的指纹。
这是一张拇指的指纹图。
飞旋的纹路,密密匝匝地聚集一点,自幽深的核心散开,张开了无形阔大的羽翼,类似于姜雪子曾在杂志上看到过的星际云图的状况。丝状的纹路,按着各自的轨迹抖擞而散,像在画布上用指尖抹开的一滴油彩,嵌下了一个人身上的密码。姜雪子一厘米一厘米地端详着,蓦地想起了肖铁的十指来。她记得,有好多个夜里,自己躺在肖铁的枕侧,掰住他的指头看个不休。
肖铁的指纹有九个“簸箕”,只有一个“斗”。
那是一种算命术。据说,“簸箕”代表了懒散、得过且过和无所谓,是一个散财童子的象征;而“斗”则是聚财、热爱、打拼和力争上游的形象。
忽然,姜雪子突发奇想了。她将肖铁的指纹图存进了!盘,慌里慌张地关了电脑,拎起包奔到了楼下。一个念头锥刺般地钉进了脑海里,让她觉得在这个下雪的午后,一定要干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她顺利地进了路边的一家喷绘图片社,要求人家将肖铁的指纹放大、修饰一遍,然后按着指定的尺寸打印出来。在姜雪子的心里,恰恰是视屏上的这枚指纹,是肖铁身上唯一的“斗”。将近一年了,他早就化成了一捧冷灰和余烬,但他生前的密码和气息留存了下来。冥冥的天意似乎眷顾了她,让她备感温存,涕泗涟涟。
她不能丢失掉,更不能漠然视之。
她想将它放大,定格,绷进租借屋里墙上挂的那只画框中,朝夕之间都能看到,都能有一个热烈的记号罩在头顶,如一枚神符那样,隐隐中发射出吉祥的热力,保佑活着的人和事。虽然,姜雪子明白那一只镜框中原本嵌的是她和肖铁的结婚照:她穿着一袭婚纱,偎在了肖铁的怀里。但姜雪子也知道,经过摄影棚涂脂抹粉的装饰,巳篡改掉的照片离自己和肖铁很远了。
现在,唯有肖铁拇指上的这一枚“斗”,才是需要去解读、去珍惜和偎依的。
一念及此,姜雪子忽觉浑身燥热,身体轻盈了许多。
她给操作员比画着,讲解一通。她试了十来个效果图,抱着肘细细品味不巳,左端右详,大多都被否决了。又看了不少的图册,参考了国内外的一摞光盘,眼都花了,始终也没找到满意的效果。
后来,老胡的一个电话催逼过来,要她立刻归队!
姜雪子的鼻子快被气歪了。她给伶俐的操作员说了一通自己的要求,要他自主做出一幅理想的指纹喷绘来。等下班时,她再过来付账取样。
拐过楼梯,一进老胡的门,姜雪子差点和文军撞个满怀。
“你怎么像个催命鬼似的?知不知道,现在是休息时间?”姜雪子边调侃着,边将文军往技侦办公室里带。文军却满不在乎的样子,嘻嘻然地解释说他下午还得出庭,为一个案子辩护,只得破费别人的午休了。
“你态度不好啊丨雪子。”
“别套近乎了,这是办公室。”姜雪子倒了杯茶,递给文军。文军却不生分,掏出烟来,给墙角一堆玩牌的警察们打了通关,而后气定神闲地坐在姜雪子对面。
“怎么?囡囡是不是对你说了什么?有新的情况和线索了?”姜雪子问。
“除了囡囡的面子,你对我公事公办?”
“当然!”
“哦,我活人活到这个地步,真是惭愧极了。”文军自嘲道,衔了根烟,余光斜睨着姜雪子说,“我还抵不上一个小屁孩的水不,真让你嘲笑了。”
“说你的正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