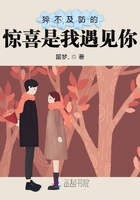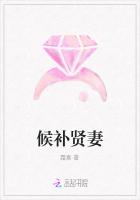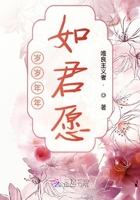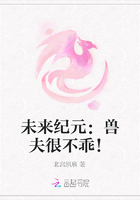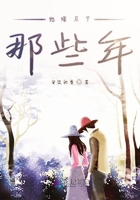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它经历了漫长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过程,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的重大发展;它为我国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对我国迎接各种挑战,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93法治中国
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从而翻开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新的一页,也明确了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
1978年,十年动乱后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亟待重振,然而重振的基础却非常贫瘠。那年,中国的人均总国民收入仅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而国家有效的法律规则似乎比薄弱的经济更为薄弱。在1978年以前所颁布的134件法律中,81%已经失效,仍然有效的另外23件就成了中国法治转型初始的“顶梁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自发的承包到户改革急于冲破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政策、法律的不置可否,使得改革充满不确定性。在欣喜于现实利益的同时,包括改革者在内的民众还是担心仅是用执政党文件形式确定的原则、政策会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与此同时,社会问题也特别尖锐。“十年动乱”制造和遗留下来的大量社会矛盾,在“文革”结束时迅速爆发,其极端表现为各种刑事犯罪的急速增长。
其次,1978年开始的改革探索,使得长期处于被批判和压抑的商品经济爆发了大量能量,对计划经济和传统观念造成巨大冲击。改革初期经济犯罪急剧增长,成为又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决策者也逐渐意识到,减少改革者所面临的各类风险。要解放思想、增加改革的积极性,就必须维护国家政策、方针和路线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加强法制就是为推进改革保驾护航。
邓小平反复地指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终于传来了温暖的声音:“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由此,法治转型随即展开,立法机关明确表示自己的使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这样的提法在当时让全世界的观察家都感到新鲜和好奇。
著名法学家江平曾做过这样的描述,中国的法治进程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有时是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原地踏步,甚至有时是进一步退两步。改革以来,市场经济建设和法治进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承认法律也有善法和恶法一样,我们也要承认法治建设的进程有进有退。1979年夏天,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应运而生。但是由于立法经验不足,这部刑法在短时间内即显露出与社会现实生活和犯罪实际情况的不相适应。从1981年起,立法机关便着手对其进行修改、补充,陆续出台了23个《决定》、《补充规定》等。其中类似于《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等直接涉及经济犯罪的规定,更表明了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保障的决心。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法制建设必须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法制建设必须保障建设和改革的秩序,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用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
第二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从国家最高法律层面对私营经济给予明确保障,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适时地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私营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家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将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真正启动,中国开始在司法领域逐渐健全相应的法律体系,在法治进程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法律开始担负起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法律体系的任务,人们寄希望于用新法律体系催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阶段,用“国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取代了“国营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提法,以“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取代了“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
宪法第二修正案结束了对深化改革的疑虑和争论,这条更具转变法律秩序意义的修正案,在几个重要修正条款删除“计划”字样,隐含了对市场经济中自治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分别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农村集体经济进行社会化、自治化方向的修改,从产权高度集中转向产权分离、下放,为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有节制退出经济生活、恢复经济自由提供了宪法道路。
从1993年3月到1998年2月,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了40多个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其中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取消了对非公有制企业设立公司的限制,直接为接下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开路。《民法通则》的出台填补了我国民事基本法的空白,为市场经济运转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原则与制度。《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规范企业进入相关领域的门槛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等进入市场后的交易法,以及《企业破产法(试行)》等在市场竞争中的退出法,构成了中国民商法基本构架的雏形。
之后,促进市场主体制度完善的《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乡镇企业法》等;维护市场秩序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保险法》、《证券法》、《合同法》等;规范宏观调控方面的《会计法》、《审计法》、《预算法》、《价格法》,以及税制改革涉及的一系列有关税收的法律法规、有关自然资源和产业、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等陆续出台,立法呈现迅猛发展之势。
法治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关于经济发展的立法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令世界瞩目,政府通过法律促进和保护市场经济发展的努力有目共睹。法治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此时,壮大和改革司法机构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人民法院在原有的刑事、民事、经济审判庭的基础上,逐渐增设了行政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控申庭、执行庭等机构;设立了铁路法院、海事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与普通法院系统相配套。在各级人民检察院中,增设了反贪污贿赂局等重要机构。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具体体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为主体,以合理分权、相互制约为内容的国家权力监督机制。并先后制定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进一步强化对司法人员的规范与监督。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叩开世贸组织的大门,为了实现司法衔接,中国废止了90件同世贸规则和我国政府对外承诺不一致的司法文件,制定了33件适应入世要求的司法解释。在加入WTO后的过渡期内,《外贸法》修改,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个人对外贸易的经营权,一个以自由贸易与和谐贸易为导向的外贸法律改革走到了前台。紧随中国入世的,还有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新的“两反一保”措施条例,进一步完善了贸易救济立法,一个能使中国本土企业与其外国对手平起平坐的法制环境初步实现。
2003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宣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每个法律部门中主要的法律已经基本制定出来,加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长久、曲折而光明的历史过程。
它的起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法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独13亿中国公民有着切身的体会,国际公约、多国宣言、WTO规则,以及万商齐集华夏,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公民想必亦有所感。
近230部法律的从无到有,涵盖宪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达600件,地方性法规更达7000件之多。从“无法无天”,到追求“民主与法治”,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正在朝法治中国、富强中国的理想迈步前进。
◆记忆中的重大事件
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中苏关系正常化。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
199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决定。浦东开发启动。北京亚运会开幕。上海证交所正式成立。
1991年,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海协会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十四大召开。国务院批复设立浦东新区。经济体制改革。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天下第一庄”支部书记禹作敏落马。三角债。整顿金融秩序。第一次汪辜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