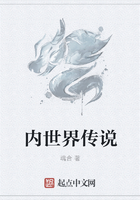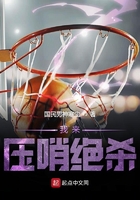2008年11月23日,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148位中国知名学者通过投票得出了一个结论:过去30年里,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
这不是一个容易得出的结论。对于在一个启蒙的年代,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年代,旧的力量没有退却,对未来的热切渴望则帮助着新的力量,各种主义、尝试都被提出,通往新秩序的道路扑朔迷离的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并非邓小平的特意安排,而是中国农民的自发行动。然后在邓小平、万里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农村改革成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关系中国发展和命运的大变革。
小岗之夜惊天动地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这年夏收分麦子,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全队18户,只有2户没有要过饭。队里严国昌等几个老人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商量: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得想想办法。办法就是不吃大锅饭!
副队长严宏昌再也不想出去要饭了,他联合了18户人家搞大包干。“我豁出去了,要是我被抓了,村上人会养活你们娘儿几个的。”他很悲壮地对自己的老婆说。
是年12月的一天夜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在村里一间屋里,他们神态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全文如下:时间: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们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到会的18人按了血红的手印。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小的契约,却预示着农村一场大变革的开始。对于这个冒着身家性命危险带头实行“大包干”的严宏昌来说:这是逼出来的,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这也正是邓小平反复告诫人们的话。
安徽凤阳小岗村20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份“红手印包干书”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份重要文件,被认为是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1979年,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1.5万多公斤猛增到6万多公斤。
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公粮的农村,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小岗的突破,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怎么看待这一突破性的实践呢?这令各省乃至中央官员伤了脑筋。1979年1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会议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是肯定人民公社,反对包产到户。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1979年1月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1979年春说:“要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
然而农民们却受不了饿肚子,行动起来了,1979年春,全国各地不少农民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划分,三家五户结为小组,共同拥有那一份共同的土地。到春耕时,全国已有200万个村的3亿社员采取了这种行动。这也叫包产到组。
“张浩事件”
张浩,甘肃档案局的干部,1979年,他回河南洛阳老家探亲,看到那里正在搞包产到组,分地分牲口。他以激烈的措词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了二十几年,群众已经习惯。现在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倒退,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
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的是王任重。他从《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送审样上看到华国锋的批示,批示批评农村中抢牲畜闹分队的现象。王任重立即于3月14日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信,指出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决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
于是,这年的3月15日,张浩的信和编者按一同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编者按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张浩的信,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
所有有头脑的人当然都认为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最新体现,而决不是一封普通来信。于是,有的县把分田到组的人都合并起来。有的县大批农民当即停止春耕,说:“报上又批评啦,算啦,不干啦!”
凤阳县更是人声鼎沸。县委书记陈庭元顶住了,仍然坚持大包干。万里叫秘书打电话给凤阳,对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说:“《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
3月12日至24日,由王任重兼任主任的国家农委请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三县负责人在京开会,会后形成纪要,经中央同意批转全国,要求“不许包产到户”。
同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指责万里不肯学大寨。
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同时,他指示安徽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安徽省两位农民的来信,题目是《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
来信尖锐批评张浩的信和编者按给农村造成了混乱,批评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和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指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
《人民日报》为此文加的编者按承认3月15日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还说: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
《人民日报》发表安徽反驳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极大地缓解了对包产到组的压力,给了各地从事农业改革的官员和农民回旋的余地。当然,《人民日报》这样做是冒了风险的。从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的整个宣传来看,这一出击,反映了当时《人民日报》一贯的支持改革的立场。
小平一语扭乾坤
但斗争仍然是很尖锐的。国务院农委主办的颇具权威性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二期和第三期分别发文批评分田单干。
1979年夏,安徽诞生一首讨伐大包干的诗:“集体干分掉了,人心干死掉了,干部干瘫掉了,耕牛干死掉了,农具干毁掉了,机械干锈掉了,公房干倒掉了,大田干小掉了,科学干停掉了,公活干歇掉了,教育干低掉了,贫富干大掉了。”
各种舆论纷起。
“万里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
“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形势相持不下。正当此时,邓小平于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发表谈话,一下子扭转了乾坤。
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中央于1980年9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后,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75号文件”)。
这份《通知》终于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通知》下发之后,到1980年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1980年初的1%上升到15%。联产承包最终成定局。1979年,凤阳卖给政府大约4450万公斤粮食。
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给他的上级写报告说,这个数字相当于过去26年凤阳卖给国家的粮食的总和。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凤阳48万公社社员生产的粮食还不能养活自己。
小岗村1979年卖给国家粮食12497公斤,超过政府计划的7倍;卖给国家油料12466公斤,超过国家规定任务的80倍。还有钱,小岗农副产品收入47000元,平均每人400多元。
一篇报告文学《丹凤朝阳》这样描写说:一只凤凰从天而降,落到凤阳县境内,亭亭玉立,金碧辉煌。凤凰忽见一瞎眼老妇,遂展其光彩,老人立即重见光明,这是凤阳老早的一个传说了。作者说:实行大包干之后,“神话变成了现实”。
到1981年秋,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上升到总数的40%。大约有5%的生产队还坚守在人民公社的阵营里,另外55%的生产队在犹豫。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该年一号文件。这个文件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它在“75号文件”的基础上又大大向前跨了一步。文件的突破点,是这样一段话:“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共产党执政30余年,还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文件中承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现在承认了,这就给农村干部和农民吃了“定心丸”。
1982年底,大体上有80%的农民实行了包干到户。人民公社体制基本上土崩瓦解。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当时农民丰收后兴高采烈所说的话语。
连续五个“一号文件”
1982年的“一号文件”,正式确认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使存留在农民心里的疑惑一扫而空,使包产和包干到户的家庭生产责任制迅猛发展。
1982年这一年,农业又一次大丰收。当年国家农委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同时成立国务院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