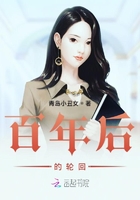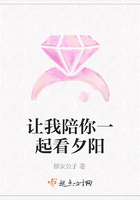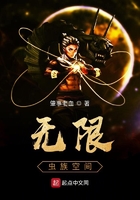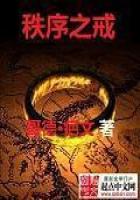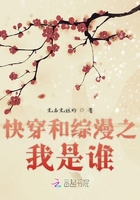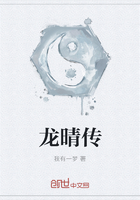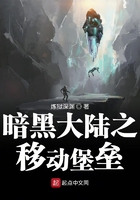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同“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和捣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最紧要的任务。他为此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对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经过1975年短短一年时间的整顿,我国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正气抬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长期培植的一小撮野心家、“打砸抢”分子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受到了打击,生产秩序大为好转,各项工作都有起色。这一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8.7%。邓小平所进行的一系列整顿工作,实际上是继承了周恩来的思想,这当然引起毛泽东及“四人帮”的不满。所以,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他们就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下台,经济整顿再次夭折。
生产力停滞不前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之间发生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的错误,乘机组成的阴谋篡夺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大规模的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使中国陷入全面混乱之中,国民经济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冲击和破坏。
其对经济的反复摧残,表现如下:
(1)批判所谓“刮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鼓吹“穷过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许多东西都被诬蔑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并进行错误的批判。比如,党和政府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水平,在农村中坚持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以及局部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等,都被诬蔑为“刮单干风”,是“复辟资本主义”,应统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
在农村中强制扩社并队,轻率地改变核算单位,使集体经济又一次遭到破坏。许多社队的储备粮、公积金等,又一次被分光吃净。另外,取消自留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减少了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供应,引发市场紧张局面。随着个体和集体商业、服务业、手工业的缩减,集市贸易的关闭以及个体商贩的取消,商业服务网点大大减少,基本上形成了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流通渠道日趋单一。这样,一方面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造成了市场的紧张和吃饭、穿衣、修理等方面的困难,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2)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林彪、江青一伙说成是“衰亡着的旧事物”,是“资本主义因素”,它造成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它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他们还把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全面否定,极力鼓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林彪、江青一伙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他们提出这种说法的政治目的,是为了把一些按照劳动分配得到收入较多的人,打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借此再度打倒一批老干部。
(3)对合理的经济管理规章制度进行批判和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和政府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技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比较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如《工业十七条》、《商业四十条》、《科技十四条》等)对推动各方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规章制度,却被视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批判。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不仅在理论上造成混乱,而且在经济上造成极大的破坏,它使经济指挥和管理机构陷于瘫痪,一些正确的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破坏、交通运输阻塞、煤炭生产下降,许多企业停工停产等。
在“文革”期间,更使50年代出现的青年“上山下乡”达到了空前的、世界绝无仅有的惊人规模。十年间,从城市来到农村的知识青年累计突破1400万人,应该肯定,广大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参与这项活动,在推进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这种“逆城市化”运动,从根本上是违反工业化的城市化要求的。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这是一种大倒退。
“文革”十年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几个十年之一,它对中国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是难以磨灭的。它使得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结构失衡,物价上升,效益下降,人民生活下降,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到临近崩溃的边缘。
当然,“文化大革命”也提供了极重要、极深刻的教训,“文化大革命”这种内乱决不能让它重演。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这种经验与教训在客观上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所进行的整顿,都不可能真正进行到底。这就充分证明,不从全局上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不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1968乡间的蹉跎岁月
1968年12月22日,广大革命群众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各级革委会立即制订落实措施;大批知识青年兴高采烈地奔赴农村。
当时毛主席教导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21日夜到22日,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到农村去的新高潮。
在各地城镇居民中,也出现了父母鼓励子女报名下乡、全家主动要求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动人情景。江苏省海安县角斜镇革命居民在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时候说,吃闲饭不劳动,就要变成寄生虫。在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第二天,全镇就有132名知识青年和居民奔向农村安家落户。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公社一位有十个孩子的妇女激动地说:“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我心坎上。我的十个孩子有八个念了书,现在已有两个工作、一个参军了,另外三个,我让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我也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参加劳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是在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从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后,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的,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并不融洽。“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是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因城市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
当年,政府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为上下山乡的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再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中共中央对这场运动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见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所失当。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
很多人认为,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80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达遗憾,但也有知青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有一些知青认为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了解了生活,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在90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员而失业。很多知青都把当年下乡的地方当做第二故乡,对当地的农民有着浓厚的感情,返城后仍时常惦念乃至回去探望。但也有一些知青诅咒、报怨、痛恨那段经历,返城后再也不愿回到农村。
总之,这场运动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记忆中的重大事件
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毛泽东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1965年,石油得以全部自给。
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揭开“文革”序幕。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爆发。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8年,开除刘少奇党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