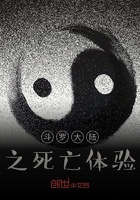“可能就因为他不像他父母,所以写信的人才这么说,真是胡说八道。”
“可惜瞎猫碰到死老鼠,给他碰对了。”乔安娜说,“而且,要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她也不会自杀,对不对?”
葛理菲用怀疑的口气说:
“我不知道,她已经病了很久了——神经质又很重,我一直负责医治她的神经疾病。我想,接到这封信所受的刺激,加上那些卑鄙的用词,可能造成她心理上的恐慌和意志消沉,所以才决定自杀。她或许想到,就算她否认,丈夫也未必相信,在又羞又气的强大心理压力下,使她一时失去了判断力。”
“所以她在心理失常的情况下就自杀了。”乔安娜说。
“对极了,我想,如果我在警方侦讯时提出这种看法,一定可以得到证实。”
乔安娜和我走进屋里。
前门开着,我们不用按铃,倒也减少了一点紧张,尤其是我们刚好听到爱尔西的说话声在里面响起。
她正在跟辛明顿先生谈话,后者在椅子上缩成一团,看起来整个人恍恍惚惚。
“不,可是说真的,辛明顿先生,你一定要吃东西才行,早饭没吃,中饭又只是随随便便塞了两口,昨天晚上也没吃东西,再这样下去,你自己都要病倒了。医生临走之前交代过,你一定要吃东西才能维持体力。”
辛明顿平淡地说:
“我很好,贺兰小姐,可是……”
“喝杯好的热茶。”爱尔西·贺兰坚决地把一杯茶放在他手里。
换了我的话,会给这个可怜的家伙一杯威士忌苏打,看起来他似乎很需要。不过他还是接下那杯茶,抬头望着爱尔西·贺兰说: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贺兰小姐,你实在太好了。”
女孩红着脸,看来似乎很高兴。
“你太客气了,辛明顿先生。我愿意尽全力帮助你,别担心孩子,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我也把仆人都安抚下来了。要是还有其他写信或者打电话之类的事,尽管告诉我,别客气。”
“你太好了。”辛明顿又说。
爱尔西·贺兰转身过来,刚好看到我们,于是快步走进大厅。
“真是太可怕了!”她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
我一边看着她一边想,她真是个好女孩,亲切、能干、懂得应付紧急状况。她那美丽的蓝眼睛里,有一圈淡粉红色,看得出她心地也很好,为她佣主的死流过了不少眼泪。
“我可不可以单独跟你谈一会儿?”乔安娜说,“我们不想打扰辛明顿先生。”
爱尔西·贺兰善解人意地点点头,带头穿过大厅,来到饭厅。
“对他真是可怕的打击,”她说,“谁想到居然会发生这种事?不过我现在也发觉,她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很奇怪,很神经质又很爱哭。虽然葛理菲医生总是说她没什么不对劲,可是我想一定是为了她的身体。她就是很容易生气,有时候真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
“我们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梅根到舍下住几天散散心——我是说,如果她愿意的话。”乔安娜说。
爱尔西·贺兰看来非常意外。
“梅根?”她用疑问的口气说,“我不知道,真的。我是说,非常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她的举动一向都很奇怪,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或者会说出什么话。”
乔安娜用含糊的口气说:
“我们想,这们或许对她有点帮助。”
“喔,话是不错,我必须照顾两个男孩(他们现在跟厨娘在一起)和可怜的辛明顿先生——他实在太需要人照顾了,除此之外,还有好多好多事情可做,实在没什么时间跟梅根谈心。她现在大概在楼上的旧育婴室,好像一心要躲开所有人。我不知道……”
乔安娜悄悄看了我一眼,我迅速走出房间到楼上。
旧育婴室在最顶楼,我打开门走进去。楼下房间面对着花园,所以窗帘没有拉上,这个房间的窗帘却全都拉上了。
我看到梅根在黯淡灰暗的房间里,坐在靠里面墙角的一张长沙发上,不禁想起受惊的动物躲在墙角的模样。她看起来似乎已经吓得发呆了。
“梅根。”我喊道。
人走上前,下意识地用一种想要安慰受惊动物的口气对她说话。我奇怪自己竟然没有拿根红萝卜或一颗糖给她,因为我当时的确有这个念头。
她凝视着我,但却一动不动,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
“梅根,”我又说,“乔安娜和我一起来问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们住一段时间。”
空洞的声音从模糊的光线中传过来。“跟你们住,到你们家住?”“是的。”
“你是说,你们要把我从这个地方带走?”
“是的,亲爱的。”
忽然间,她全身都颤抖起来,看起来有点怕人,但也令人感动。
“喔,快带我走吧!请你快点带我走。留在这个地方真叫人觉得可怕死了。”
我走到她身边,她紧紧抓住我的衣袖。“我是个讨厌的胆小鬼,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胆小。”“没关系,小傻瓜,”我说,“这件事的确很让人震惊,走吧。”
“我们可以马上就走?不用再等一下?”“喔,我想你也许需要收拾东西。”“为什么?有什么要收拾的?”
“亲爱的傻女孩。”我说,“我们可以供应你床铺、浴室等等,可是恐怕没办法借牙刷给你。”
她有气无力地微笑了一下。
“我懂了,我今天实在很笨,你可别介意,我这就去收拾收拾。你——不会溜走,会等我吧?”“我一定等你。”
“谢谢你,真是太谢谢你了。很抱歉我这么笨,可是你知道,一个人的母亲忽然死了,实在是件很可怕的事。”“我知道。”我说。
我友善地拍拍她的背,她对我感激地笑笑,走进她的卧室,我也下了楼。
“我找到梅根了,”我说,“她愿意去。”
“啊,那可真是太好了,”爱尔西·贺兰说,“可以让她暂时放松一下,你们知道,她是个很神经质的女孩,很不容易相处。我心里不必再替她担忧,就像除掉了一个很大的负担。谢谢你,柏顿小姐,希望她不会惹人讨厌。噢,电话在响,我得去接,辛明顿先生人不舒服。”
她匆匆走出房间。乔安娜说:
“真是个看护天使!”
“你的口气好像很不以为然,”我说,“她是个又好又亲切的女孩,而且显然非常能干。”
“非常能干!她自己也很明白。”“你不该这么说,乔安娜。”
“你是说,她为什么不能尽她的本份?”“一点都没错。”
“我最受不了洋洋得意的人,”乔安娜说,“使我想起最坏的人性。你怎么找到梅根的?”
“她一直躲在黑漆漆的房里,看起来像只吓坏了的小羊。”“可怜的孩子,她真的愿意来吗?”
“她高兴得跳了起来。”
外面一阵砰砰声,想必是梅根拿着箱子下楼来了,我过去把箱子接过来。乔安娜在我身后急切切地说:
“走吧,我已经拒绝了两杯好的热茶了。”
我们走到车旁,乔安娜必须用力才能把皮箱扔进车后的行李厢,我现在只要一根拐杖就能步行了,但是还没办法做这类事。
“上车吧。”我对梅根说。
她先上车,我也跟着上车,乔安娜发动车子,我们就上路了。
回到小佛兹,刚进客厅,梅根就用力坐上一张椅子放声大哭,像个伤心透了的孩子一样。
我离开客厅,想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乔安娜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
忽然,梅根用低沉哽咽的声音说: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真像白痴一样。”乔安娜亲切地说:“没关系,这条手帕给你。”
我猜她大概把手帕递给了她,我走回房里,递给梅根一个高脚杯。
“这是什么?”“鸡尾酒。”我说。
“真的?你说的是真的?”梅根立刻停止了哭泣,“我从来没喝过鸡尾酒。”
“每件事都得有个起头。”我说。
梅根小心翼翼地喝着饮料,然后露出愉快的微笑,把头向后一仰,一口气喝光了剩下的鸡尾酒。“太棒了,”她说,“可以再给我一杯吗?”“不行。”我说。
“为什么不行?”
“再过十分钟,你差不多就知道了。”“噢!”
梅根又把注意力转到乔安娜身上。
“实在很抱歉,我刚才那么大哭大闹的惹人讨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到这儿来就那么高兴,看起来真是好笑。”“不要紧,”乔安娜说,“我们很欢迎你来。”
“你那么亲切,我实在太感激了。”
“用不着感激,”乔安娜说,“不然我会不好意思。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很高兴你来玩,没别的什么……”说完,她带着梅根上楼去安放行李。
派翠吉一脸不高兴地走进来,说她中午只准备了两份布丁,现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