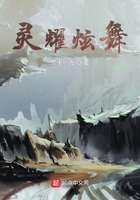“我有个死党,因为名字里不知怎么犯火犯到居然有四个火,我通常叫他老四。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怂的爷们了,长着一米九的大个子,人也不丑不傻不笨的,但他居然不会打球,更不会打架,成天龟缩在那里,恨不得能把自己变小一点!我要是有他这身高,不知道现在能成多少事。那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圆满。可是上帝是残酷的,既然给了我如此多的优点,那总得有一些小小的缺憾。所以我看着他那叫一个恨铁不成钢。先前我问他:你想干什么?你说想干什么我们就去干。他就躺那草皮上,抻着他那两条吓死人的长腿,说我想静静!我勒个去了静静是谁啊!他就只会想,头盖骨撬开下面能开宇宙战舰,但别人到死也不知道。”
002。怪杰
“咦……”女人哼出了疑惑的问声,悬在空中的双手紧了紧,跟着垂下来。
她身边华服重胄的男人发觉了,勒住缰绳转头向她。“怎么?”
“我的箭居然落空了。”她眨了眨泛着一层红光的眼睛,那怪异的光华从瞳膜上褪去,变回了原本深棕的颜色。“城里有异人。”
男人嗤笑一声。“异人?怎么可能!就凭申国那道几乎枯涸的‘异门’……”
“是真的。”女人平静地打断他的话。她斜坐在一匹温顺的牝马上,浑身裹着仿佛祭祀一样的符文装饰,并用纱巾遮住了脸。缰绳由人牵着,周围重兵拱卫,可见她人身安全的重要性。
“没关系。即便申国真藏着异人留有后招,也并不能扭转眼前的局势。”他冷冷地说,“而我们也还没有弱到只能靠异人来替我们开疆拓土,或者看家护院。你们充其量,”他不再望着女人,只是定定地看着前方高耸的城墙,一字一顿地说,“只不过是好用的卒子罢了。”
“是的,殿下。”
女人望着他轻声地回答,眼神平静无波,并没有谄媚讨好、或是不甘怯懦的神情在里面,她就像那匹牝马:已经温顺而甘愿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似的。直到男人举起手、下达号令:
“攻城!”
付义哲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眼前的状况。他至少很清楚自己在一个和先前常识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以及这两国之间正在展开惨无人道的战争的事实。透过那只怪鸟用喙在城门上啄出的大洞,敌国军队很快攻入了城市,他们毫无怜悯之心,也完全没有显现出任何收编俘虏的举动。然而,即便在如此残酷的战争中,他仍能感到自己是个彻底的外人。屠杀在双方之间展开,他们在他身遭哀嚎、逃窜、杀戮,却并不向他投来一眼,仿佛他只是一个人形的雕塑。温热的血水溅到他的脸上、衣襟上、背包上,穿着布单鞋的脚像踏进了沼泽泥地。
“救命,救……”
他听到朝向他的一声游丝般的呼救。有一瞬间,他甚至觉得那也许是自己发出来的;因为他内心此刻也有个意识拼命地想要做徒劳无功的呼救,然而理智却一再叮嘱和冷嘲这并不会有任何作用:你必须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才能被救,他告诫自己;然而他还是忍不住朝着呼救声的方向转头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两个孩子,一个拖着另一个、正跌跌撞撞地向他跑来。士兵追在他们身后、高举着战刀——
“救救我们!!”跑在前面的大一点儿的孩子朝付义哲哭喊,“救救我妹妹!”
这样小的孩子!大的那个也不过五六岁的模样。付义哲犹豫了一瞬,因为他连自己能否自保都不确定;另外,他此刻的行动真如手脚灌了铅那样(他现在明白这不是精神上的压力导致的错觉了,而是实在存在的),连迈出一步、抬起一只手都十分困难。然而就这一瞬,士兵赶上了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地砍向身后跑得慢的女孩,他们听见一声尖锐而短促的厉呼,紧接着女孩跌在了地上。
没有奇迹发生。她那双小小的、还穿着粗麻布鞋的脚就这样被轻易地砍断、留在离她的小腿一米开外的位置,血从断口处汩汩流出,沿着坑洼的泥地,交融汇合到一起。
“不——”
跑在前面的男孩大声地嘶喊起来。他返身扑向举刀的士兵,用尽全身力气将他狠狠撞倒在地,挥舞起小小的拳头砸在对方身上。但那人又举起了刀;这下付义哲来得及扑过去了,他艰难地拔起双脚,用手上厚重的铁镣重重甩上对方的胳膊,把长刀整个撞飞,又将小孩子撞向相反的一边。男孩在地上打了个滚;他的脸上染上了混着血水的污泥的脏色。
“住手!”他大声喝道,“他们是那么小的孩子——”
“长大了不就是我们的敌人了么?”
士兵立刻反驳,有两个士兵打算上前帮忙,付义哲仗着人高马大,一个箭步便跨到男孩身边;他用力挥舞起戴着镣铐和铁链的手腕,立刻将他们砸开老远。
“你做什么!?区区一个异人,胆敢反抗我们!”
“告诉你!这儿没有异人说话的份儿!”
“说到底,这一切……本来就是你们这些怪物造成的!”
士兵们喝道,他们这下换拿了长枪,一下子就绞住了他的铁链,狠狠一扯,将这个一米九几的大个子拽跪在湿软的血泥地里。五六个士兵围住他们,他们都提着被血洗得几乎卷刃的武器。
付义哲能做的,只有将小男孩护在怀里,不管他挣扎,只是埋着头、死命地按着,用自己的背脊对着刀刃上的血光。男孩大声的哭喊:“香子!香子!”从他怀里挣出一只手,朝着妹妹倒下的方向尽力地伸去。
……为什么没人阻止这么不合常理的事?为什么世界不再是以前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够无聊的。要是能穿越就好了。”他突然听见自己说。
模模糊糊的熟悉记忆浮现出来。
在一个翘课的午后,他的确这么说过。老三嗤笑:“就凭你?穿越了你都活不下去!”
“如果运气够好的话,穿到武林高手、或者大户人家……”
“那要运气不好、穿成乞丐了呢?”
他记得自己定定地说:“那也比现在要好。”
到一个完全不知道我名姓的地方,一切都可以重头开始。这一次谁也不会刚听我的名字便忍不住发笑、或者借这个名头来欺侮人了,也再没有给了我姓名后就销声匿迹不负责任的父母,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响当当亮堂堂的人物,到哪里都像武林高手那样高声地报出万儿,完全可以堂堂正正、意气风发地活下去——
瓮地一声,以他为圆心,一层灼热的气浪轰地向四周荡冲过去。四周的温度陡然加高、而某种强大的阻力令人寸步难行、继而不自觉地感到恐惧、开始后退,紧接着兵刃甚至开始融化变形……
“异人!”士兵们惊恐地叫道,“城里有异人!”
先前的女人已站在城墙高处,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她解开系带,任风将披肩和裹纱带走,露出雪白的肌肤、糖棕色的大眼睛和朱红的嘴唇,浓妆之下不算倾城,倒也薄有姿色。她的十指涂了鲜红的指甲油,那现代式的涂法与衣服的穿戴款式,也同样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她朱唇轻启,双手平张,像将整个城市都拢在中央一样,轻声吐出三个字:
“「定城土」。”
嗡地一下,整座城池像平地坠了千斤重物,轰地掀起好大的尘雾;待得土灰散去,刚才那一阵火燎般的异象,也随之消弭殆尽了。
“喔喔!!”
夲国的士兵们欢呼起来。
而整个城市里,除了他们的欢呼以外,再没有别的声响。
“大个子叔叔……喂,大个子叔叔?”
付义哲被唤声惊醒,微微抬起头。他个子高,人长得老成持重,被叫叔叔也不是一回两回。
眼下顾不得憋屈,自己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怀里还紧紧箍着那个死里逃生的小男孩。而原本打算袭击他们的士兵也同样躺在不远处一动不动了,他们手中的刀像软糖一样变形歪曲地插进土里。
“怎么了……?”他松开即便昏迷也一直箍着没放松过的手,男孩立刻从他怀里跳出,冲向妹妹所在的地方。付义哲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艰难地挪动身子,走到一名士兵面前,试图将对方翻身过来。然而刚刚走近,他便闻到了皮肉焦糊的味道。
远处响起男孩低声的啜泣。
“……叔叔……”小子哭着说,“求你……救救香子……救救我妹妹!”
“我……?……不……我没有……”
“可你明明救了我!!”
付义哲张了张嘴,他看见小女孩惨白的脸和空荡荡的双腿,不知该怎么回答。
马蹄声由远及近,片刻间一队赤黑衣甲、形容鲜丽的卫兵出现在面前。领头的将官虎眉凤目,英气逼人,一身铠甲贴身细制,片片雕麒绘麟极尽奢工,显然地位非凡。他勒住缰绳,居高临下地打量着付义哲的装束、手腕上的镣铐和铁链,轻蔑地扯开嘴角。
“你就是那个让我们大费周章的异人?”
不能回答实话,付义哲心里清楚;但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躲避,他定了定神,将自己情绪中的惊惶和乖顺的一面放大出来:“不……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小心地使用迄今观察所得的信息补了一句,“是鲁大师把我带到这的。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同时观察着对方的反应。果不其然,男人露出了鄙夷的神情,很不置信地皱了皱眉。
“什么?是鲁厚?那个疯疯癫癫逃回申国的家伙也能猎得异人?不可能!他充其量也就只能捉些陌客罢了!”他又仔细地打量了一遍付义哲,神情更是怀疑,“你——‘局’、‘赋’和‘格’都那么弱——根本不可能是你,最多也就是有一些‘气’的劣等货罢了!”
他这么一说,反倒让付义哲更冷静了一些。作为被人从小欺负到大的鼻涕虫,别的本事不敢说,但多少也有积攒这些方面的经验。他立刻顺着话、掺入些事实、慌慌张张地说道:“可、可是、鲁大师……刚刚让我站上城墙……”
敌方的统帅立刻大笑出声了:“你是刚刚城墙头的那个异箭都挡不住的肉盾!你算是哪门子的异人?死马当活马医吧!”他笑着摇头,“申国无人啊!”等笑够了,却跟着神情一冷,“那我问你,鲁厚人呢?”
付义哲本想说他死了,但见他这么问,脑筋一转,又想起杀了鲁厚那人的举动,便含糊地说:“我不知道他去哪了……他把我拽下城墙、丢在这里……”
这一次他又赌赢了。果然,男人只是哼了一声,鄙夷道:“果不其然……那家伙,丢下你当幌子自己逃了吗……”他斜睨了付义哲一眼。付义哲听着他话里的玄机,心里也盘算着逃脱的手段;而这时候,一直在旁边看着妹妹的男孩,突然抬起头说:“……是我。”
这下倒让两人都惊诧了。
男孩抱着断了腿失血过多、已经气若游丝的妹妹,抬起一张方正的小脸,一字字说:“你要找的异人是我。”
他语气太过笃定,付义哲都没法判断他说的是真假。刚才的情形他没有实际的记忆,但身体仍然留有一些隐约的触感;可这男孩这么一说,他不由得也怀疑起自己了——是了,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世界的力量……
但那名夲国统帅显然不太买小孩的帐。“哦?你是异人?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定定地直视敌方主将:“我不能告诉你。”
“你的主人是谁?”
“这个更不能说。”
“在我看来你不过是这城里的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妄自想要活命的小崽子罢了。”
“我和妹妹来得很早。”他说,看了一眼濒死的小女孩,大胆地说:“你看不见那些,因为主子对我用了‘迷彩’。”
男人警惕地看着小孩子。他至少信了一半,付义哲观察着。
“告诉我更详细的情况。”男人说。
“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男孩说,“但你要救我妹妹。”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不信也可以。”男孩低声说,女孩的气息越来越弱了,生死显然只在刹那之间,“但我会记得,她是被你们砍成这样的。我会记一辈子。”
付义哲反倒变成了一个旁观者;他惊诧地看着这瘦小的男孩子的言语。很明显,他掐准了对方的软肋。统帅恼怒地一甩马鞭,最终示意了一下身边的人,他们立刻拉扯起男孩、抱上断腿的女孩,匆忙地询问了几句,便向给士兵疗伤的大帐奔去。
“殿下,”始终跟在旁边的副将谄媚地问道,“这个傻大个怎么办?”
殿下?他是敌国的什么重要人物吗……付义哲心念电转,但脸上情绪不露分毫。正常的思维从环境的陡然改变造成的冲击中正在逐渐恢复。不得不承认的是,让他能够冷静思考的,居然是那个不过五六岁的小孩子,他为求生存而展现出的冷静和强大,像一闷棍打清醒了付义哲。也许是穿越……最差如果真的是穿越……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不是早就设想过这样的人生吗?这未尝不是机会,一直想要的机会……
“按陌客的规定处置吗?但没有狩异师持有的‘真名’的话……”
“也可惜了,还是有一些‘气’的。”那位殿下瞧了瞧他,像打量一件商品;最后得出结论,“先牵下去关起来吧,总是能当肉盾,也不算没有好处。”
总管点点头,旋即一招手,上来三五个大汉,将他头头脚脚地一抬,哼哧哼哧地扛上了一架臭烘烘的牛车,拖着去了监牢。
为什么一定要用人抬?我明明自己能走……付义哲这才想起他想行走时脚仿佛灌满了铅,以及别人来怎么拉拽他的铁链,他都没办法轻易跟着他们离开……
他又想起那位总管的话,以及懵懂刚醒时,面前初见的被称为“鲁大师”的男人问他姓名的样子。
‘真名’……?
难道都到了另一个莫名其妙的世界,还和那个该死的名字脱不开关系吗?
他被重重扔进监牢。这里显然是原来这座城市里关押囚犯的地方,然而那些囚犯却不知所踪,并没有新的犯人或俘虏被关进来。他想起外面仿佛地狱般的情景,缓慢地坐下,心想在他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种种见闻,相比下这窄小的、散发着潮湿稻草气息的监狱反倒称得上是天堂了。
他闭上眼,喘一口气。如果那个小男孩在那时没有说出那些话,自己的嫌疑很难洗脱,现在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但那到底是什么?那火焰灼烧一般的感觉、那些士兵又是怎么倒下的?完全记不起来了,也许真是那个男孩……但如果他只是想救妹妹就说出这样一篇的谎话,是不是也太夸张了?为什么那个什么‘殿下’的居然会相信他的话?
他又想到那个女孩。“香子”,是这么叫的……即便她侥幸活下来,她的腿也……如果最初不犹豫,是不是应该能更快地把他俩扯过来,那样就不会——
他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梦继续着那个翘课的晴朗午后,老三和他并排躺在草地上。“不管去哪,都带我一个吧。”老三说,“这样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我们到哪都是无敌组合。”
付义哲感到自己确实安心不少。毕竟,他俩实在是难能一见的难兄难弟。在自己曾以为要被人欺侮得往失足青年那范儿上走、感觉再下去就要闹出人命的节奏上,是这个乐天的家伙出现挽救了他的人生。毕竟,一个叫傅燚喆念起来像“妇炎洁”的人,在生命中碰到一个叫衡钰湘念起来像“恒源祥”的比例,大约是万中无一吧。
他们都经历过姓名被嘲笑、从而被欺负、孤立的经历,甚至还被起了各种卑微的外号,然而却成长成了两个全然不同的人。与自己的阴郁、话不轻易出口相较,衡钰湘乐观开朗得简直像过去的倒霉日子都不存在一样,当然,这有可能归功于他个人十分会打架。而自从他俩结伴后,虽然看他们不爽的人还是有,但毕竟不敢上门直接挑事了。
“老天爷还能听你安排吗?”他听见自己当时嗤笑着说。
“我们为什么要听他安排呢?”老三叼着草根,懒洋洋地反问。
“你也是被抓到这里来的?”
一个女声突然传来,把浅眠中的付义哲惊醒、吓了一大跳。他本以为这间囚牢没有其他人了。他快步走到牢槛前,隐约看见隔着一条走道的另一边,关着一个穿着牛仔服的年轻女子。长得不算漂亮,却平平白白,耐看得很;梳着齐耳短发,穿着眼熟得令人流泪的服装:牛仔吊褂、**带衫和牛仔裤,下面是一双雪白的运动鞋。
那感觉真像头脑上挨了一闷棍。这到底……如果是穿越还带组团玩的啊?付义哲不禁对自己的推论再一次产生了怀疑。也许,这一切只是某个黑箱的什么电视游戏?生存节目?就像自己以前遭受的那些不公正待遇一样,自己又被人作弄来了这里,一群看客以看他出洋相为乐吗?
他下意识地警惕起来,惯性地将嘴唇抿成一线,四处环顾周围的景象。也许某个角落藏着什么提示、或者摄像头,也许铁门是虚掩着的,对面是给他配戏的专业演员……有一群那样成天闲着没事做、以嘲笑别人为乐的家伙,正捂着嘴,焦虑地等着看他洋相的一刻——这样的经历,他在成长过程中也算是经验丰富,不过在遇到那个没心没肺又打架吊炸天的死党祥子之后,他有阵子没有烦心过这种事情了。
付义哲站起来,打量牢房内部的每个细节。他并不擅长和女人说话,所以干脆不说。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反倒会引起对方的兴趣,可能是因为他的背板得很直,而神情又一如既往地高深莫测,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再多试探他一点。
然而不露声色就是这个大个子这么多年来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他已经把这招练得炉火纯青了。只要微皱眉头,眼神专注,即便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发呆,也让人觉得他似乎胸有成竹,从而在行动上要自怯三分。
女人果然好奇地打量着他,先一步开口发问:“你就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你知道的不见得比我更多。”付义哲简单地回答。他不太搞得定女人,老实说有点拿她们没辙,也找不到什么话题,为了避免尴尬,所以总是尽量减少自己和女人的对话。在日常生活里,却总被人说是高冷。但他也不想解释,解释还得费唇舌,他更想多一点时间去做自己的事。
“别这么不近人情,至少可以交换一下相互的信息,我猜你也很茫然。”女人更好奇了,她甚至凑过来,贴着栅栏观察付义哲的动作,“你在找什么?”
他确定了门的确锁得严实,锁眼也并不是他所在时代常见的弹簧锁等新式款型,而是老式横开的,显然也用过了很长时日,相当老旧。接下来他检查铺在角落里的破席子,查看上面有没有标签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证据。”他最后还是回答了。
女人撑着下巴看着他笑:“证明这不是一场整蛊游戏?”
“这的确是要证明的内容之一。”
“这一路来你就没问问人吗?”女人说,“一看也就知道。”
“我所见的也是‘他们’让我看见的,并不一定为实。”付义哲回答,“比起被人引导着或是想当然匆忙下的定义,我更确信自己验证得出的结论。”
女人大笑起来。
“哎,我还以为每个异人看见我都会那样大叫着‘妈呀我终于看见一个正常人了’然后拉着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上一大堆,最后累得放心地倒头大睡呢。原来也有你这样谨慎思考的啊。”
她话里的信息终于让付义哲猛地抬头,把注意力转回了她身上:“你是说……还有别的人在?在我之前就找过你?”
女人摊了摊手,露出一个“你早该问我”的神情,向左侧一努嘴。
隔壁厢的牢房里,也几乎同时、配合地传来隆隆的鼾声。
付义哲只往那边看了一眼确认,就忍不住扶额——不会吧——
还特么真是他啊!
但见那囚笼之间、一方稻草上头,正睡得昏天暗地浑然不知、一手还惬意地挠着肚皮的男人,正是他的死党兼“病友”:
因为名字发音近似“恒源祥”而人送外号“三羊”的,超·乐天派怪人,衡钰湘。